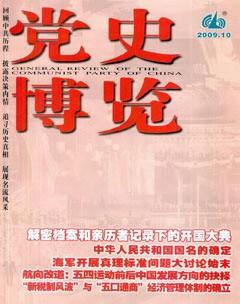航向改道: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展方向的抉择
齐卫平
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百年抗争中具有历史转折的重大意义。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五四运动洗礼而显现出新的生机。这样的生机,表现在一些先进人士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的思考。他们的思想动向,印证了中国发展道路改向,代表着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鲁迅:“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经使中国人激动、欣喜。中华民国的建立,给许许多多对民主共和充满憧憬的人们带来热切的期待。然而,失望很快随之而来。中华民国初期的实践不仅没有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反而使人增加了新的忧虑。
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帝制,使中国政治驶入了近代的航向。权力制衡的政权架构、约法之治的宪政端倪、党派竞争的政党政治、内阁议员的选举制度等西方近代政治形式都搬用到了中国,一个传统的古老帝国也终于“走向共和”了。但是。人们很快就品尝到了南橘北枳的苦涩,这些在西方国家搞得像模像样的政制,一到了中国却无不扭曲走样,变了味道。内阁总理走马灯似的更换,旧官僚变脸成为新权贵,贿选盛行助生猪仔议员,政党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共和其名,专制其实”、“挂羊头卖狗肉”,成为人们对中华民国的普遍感觉。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是深深陷入思想苦闷的一个学人。那时他住在北京一间屋子里,备感窒息。《狂人日记》、《呐喊》、《彷徨》反映的创作心情,与鲁迅描述这间“黑屋子”有关。他由“黑屋子”的沉闷想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很想冲破牢笼。对于改制换新的共和社会,鲁迅很是纳闷。他把中国社会比作一个黑色的染缸,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皮毛改新,心思依旧”,讥讽中国人不是不善于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乎自己”;他说武昌起义掀动的风潮在许多地方就像是在衙门的屋顶挑掉了几块瓦片,其他一切照旧,“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他甚感迷茫,想大声地呐喊,呼唤“黑屋子”里的人们从沉睡中醒过来,但又忧虑唤醒人们是不是更加残忍,因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他愤慨地写道:“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当然,鲁迅决不甘于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虽然写于1926年,但把它用在认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的思想状态同样是适用的。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只有八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就被社会耗掉了它的巨大历史价值。鲁迅的失落、愤慨和困惑只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个缩影,许多知识分子把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比作一只小船,“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激荡,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怅望前途,不寒而栗”(李大钊语)。超越辛亥革命,寻找中国发展新的航向,成为社会的客观需要。
李大钊:“惊秋的一片桐叶”
鸦片战争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踏上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征程。“天朝帝国”的急遽衰败,促使他们将眼光转向了域外。曾经有过的民族辉煌已经风光不再,曾经体面的民族尊严已经一扫而光,真可谓“国已不国”,主权丧失、城下之盟、割地赔款、资源旁落。亡国灭族的灾难,成为时刻悬挂在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摆脱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一方面开展英勇的抵抗斗争,另一方面开始了社会前行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朝代更替和帝王换位不断重复着历史周期,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方向和道路的危机,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内循环的运转轨迹,第一次将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五四运动之前,~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临摹式的仿效。在学习内容上,先是学兵舰轮船、火器枪炮等器物层面上的船坚炮利,后是学内阁、选举、政党、宪法等制度层面上的政制规章,再是学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层面上的理论学说。在仿效目标上,先是以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为榜样,然后是以英美为师,再是崇尚法国革命,到五四运动后,“走俄国人的路”成为新的选择。近代中国先进人士不甘心受外国凌辱欺压的命运,在救国救民的抗争中,一次次寻求道路和方向的超越。
李大钊曾经热烈地追求过民主共和的理想,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中华民国建立后,他就十分担忧中国是否能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12年他写了《隐忧篇》一文,表达了自己对中华民国的热切期待。1914年他又写下《大哀篇》一文,激愤之余流露出一份伤感。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的所见所闻让他深感失望。“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无所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悲切伤感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李大钊开始怀疑辛亥革命是否真的成功了,开始怀疑西方民主共和的道路对于中国是否真的有价值。这样的怀疑表现在他对议会制度的思考中,他指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意思就是说,以代议政治为核心的民主共和道路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民主共和在中国不成功的试验在他头脑中的反映。像李大钊这样的怀疑并非只是个别现象,很多知识分子都处在疑虑、苦闷、徘徊之中。他们观望、挣扎,但却不知道希望何在;他们思索、探寻,但却不知道路在何方。
历史必定是要朝前迈进的,山重水复后总会迎来柳暗花明的那一刻。1917年近邻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立即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李大钊最早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具有路向意义的新讯息,从而为作出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抉择奠定了基础。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西方各种歪曲、污蔑、攻击的报道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大量出现。使人难以了解真相。李大钊则不为流言飞语所惑,仔细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他热情讴歌和颂扬社会主义“滔滔滚滚的潮流”,“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这些洞穿时代的认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航向改道的思想引领,在民国初年共和实践的迷茫中透出一丝明光。
陈独秀:“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在五四运动之前,西方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旗帜,卢梭、伏尔泰、盂德斯鸠等思想家受到热捧和颂扬。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西方的这些思想,遇到中国封建文化就败下阵来。辛亥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结出的硕果,但中华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却又成了这个思想在中国行不通的证明。
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起改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办。它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思想界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试图从思想变革的路径,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作最后的拼搏。在那批新文化运动的勇士看来,中华民国之所以搞得不伦不类,原因在于虽然中国的体制变过来了,但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旧的,用旧的思想操作新的制度,必然换汤不换药。“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陈独秀语)在新文化运动中。伦理觉悟、文学革命、道德革命、人格解放、个性独立的呼喊不绝于耳,并以广泛的影响促进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空前的思想解放,西方各种新思想纷拥而入。这场新文化运动,从方向上说,并没有摆脱原先的发展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然是思想旗帜,民主共和仍然是追求的目标,但它所酝酿的思想变革,则为中国革命航向的改变扫清了障碍。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就是首先在他的手里高高举起的。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的历史人物,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不是个等闲之辈。他以与封建制度势不两立的激进态度,投身反对清廷的革命斗争。武昌起义后,他成为安徽革命党活动的骨干,还两度担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时人流传“武有柏文蔚,文有陈仲甫”。柏文蔚任都督,因长期在外,安徽的事情都由陈独秀在负责打点。陈独秀年轻气盛,志远情急,在任上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招惹得罪了一大帮守旧顽固人士。1913年,他参与孙中山兴师讨伐袁世凯失败而逃离安徽,亡命上海。经过这样的折腾后,陈独秀开始一心致力于思想革命运动,周围聚集起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激进知识分子,探寻改造中国的新道路。正是在新的探寻中,陈独秀实现了其个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
五四运动以前的陈独秀,对民主共和的信念非常执著。他虽然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但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陈独秀认为,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还是将来的事情,当下急需要做的是真正实现民主共和。1917年1月,陈独秀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新青年》向来以传播新思想为职志,上面为什么不见有最新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呢?陈独秀回答这位读者说,因为中国产业还不发达,兼并还没有盛行,阶级矛盾尚未激化,现在提倡社会主义为时过早。从这个答复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从社会发展程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五四运动前后思想变动深刻地影响着陈独秀,他经过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开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形成新的判断,认为中国“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路,前途遍地荆棘”。经过对俄国十月革命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陈独秀放弃了民主共和的追求目标,作出了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他指出:“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陈独秀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者,有独立、鲜明的个性。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接纳和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完全是出于思想上的反省。从开始时认为提倡社会主义为时过早,到后来认为,中国要急于讲社会主义,陈独秀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认识十分深刻。他认为:“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以此为据,他认为,“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这就是说,陈独秀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发展的实际意义,他的思想转变是顺应社会需要的结果。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轨迹表明,中国革命航向的改道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五四运动前后思想变动是多层面的,主要表现在两种知识分子身上。第一种是像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过辛亥革命,强烈追求过民主共和的目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烙印很深。对他们来说,选择新的革命方向,意味着将抛弃旧有的世界观,告别曾经选择的道路。第二种是像毛泽东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五四运动前后初出茅庐的青年群体,阅历相对较浅,世界观尚不成熟。对他们来说,选择新的革命方向,意味着在各种五颜六色思想的分辨中确定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生平阅历、教育背景、身份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中,则最后走到了一起,共同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携手进行了组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活动,引领着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道路发展。
五四运动时的毛泽东,相较于陈独秀、李大钊来说是学生一辈的年轻人,他和同时代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如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等人一样,大都刚刚走出校门,踏上社会不久。涉世不深。可他们志向远大,血气方刚,激情洋溢,立志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与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变过程中需要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痛苦挣扎不同,他们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不需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也不需要考虑什么声名地位、利益得失。辛亥革命发生时,他们虽然也会跟着长辈们亢奋一阵,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也不像曾为民主共和浴血奋战的前辈们那样有严重的失落感,有迷失方向的沉重心。五四运动发生时,青年毛泽东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一年,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风暴为他提供了介入社会和投身洪流的舞台。他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来回活动,广泛联络,接触新思想,结识先进分子,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国家大事和时事政治,在同学中是一个思想活跃分子。他曾经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很感兴趣,后来又崇敬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读过林肯等外国人的书籍,但这些人物的思想没有主导毛泽东的世界观。1915年以后。毛泽东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对陈独秀敬佩不已,成为当时先进潮流的追随者。该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寻求志同道合者。1918年,他与好友组织成立的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一个很著名的进步团体,起的作用很大,从这个团体里走出了蔡和森、萧三、何叔衡等著名人物。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研究各种思想、主义的是非价值。以便找到武装自己思想的利器。
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转变中,毛泽东表现出“思想饥渴”的症状。他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都曾经影响过他。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形容五四运动时自己的思想就像一个“大杂烩”。这种思想状态恰恰反映了世界观尚未成型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没有固定的思想信仰,奋斗目标尚不清晰,对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处走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毛泽东竭力主张新民学会的会员要确定某种主义作为团结奋斗的基础,说:“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在学会讨论和在给会员的信件中,围绕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主义反复进行分析比较,在慎重思考的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与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代要求相吻合,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主义就是旗帜,有了旗帜就有了方向。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者以后。就积极投身实践。他参与陈独秀等人的建党活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取代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反复实践,几经周折,终于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确定了正确的航向,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因此而得到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