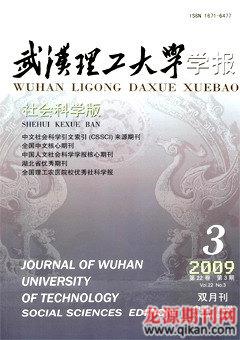路遥作品悲剧美学特征论
徐祖明
摘要:从艺术的角度,对路遥作品中的悲剧美学,概括其三点特征:一是对比手法展现生活环境的无限悲苦;二是反讽艺术揭示人物性格的严重扭曲;三是圆形结构绘画人物命运的深重灾难,它们共同构织出路遥作品中悲壮的生活图景。
关键词:路遥作品;悲剧美学;艺术解读;对比手法;反讽艺术;圆形结构
中图分类号:I01;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31
路遥以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才华,创造了一座供人景仰的艺术高峰。他用生命所绘制的现实主义文学珍品,蕴含着一种厚重而隽永的悲剧美学,凸显出一股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一、对比手法——展现生活环境的无限悲苦
路遥的作品运用对比手法,刻写了二元世界的巨大反差,描绘了两样人生的不同作为,凸显出生活环境的无限悲苦。
(一)二元世界构成生存的苦难背景
路遥的作品前后跨越30年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初一90年代初)。不管是前十多年的困难和动荡,还是后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都构成了作品展现人物生活的深厚背景。在这起伏不定、变幻殊异的生活岁月里,作者总是营造出对比鲜明的二元世界:幸与痛、喜与悲、乐与苦、顺与逆,而作品又往往是将它的主人公置于负面的境遇即苦难之中,让他们经受煎熬和磨砺。
人们曾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概括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农”问题。实际上,“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前已普遍严重地存在着,路遥在他作品中就用如椽史笔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凋敝惨状,书写出广大农民的悲苦生活。
1.生存的艰辛。改革开放前的亿万农民,最现实也最迫切的是吃饭穿衣的生计问题。路遥将切身之痛融注于作品的人物形象之中,勾勒出人物生存的悲苦图景。
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作者将其主人公马建强置于县立中学一个贫富悬殊的班集体里,马建强是这个所谓尖子班的唯一农村学生,其他都是来自县城干部家庭。在这里,作者对比鲜明地突出了马建强这个农村学生生活的极度贫困:他家里穷得“烂包”,他是带着一点“百家粮”来求的学。马建强的穿着和食物在这群衣食无忧的同学眼中简直就是一个“异类”。一次“鼠盗玉米馍”事件和“国庆节会餐”,使马建强倍受屈辱。作品逐层深入地刻写了马建强在学校里所遭遇的多重磨难,既有充饥御寒的生存困扰,又有其他同学的眼光刺激,还有他本人的内心煎熬。更令人心痛的是,女同学吴亚玲两次暗中送他钱票,好心相助异化为无情伤害,给他造成的痛苦决不轻于饥饿袭身的折磨。作者这种对比性的写实之笔,渲染了主要人物生存环境的极度苦难,为他们日后的性格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2.奋斗的艰难。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桎梏。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人生》中的高加林就经历了迥异的两种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其一是繁重艰苦的农村劳动,其二是优越体面的县委宣传干事;又面临两种不同的婚姻选择,一是农村姑娘刘巧珍,二是县城同学黄亚萍。作为农村出身的一个追求知识、富有抱负的青年,自然选择了后者而舍弃前者。但是,他生不逢时,在履新职后刚显身手,采访报道初战告捷,就遭遇被人告发(是靠走后门而转干)的沉重打击,政治的、爱情的美景竟是昙花一现。高加林出外奔前程的夭折反映了当年农村青年圆梦的困惑和艰难。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孙少平所遭受的苦难,不仅是有马建强所经历的种种衣食窘迫,更有出外当揽工汉的超常辛酸,以及成为煤炭工人后的重重磨难。这个人物应该是综合了马建强与高加林两个人物命运的痛苦和坎坷而又有新时代因素的崭新形象。孙少平在县立高中的生活困境,是马建强中学生活的继续和发展,后来他离乡背井的遭遇就比高加林更为惨苦。作者一改高加林靠关系走后门的悲剧,让他的主人公孙少平凭着自身胆识独自闯荡江湖。孙少平首先来到黄原市,成为当时农民出外最易就业也是最为艰苦的揽工汉,每天超负荷的苦脏累活不仅不是痛苦,而且是求之不得的第一需求,经常是干了今天,又担心明天,一遇没人请去干苦脏累活,就不成其为揽工汉,就面临肚皮之虞,生存堪忧,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的孙少平,就是一个地道的漂泊异乡的流浪汉。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农民工生存境遇的一个生动写照。
孙少平告别揽工汉生涯,虔心争当“煤黑子”之举令人咀嚼。市郊阳沟大队曹书记帮助转出来的户口,由于其女儿瞧不上孙少平,而失去任何价值。孙少平到黄铜矿务局大牙湾煤矿当挖煤工,实现他人生的战略大转移,此事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按世俗计,在黄原市有田润叶和田晓霞两姐妹的鼎力相助,孙少平满可以在这座城市立稳足根。尤其是田晓霞,与孙少平之间已明确了恋爱关系,作为黄原市的第一“公主”,完全有能力为孙少平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作者可以让曹书记利用便利条件为孙少平领来一份当煤矿工人的表,也可以让田晓霞出面找有关部门成全孙少平当煤矿工人的心愿,就是不让田晓霞直接帮忙,在黄原市解决孙少平的工作问题;而且还把孙少平在黄原市团委组织暑期夏令营的突出功绩也漠然处之。当然这里有高加林的前车之鉴,孙少平不能再步其后尘走裙带关系的老路,只能另辟蹊径。同时,作者主观上是坚决反对靠关系谋职业的,他曾对他的一些亲戚找上门来要求他给“安排工作”很是不满和大发牢骚。另外,作者占有煤矿工人一定的生活素材,他弟弟王天乐就当过五年的煤矿工人,这对作者安排孙少平去煤矿当“挖煤工”,无疑提供了活生生的启示和借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对劳动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尊重劳动人民,热爱艰苦的劳动,把劳动视为砥砺意志、打造精骨的有效途径和最佳方式,越是艰苦越是推崇。孙少平作为他理想的实践者,就势必要终身与劳动为伴,而且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艰苦地劳动,这是路遥自身信念的外现,所以孙少平要离开黄原市的揽工汉生活,选择挖煤工就合乎作者的理论逻辑。有所遗憾的是,孙少平不是不可以去当挖煤工人,而是作者把孙少平在黄原市的地位,也就是把他在这里的社会关系铺排得太厚重了,使得他在工作出路上有着多样性的选择,去煤矿就不是唯一的去向,而变成了一种低劣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社会成本太高;而且作品对孙少平作出这种选择也没有给予必要的心理分析和说明。
大牙湾煤矿的客观条件不能与黄原市相比,
挖煤工人的生活与揽工汉的境遇相比也无优势,甚至可以说,孙少平是脱离了“虎口”,又掉进了“狼窝”,一个地方更比一个地方艰苦。作品也藉此逐层深入地凸显了主人公的奋斗精神。
作者通过孙少平的滞重足迹,步履出中国农村嬗变的艰难历程;通过与他兄长孙少安留守家乡创业起家的映照,突出了一代青年农民在那个社会大变革年代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两样人生折射出现实的严酷
作者以爱憎分明的炽烈感情,歌颂了正面形象的可贵品质,鞭笞了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
1.于政治冲突中抑恶扬善。“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忧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雄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弩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雄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透过这特殊的一幕场景,我们深感社会对人性的严酷挤压,因此也愈益钦佩正面形象的坚强品格,鄙视一批势利小人的龌龊行径。
2.在人生抉择中贬丑颂美。在人生旅途中,往往会出现各种扑朔迷离的十字路口,如作者笔下:大学毕业分配的何去何从,爱情婚姻的忠贞与否。对这类关键问题的选择和回答,可以披沥出人物品质的高下优劣。
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男女主人公,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一起同学到大学毕业,但在分配去向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作者深情地赞美了女主人公郑小芳信守初衷,毕业后坚决回到家乡那个艰苦、贫瘠、单调的沙漠农场去工作的献身精神,贬斥了男主人公薛峰食言不专、逃避艰苦、贪图舒逸的个人享乐主义。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设置了两对鲜明的对比,其一是两个女性:卢若琴与刘丽英,前者善良、清纯如水地关爱高广厚父子,后者势利、贪图虚荣而抛夫弃子;其二是两个男性:高广厚与卢若华,前者厚道、忍辱负重地尽职爱家,后者自私、心理阴暗地追名逐利。
作者在这对比的文字中,鲜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审美观:爱人民、谋他人之利就是大善大美,图私欲、求一己之得就是大恶大丑。
然而透过这些正反形象,我们也痛感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及其对人性的刚性挤兑:使优者刚强伟岸,使劣者扭曲变形。
二、反讽艺术——凸显人物性格的严重扭曲
李建军先生指出:“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表现对象在内容、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为了维持这种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路遥作品中运用的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权势异化的反讽
1.权势对小人物的愚弄。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位置,被大队支书的儿子靠权势顶替了下来;而后来他又靠其叔父的权势成了县委宣传干事。这里面就包含着一种让主人公十分尴尬的二律背反,高加林既遭祸于权势,又得益于权势;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加林最终又被一种更大的“权势”终止了他的人生美梦,他在县城的情敌之母利用了人民政府的权威,逼使他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乡。
这里,作者通过高加林的祸福转化,针砭了权势对小人物命运的摆布和捉弄。
2.权势对平民的挤兑。《卖猪》中,刘婶子卖猪的辛酸是对那个“大革命”年代所谓“公家人”荒唐行径的控诉。一个穷乡僻壤的孤老太婆,对“公家”一片虔诚,卖猪途中,捡到一头“公家人(副食公司的收购员)”丢失的一头大肥猪,她义正词严地斥责了一个图谋趁火打劫的肥私者,“天经地义”地交给了来寻猪的“公家人”。然而她辛辛苦苦喂养了半年的“小黑子”猪却被“带红袖标”的“公家人”以低于她半年前买猪钱2角的价格(7元8角)“统购统销”了去,以至于害得刘婶子后来于苦痛之中竟丢失了那点血汗本钱。刘婶子卖猪的苦痛遭遇,无情地披露出她所心仪神往的“公家人”无异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
作品表层写刘婶子的愚忠,实质却痛击了世事的乖张,揭露了那个时代一些人的邪恶。
3.势利小人的劣行。“文革”中的跳梁小丑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演绎着滑稽的闹剧。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金国龙这个“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质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的小人,文革中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组织“红总(孙大圣)”战斗队队长,他以革命者的姿态泄私愤、图报复,审问、毒打当年判他刑罚而今被关押的县委书记马延雄。还有所谓的“段司令”、“侯政委”之流,又借机扇阴风、点鬼火地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给予这群小丑们以无情嘲讽的却是,他们下“通缉令”要捉拿归案的“畏罪潜逃”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原县委书记马延雄”竟神奇地出现在他们誓师大会的现场,使得这伙“革命者”手足失措之中以草菅人命而收场,这群小丑们的劣德败行也就赤裸裸地毕现于大庭广众之下。
4.落伍者的愚钝。《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里的五叔和《平凡的世界》里的田福堂、孙玉亭,他们是作为旧时代的象征型人物进入作品而成为揶揄对象的。
作者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这部短篇小说里,浓缩了五叔这个人物大半生的生命历程。五叔是“我”姑父的弟弟,是“我”亲眼目睹了他大半辈子的为人处事。五叔由在村里说人的人变成一个被人说的人,一个堂堂的村支书却成了一个被拘留所拘留的羁押者。五叔的前后变化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那一类人的讽刺和嘲笑。他们抱残守缺,固持教条,不理解新时代、新政策和新生活,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新步伐,自然就受到历史的唾弃。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五叔”一个人,而是写出了一个典型,正如作品所说:
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这里作者揭示出一个悲剧时代与悲剧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悲剧人物不会随着悲剧时代的结束而结束,这是更为沉痛的悲剧。而且作者的立意还在于,他要探讨如何结束这种悲剧人物给社会造成进一步的悲剧。五叔是一位村支书,由这么一个满脑子旧思想的人把持着农村基层政权,怎么能够带领农民实行党的农村政策,他将会给
我国的改革开放造成多大的阻力。所以作者忧心忡忡地说:
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们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办法……我们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30年后再回过头看过去的岁月,我们所走过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足以证明作者当时的远见卓识。
在《平凡的世界》里,田福堂和孙玉亭,具有五叔类似而又不同的性格特征,也成了作品漫画和讽刺的可悲人物。田福堂是双水村几十年来的党支书,可他的权威也屡遭新时代新生活的嘲弄。在家事上,他施用“阴谋”扼杀女儿的爱情,其结果是害得女儿田润叶在爱情婚姻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挫折。他起初坚决反对儿子田润生与其同学郝红梅(寡妇)结婚,但后来还是抱着他们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在公事上,他为了加强个人威信,组织策划社员深夜开挖石圪节村库坝偷抢东拉河水,结果闹出一条人命,社员金俊斌被偷出的汹涌大水冲走。作品还特写了这个人物的老谋深算而又机关算尽。1977年,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激励”下,他头脑发热,想大干一场,像陈永贵一样出人头地。他构思出了一条妙计:用炸药把村前的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搬迁房屋闹得全村鸡飞狗跳,人怨天怒。其结果又是事与愿违,不仅开山炸死了“半脑袋”田二,而且后来洪水还冲毁了大坝,把“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的标语冲得只留下“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对他这位决策者的嘲讽。
孙玉亭出现在读者眼前时是村支委、农田基建队队长、学校贫管会主任。这是一个典型的“开会迷”、“运动迷”,他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满门心思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可他不会劳动,老婆贺风英也不会过光景,家里寒碜得“烂包”透顶。在作品里他自始至终都穿着一双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四处“革命”奔波,总是从他哥孙玉厚烟锅里挖点烟叶抽,这幅寒酸相就是对他这个“革命者”的尖刻嘲笑和讽刺。他与寡妇王彩娥偷鸡摸狗,成双结对地被锁在王彩娥家,闹出王姓与金姓两个家族的械斗,出尽了这位“农民革命家”的洋相,也更是对他“革命意志”的否定。他的一系列革命举止,让人啼笑皆非、五味杂陈,活现出一个可憎可恨、可怜可嫌的那个时代的革命家形象。
所不同的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作者对他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里所表达的忧虑进行了化解,他让代表旧时代的人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新人物日益成长、强大,以孙少安、金俊武为代表的新生代到后来完全取代了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些“遗老遗少”,成了双水村的带头人。不仅结束了一个悲剧时代,也让那些悲剧人物寿终正寝。
(二)对爱情婚姻变味的反讽
路遥还对一些变味的爱情和婚姻给予了贬斥,构成了一种反讽艺术意境。
高加林的爱情悲剧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违背人生准则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我们也感到,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也像他的人生悲剧一样,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转型期一代青年的共同悲剧。在《你怎么也想不到》里,薛峰也是由于人生观发生了偏斜,使得他的爱情生活才出现了差错。他离弃郑小芳而又被贺敏所戏弄,生活常常就是这样无情,善恶有报,一报还一报。《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由于她对爱情的不忠不专,在婚姻问题上,这山看着那山高,结果也是白吃苦果,不得不与她高攀的第二任丈夫离婚,一场婚姻美梦一场空。
爱情婚姻上的变味,不仅透示出当事者可鄙的灵魂,也折射出时代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拘囿和威逼。小丽自得地离开高大年,是因为她考上了省城大学。康庄不顾冯玉琴的真挚感情,竟然当起说客,其无耻的背后却是生活的威逼。郝红梅拒绝孙少平,一味地追求“白马王子”顾养民,结果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惩罚。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因素在左右着。
三、圆形结构——展示人物命运的深重灾难
圆形结构是文学作品刻写人物命运的一种惯用艺术手法,它能形象地揭示事物发展的固有属性,反映人物性格的局限和悲剧命运。路遥作品中也运用这种表现方法,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一)圆形结构反映现实生活的严峻
《人生》这部作品是一个典型的圆形结构,高加林从农村到城市(县城)又回到农村,经历了一个圆周运动。它昭示出自身力量的有限,个人奋斗的艰难;同时它也揭示出生活现实的严酷和无情。在这一圆形运动中,高加林问心无愧,他并非人们所指责的忘了根、背叛了土地,而是社会不够昌明和有失公正的一个受害者。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所经历的圆形运动有其独特性:从土地上走出来,到黄原当一名揽工汉,最后来到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实际上又回到了土地之中),可简化为土地之上——城市——土地之中。孙少平属于高加林一个类型的人物,只是凭着一股不愿困守家乡的闯劲和胆识,才得以离开土地成为最初的农民工到外面闯世界。可是他在黄原市当揽工汉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后来他劳神苦心地当了煤矿工人,成为当时为农民们所羡慕的公家人,其“煤黑子”的种种艰难却是古往今来煤矿工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孙少平出外闯荡的艰辛决不少于留守土地上的农民。这也是把他的生活之路归为圆形之一种的理由之一,从他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农民工出外谋生的艰难困苦和忍辱负重。
在作者笔下,还有王满银作为一个“逛鬼”离家出游又回归故乡的圆圈运动,有刘丽英离婚再婚又回到前夫与儿子身边的人生周折,有薛峰与郑小芳从小相恋到同读大学再到毕业分手,后来又有走到一起的可能趋势。
作者通过这种种的圆形艺术,表现了当事者的悲欢离合,更揭示出社会对人生的强行揉搓。在生活的固有磁场中,个人都难以摆脱圆周运动的制约,都要遭受各自命运轨迹的沉重羁绊。
(二)圆形结构勾画人生命运的坎坷
作者通过这种圆形结构形象地反映人物的生活图景,揭示人物命运的曲折走向,增强了作品的悲剧美学魅力。
孙少平的人生之圆,他从家乡来到黄原市当揽工汉,再到大牙湾煤矿成为“煤黑子”,这是当时农民离开家乡土地到外面闯荡世界的写意图。一个农民家庭的后生,劳动与艰苦是其天然的伴侣,他不会躲避,反而还生眷恋和喜爱之情。作者给他在黄原市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爱情世界,对于一个揽工汉来说,他有无上的幸福喜悦感,但他绝不会利用田晓霞和她父亲的权势,谋得一份体
面的工作。但煤矿又确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地方,不仅有繁重的劳动,而且还有生死的考验,小的有煤矿井下劳动过程中的突发事故,大的更有矿难的爆发。作品只是描写了几次小事故,就已经惊心动魄,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为救徒弟安锁子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孙少平为救自己班上的兄弟,身负重伤,虽然得到及时救治,但脸上却留下了一道刺人的疤痕。
孙少平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圆形:现实——浪漫——现实。他与郝红梅之间,尽管在县立中学里有着共同的生活境况,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郝红梅要摆脱她地主家庭的阴影,就不可能与孙少平相爱。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尽管孙少平个人素质(坚毅、顽强、拼搏、永不屈服的性格)令田晓霞真心相爱,尽管田晓霞具有超凡脱俗的个性特征和情感世界,但两人之间,从个人条件到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地委书记(后来还是省委副书记、省城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一个是地道农民的儿子、揽工汉、煤黑子,他们两人之间简直就是现代的“林妹妹与焦大”,他们的浪漫爱情成了现实的天方夜谭,所以田晓霞就只能被作者安排在一场突发洪水中献身,悲壮地结束他们的爱情之旅。最后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与惠英嫂之间,一步步地走到一起,在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他们的结合符合生活的逻辑。
孙少安的生活也画出了两道圆弧线,由穷得烂包到自办砖厂逐步富裕到破产倒闭,再到重办砖厂再度富裕辉煌,捐资建校又遇妻子癌症突发倒地,再次面临命运的挫折和考验。他的经历反映了农民生存窘迫的真实图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孙少安,敢于承包,自办砖厂,先行富裕起来,但是又极其脆弱,稍有不慎,就遭毁灭性的打击,即使再次站起来,还有生老病死等种种灾难的袭击,所以他们在前行的路上,就必然地会站起,跌倒,再站起,再跌倒,处在一种不尽的破残缺损的圆形运动之中。
再就田润叶来说,她的爱情婚姻之圆,也书写出其命运的辛酸。她与孙少安之间,虽然两小无猜,情深意笃,但由于家庭背景和后来生活道路的差异,又由于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快速结婚,使她吞下了一颗爱情异化的苦果。后又由于她的善良,加之叔父的岳父徐大伯劝导所造成的压力,她只得委曲求全,违心地与她根本就不爱的李向前结婚,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现代女性演绎了一曲现代爱情婚姻悲剧。又由于她本身的道德涵养,在丈夫李向前因苦恼而驾车出事身残后,又主动地回到李向前身边,承担起一个妻子的义务和责任,悲痛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平衡和道德的救赎。她与丈夫由分到合的悲喜剧,既印证了生活中亦分亦合的相互转化,也突出了主人公在生活现实中的无奈和隐痛。路遥作品中的这一幅幅圆形图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人物所处生存环境的苦涩,人物生活道路的艰难。
综上所述,路遥运用对比、反讽和圆形等艺术手法,突出了生活环境的苦难色彩,彰显了人物命运的悲痛特征,深化了整个作品的悲剧美学意蕴。
(责任编辑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