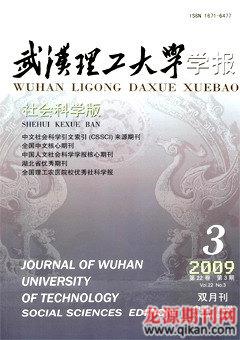毛泽东关于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作用的思想
张俊国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从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和“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的基本国情出发,要求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提出既要明确我们培育什么样人的问题,又要确立我们培育人才的基本原则;既要通过教育达到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辩证关系的目的,又要通过教育鼓励和重视普通劳动人民对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作用。惟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人们在发展生产力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A4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13
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在于向受教育者传授为发展生产力所必须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生产实践经验、劳动操作技能和组织管理才能等,从而为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杰出代表的毛泽东也深谙此中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认为,我国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此,他从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和“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的基本国情出发,要求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他关于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作用的思想。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发展生产力必须把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放在首位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当时“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毛泽东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我国“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在这样的教育状况下,我国发展生产力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为此,毛泽东从我国现有的基本国情出发,要求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除认真做好其它工作之外,还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顺民为己任。至于说这些被培养出来的“人才”到底能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起什么作用以及起多大的作用,那是统治者从来都不关心的事。所以有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总而言之,坏事不少”。毛泽东认为这不能不说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针对此,毛泽东坦然承认“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仅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而且还要求党和政府从今以后必须把“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而这一切的关键均取决于我们对培育什么样人的问题的正确定位。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他看来,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而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或空谈家;与此同时,这样的劳动者和建设者还必须符合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要求。
在德智体几方面中,体育最重要,它是其它几方面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试想一个没有良好身体素质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怎样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呢?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强健的身体,而没有正确的思想道德修养,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动机就会大打折扣,搞不好甚至还会滑到邪路上去。为此,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于是,他提出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著名论断,为我国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有了强健的身体和正确与科学的思想道德修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成为受教育者的刻不容缓的事情了。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毛泽东也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因此,全党上下必须首先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以不断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成为新中国的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了。
二、发展生产力必须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在建国后对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定位十分明确,即新中国的教育主要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为保证这一教育目的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落到实处,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号召。他认为,“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果离开这项基本原则,就会出现许多空谈误国的幻想家,这样的人是既害国又害己,不仅不会对发展生产力带来什么好处,反而还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良性运行。为此,他提出必须要在各级各类学校之中贯彻“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这项原则的基本点应该包括,“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
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原则,其根本动因就在于要达到“改造思想,改变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教育与实际脱节的状况,改变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目的。他认为,能否做到教育和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决实行”。为此,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好工作。
一是必须实行新学制。他对新学制的设想是:“全日制中小学的年限缩短到十年左右,程度提高到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年级。当然,教学改革光有试验还是不够的,还要准备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是:第一,必须提高教师的水平,这就要求对师范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注意组织现有教师的进修。第二,必须把现有的‘二部制学校逐步地分批地变成全日制的,然后再变为寄宿学校,这就要进行基本建设。第三,必须办好幼儿园、托儿所,这就要大大发展幼儿师范学校和训练保育护士的学校。第四,采用录音带、幻灯等新的教育工具,以及充分配备必要的仪器、模型等新式教具。第五,要有充分的纸张供应。”
二是必须对现有的课程设置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认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同时,由于“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所以,他建议:“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对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等做法甚为不满,认为这些“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为此,他不仅要求学校教育必须改革,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努力实践之。
三是必须力争在有条件的学校设立工厂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由于“现在这种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所以,他认为,如果学生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对此,他的看法就是:工科和理科大学,虽然“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想方设法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而文科大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因此,他提倡:“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四是必须使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毛泽东看来,“任何知识分子,不同工农打成一片,不知工厂、农村情形,要指导工农事业,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一方面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另一方面又号召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国人口的85%都在农村,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就不可能单独发展。所以,到农村去工作,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极其光荣的。
三、发展生产力必须摆正“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辩证关系
在传统的社会制度之下,人们从事发展生产力活动的积极性是否能够被调动起来,大多数采取“物质鼓励”的方式。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既要有“物质鼓励”,也要有“精神鼓励”。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或者将其强调得过头了,都会存在变成个人主义的可能与危险,这对调动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极为不利。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这本教科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钱能通神”这点上却很有体系。在苏联人的眼里,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他认为,苏联人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他指出,充斥于整个教科书中的依靠物质刺激就能“使生产增长”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物质刺激不一定每一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只要把道理讲通了,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这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极大多数人,他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却不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要使这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通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因为“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
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对此,他批评苏联“以计件为主、计时为辅”的工资政策是导致“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他要求全党“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他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了党通过“精神鼓励”的方式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一方式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同样能够起很好作用。他指出:“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来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他还结合革命战争年代的体验,强调指出,当时的革命人民“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当时的人民军队能够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他认为,如果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四、发展生产力必须鼓励和重视普通劳动人民的基础作用
毛泽东一生中对普通劳动人民十分关注和同情,而对权贵强势却十分深恶痛绝,更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习俗难以容忍。在早期忧患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毛泽东,形成了十分明显的个人叛逆者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可以说,“在毛泽东的人生字典里,找不到臣服、屈从、退让之类的字眼。毛泽东能够欣赏鲁莽,能够接受无知的粗率,但绝对不能容忍卑躬屈膝、甘受命运摆布,或者主动缴械投降的奴才性格。他的生存意志就是大张旗鼓、不屈不挠地向不公正的旧世界挑战”。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特征,才使得他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高度重视普通劳动人民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有着许多至理的名言。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里的“人民”,主要指的就是广大的普通劳动人民。
另外,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是对普通劳动人民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有加。如他在读书时,不仅不同意教科书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的说法,而且还提出了非常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观点,认为“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他以屈原为例,指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在他看来,“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从历史上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加快车速的技术。你看,这个经验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由此,他认为普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中应该勇于和敢于探索与创新。在实践的探索中,即使发生一些失误,也不必为此停止探索的脚步。因为“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五、结语
今天,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对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与毛泽东所处时代相比已明显地深化了许多,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说我们对教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已经完全由必然走向自由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类社会的认识活动也同样是无止境的缘故。因此,我们在认识和重视教育重要作用和功能的同时,或许还可以从毛泽东关于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作用的思想内涵中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
第一,教育仍然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三个面向”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虽然对教育的作用十分看重,但对教育的战略发展方向并没有清楚指明,这样,用之指导发展生产力的实践就未必能够收到实效。针对此,邓小平在1983年就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命题,并认为“三个面向”之间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还具有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虽然“三个面向”的理念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如何将这一理念和思想落实于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件任重而又道远的事情。不过,无论如何,“三个面向”的教育原则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如一地贯彻之,否则,教育对发展生产力的正面促进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教育仍然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不仅是教育本身的事情,而且也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发展前途的战略方向性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无疑把培养人的目的过多地放在通过“思想改造”和“灵魂深处的革命”以达到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上。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改变人生命运,教育改变人生的发展轨迹的思想及理念虽然已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不少人已从昔日的“政治挂帅”的泥潭走向了“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拜金主义的怪圈之中。如果这样的状况不加以认真地改变,则期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望恐怕就难以早日实现。
第三,教育仍然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深化教育改革应该说是建国以来教育界不断思考着的一项重要课题。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比较具有真知灼见般的见解和思想。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关心学生的睡眠时间和身心健康等。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见解和思想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在实践中被迫中断,甚至走向了愿望的反面。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尽管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触及教育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暴露和被重视起来,但对其解决的效果却往往不太令人满意。如如何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问题,如何做好由应对考试向培养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转变问题等。可以说,这些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以及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怎样,都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教育改革得失成败的判断效应。
(责任编辑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