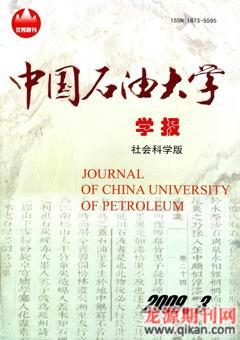道德:“应然”的自由意志
牛俊美
[摘 要] 在黑格尔看来,道德作为“主观意志的法”和“自由意志的内在定在”,本质上是将自身作为他物的远距离反思。因而,只有与内在的善和外在的现存世界相互对待的自我反思着的自由意志才能称之为道德。就其过程而言,道德乃是“向善”和善现实化自身的辩证运动,善及其实现既是道德的“他物”,更是道德的“应当”,亦即道德所希求的目的。这不仅表明道德处于自由意志的“应然”而非“必然”阶段,而且凸显了其向伦理推进的独特内在超越途径。
[关键词] 道德;意志自由;应然;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75-(05)
“自由意志”作为一条精神纽带逻辑地贯穿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而自由理念的自我实现历程囊括了三大有机环节:(1)抽象法:自由意志的外在定在或仅仅自在的自由;(2)道德:自由意志的内在定在或自为的自由;(3)伦理:自由的理念或自在自为的实体自由。其中,作为客观精神发展的第二大领域的道德,是自由意志在人内心中的实现,即“主观意志的法”[1]111。“主观意志的法”既规定和限制了道德的本质是“被设定为与自在地存在的意志自为地同一”[1]110和“尚未被设定为与意志的概念同一”[1]112的主观自由,同时也指明了道德应当否定地对待这一界限从而发展和回归到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质言之,道德的客观性本质是通过其极具主观性的“应然”方式体现出来的,“应然”表明了道德意志与意志的概念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紧张和一定的距离。
一、应然的根源:道德主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
自由意志在道德阶段的进步首先表现在道德的出发点——道德主体上。黑格尔认为,“在抽象法中,意志的人格单单作为人格而存在”,而在道德环节“意志已把人格作为它的对象”,“而把人规定为主体”。主体是抽象法阶段人格的进一步规定,即人作为道德主体。人和主体的区别与联系,体现于“主体”在客观精神领域两种不同的意蕴中:在广义上,主体泛指同绝对精神和无限神性相对待的作为有限存在物的人以及动物个体的“人格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人”相对于这种主体而言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1]110,只有人才具有思维着的精神,反映了“人之异于禽兽”的精神本质,通过而且只有通过这种精神,人才在本质上同动物、同外部自然区别开来;在狭义上,主体特指不仅具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自由意志和行为能力的能思者、能动者,即道德主体。这一意义上的主体说明人的精神本质不在于与自然属性藕断丝连的自由的任意,而在于自我作为主体的自我规定,即“自我的自我规定”[1]17,它体现着“人之贵于禽兽”的自由本质。道德主体与抽象法的人相比,显然处于较高形态。
上述人格与主体的区别在“主体性”意义上也可看作主体性在客观精神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差别。主体性,在“法哲学”领域是相对于客体性、实体性、普遍性而言的精神自身分化和自我运动中主体的、内在的、能动的一面,它与客体性的关系是由相互规定、相互对立而直接同一的进展过程,就是自由理念达到真理、客观精神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同其他概念一样,“主体性”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规定性,而是一种随着自由意志的发展而发展的总体性和过程性的思辨理念。参照自由理念实现的三个阶段,可以将“主体性”细分为法权意义上人格抽象普遍的主体性、道德主体的有限主体性、伦理实体的绝对主体性和具体普遍性即实体性三种发展形态。主体性在道德主体中处于抽象普遍性的主体性推进到否定阶段而又尚未达到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联系环节和展开环节。它形成于前一阶段人格的扬弃和否定,但这个否定是规定的否定和肯定的否定,即是在否定中包含肯定,否定的结果因此不是主体的虚无,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内容充实的新的主体性。
从这个高度反观抽象法阶段的主体性,可以说人格还没有达到主体性,或者说只具有抽象的主体性。主体性在人格环节那里只是一种形式可能性,主体的权能在抽象的人格中只是一种内在的可能性、一种能力,它本身事实上不具任何特殊内容的抽象规定性。故而,“在抽象法中只存在着禁令”[1]47,法权意义上的人格拥有的只是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的自由”,也就是“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1]15的“抽象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自由。严格说来,人格只是无规定性的主体性或抽象规定的主体性,还不具主体性的质的规定。真正的主体性,只有当自由意志的定在从“在外在的东西中”过渡到“在意志本身即某种内在的东西中”[1]109,即自由的理念从抽象法发展到道德领域,才开始真正形成,主体也因而才有可能摆脱其纯粹的抽象性而真正成为现实的存在。因此,道德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材料”,“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1]111。
但是,道德主体的主体性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用黑格尔的原话表达就是,“道德和不道德的一般观点都是成立在意志主观性这一基础之上的”[1]112。“主体性”和“主观性”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替换使用。但在客观精神哲学里,黑格尔把主体规定为精神实体,主体性就是这种精神实体的抽象的能动性。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是由这种精神实体派生出来的。“主体性”不只具有主观性这一方面的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指个体的自主性、反思性、能动性以及自我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行为能力等含义。要言之,“主体性”和“主观性”的异质性就在于主体性高度表征了人的自由本性。因此,从概念上讲,“主体性”和“主观性”不完全对等,“主体性”必然具有主观性,但主观性不一定就是主体性。从“主体性”和“主观性”的这一根本区别可以引申出: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内在性和外在性之分;体现人的自由本质的主体性不可能从它的“直接主观性”中获得价值,而只能从“反思的主观性”即将主体的主观需要和感性自然冲动“客观化”为道德目的和道德意图,在与他人意志“相互间的肯定关系”中实现精神的自我确证。黑格尔说:“意志的活动在于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1]112。追根溯源,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内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矛盾就是道德既自由又不自由的根本原因。
黑格尔在分析道德自由的“自我同一”时指出,主观性和客观性在道德阶段之所以相互关联,是因为它们共构地处于矛盾的双方,是“相互区分的,只是成为矛盾而彼此结合起来”,主观性和客观性在道德主体中相互对待,道德行为的主体即个别人的主观意志只是把普遍意志当作“应然”的东西加以追求,个人意志与客观的、普遍的意志的符合是间接的,通过主观的法这个中介而实现。进而,黑格尔认为,“正是这一点特别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现象方面或有限性。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这些矛盾及其解决的发展,而其解决在道德的领域内只能是相对的”[1]115。普遍意志实现的条件性决定了其在道德阶段仍停留在“应然”而非“必然”的阶段。
二、应然的本质: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他物关系
在“法哲学”中黑格尔对道德的明确表述有这样几种:在道德阶段,“意志的定在是在意志本身即某种内在的东西”[1]109;“道德的观点,从它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1]114;“道德的观点是关系的观点、应然的观点或要求的观点”;“在道德的领域中意志尚与自在地存在的东西相关联,所以它是自我区分的观点”[1]111。综上,道德就是在意志自我区分形成的道德关系中对意志概念及其现实的应然追求,即道德是“应然”的自由意志。所谓“应然”的自由意志,如果仍沿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表达就是:道德意志“被设定为与自在地存在的意志自为地同一”[1]112-113而“尚未被设定为与意志的概念同一”[1]110,但“应当”与意志的概念同一。
首先,道德意志“被设定为与自在地存在的意志自为地同一”是对道德价值合理性的肯定性规定。道德主体的出现使自由概念逻辑地现实展开,自由由此获得了现实的生长点,有了我的特殊目的、我的主观动机之类“关于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动机以及关于故意的问题”[1]112。联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道德的规定——“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2]就可看出,道德的主旨并不是要否定个人对自己利益的感性冲动,而是使人的诸多冲动之间的冲突成为“意志规定的合理体系”。尽管道德与自在的意志的“同一”是自为的,是“我”的内在目的,但它的目的和内容已经具有了客观性的形式,具有“应当”与普遍意志相符合这一客观性的规定。道德主体通过“自我规定的规定”,过渡到自己设定一个规定性来作为内容和对象,使抽象人格在自我展开、自我区别和特殊化自身中从它的内在中获得了实存和现实性,不但使自己主观特殊性的欲望和冲动的“自然”获得了自由的定义,而且达到了主体自身的确证、肯定和发展。这样一来,抽象法阶段无规定性和无区别性的“纯粹主观性”[1]111即完全抽象的自我得以克服而被赋予了内容和客体性。黑格尔说:“在道德的观点上,意志在法的领域中的抽象规定性被克服了”[1]112。道德不但使客观的自由获得了内在普遍性,而且使主观的自由避免了空洞性而获得实在性,从而,“就对自由规定了一个更高的基地”[1]109。
然而,“被设定”却明确无疑地彰显了道德的不自足性和应然性。即,自由意志的这一主观性和实在性环节完全是被意志概念“设定”的存在,主观的道德意志与客观的自由意志在道德领域是相互设定、相互规定的,它们矛盾地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还没有达到双方绝对地和完全地同一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客观性高度。思辨地看,“被设定”的反面——“尚未被设定为与意志的概念同一”就是对道德的否定性规定。它意指道德只是作为自由概念的主观环节而不是概念的全体和真理而存在的,道德只是自由意志的内部状态和内在定在,它作为主体单个人的意志最终实现的只是主体的主观自由和内在必然性。或者说,道德主体的意志行为在“应当”的道德反思中扬弃了法权意义上的“仅仅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即与自在地存在的或普遍的意志直接地、仅仅自在地同一的意志”[1]110的人格的抽象性,达到主体对自身绝对的自我规定之时,同时又陷入了“普遍主观性”即单一性的片面性、主观性、抽象性之中。故此,黑格尔补充说,道德的主观意志与意志概念的符合“仍然是形式的,因之这一符合不过是一种要求,而且它同时含有与概念不相符合的可能性”[1]114,有可能成为主观片面的东西,因此,“这种主观普遍性时而是恶,时而是良心”[1]117。
上述正反两个“设定”是对自由意志在道德阶段的应然性的一般规定。同时,也曲折表达出道德“应当”与意志的概念同一之意。“应当”是在“关系”中的“应当”。而这一关系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就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对立关系。法哲学的总论明确指出,道德作为“与普遍物对立的主观单一性”,与之对立的“普遍物”有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内在的东西,就是善,另一方面作为外在的东西,就是现存世界”[1]41。更进一步讲,道德作为“主观意志的法”和“自我的自我规定”,在本质上是将自身作为他物的远距离反思。因而,相对于自身这个他物来说,无论是内在的善还是外在的现存世界,都是与道德意志相互对待的外在他物。善和现存世界作为道德的对立面,亦即设定和限制道德的“他物”,与道德处于相互外在、彼此对立的矛盾关系之中。这样,我们可以从中析出道德领域的两对他物关系:其一,主观道德意志与“概念这种实体性的东西”即善的他物关系;其二,道德意志与“外部定在的东西”[1]113即现存世界的他物关系。善及其实现既是道德的“他物”,更是道德的“应当”,也就是道德所指向的目的。
因此,道德的“他物”之于道德具有双重意义,对道德的限制以及对这一限制的超越:
其一,在他物关系视阈下,置于上述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是被“他物”规定为“他物”的有限“他物”。一方面,只有处于与外在的现存世界和内在的善相互区分中的自我反思的自由意志才能称之为道德;另一方面,普遍物也只有作为单一性的非有、否定、自在存在的规定性才能称其为道德的普遍物。这揭露了道德仍停留在“尚未与意志概念同一”的应然阶段和道德阶段“抽象的只是应然的善”和“同样抽象的应是善的主观性”[1]161的有限性本性。
其二,他物关系又意味道德本质上应当否定地对待这一界限,超出限制。事实上,当主体的意志与普遍物对立起来时,也就同时使之发生了相互关系:两者互为界限,谁也离不开谁。外在对立性中的不可分离性显示了单一物和普遍物的内在联系。黑格尔自己说得好:“某物在被规定为限制之时,就已经超出了限制。因为一种规定性、界限,只是在与它的一般他物,即它的不受限制之物对立时,才被规定为限制,一个限制的他物正是超出了限制的东西”[3]。
所以,就其过程而言,道德就是“善以它的现实性为对立面,主观性以善为对立面”的辩证运动。一方面,道德就是单一性扬弃自身的有限性而恢复自己无限本性的“向善”运动。道德通过反思扬弃了自然欲望和感性冲动与善的对立,在自己本身内达到了普遍性,尽管这种普遍性是主观的,是“普遍主观性”;另一方面,道德也是普遍物扬弃自身的彼岸性而回到自身的辩证运动,即善现实化、特殊化自身的运动。由此,善不再是彼岸的定在或自在存在,不再是只能敬畏但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是内容充实的、“被实现了的自由”。当然,“主观意志跟它的概念的同一化”的这两种反向运动在道德领域并不能完全实现,即只是抽象的“应然的善和同样抽象的应是善的主观性”[1]161,而“原在道德中的应然在伦理的领域中才能达到”[1]113。
三、应然的局限性:“应然的善”和“应是善的主观性”
在他物关系的分析框架下,黑格尔对道德的应然本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而这一分析过程,同时也是黑格尔对康德的道德哲学展开批判的过程。因此,本文将在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评论中对作为“应然”的自由意志的道德的主要缺陷作一概述。
黑格尔首先肯定了康德的自由观“着重指出纯粹的不受制约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并把它作为义务的根源”和意志“只是通过它的无限自主的思想,才获得巩固的根据和出发点”[1]137的合理性,并点明康德的道德律和绝对善在实践理性中由经验的自然界向超验的道德世界过渡的积极意义:善,“作为通过特殊意志而成为现实的必然性以及同时作为特殊意志的实体”[1]132,是“特殊意志的真理”,是主观意志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由于主观意志对善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即善对主观意志说应该是实体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主观意志应以善为目的并使之全部实现,至于从善的方面说,善也只有以主观意志为中介,才进入现实”[1]133。因此绝对善具有实体性、本质性和普遍性。但是,与其说上述是黑格尔对康德的赞肯,毋宁说是在为批判康德夯实基础。以下三个方面是黑格尔对康德自由理论的批判的主要方面,亦是应然的道德其局限性的表现:
其一,抽象性。善在道德的他物关系中作为单一物的否定或他物,是与主观意志各自对立、彼此分离、相互外在的对立面,因此就只能是与单一物和现存世界相对立的无规定的虚空、空洞的自在存在、现实定在的自在存在。“善作为普遍物是抽象的,而作为抽象的东西就无法实现”[1]132-133。鉴于这一对立关系,“即使人们在主观意志中被设定了善,但这并不就是实行”[1]113。因而,与主观意志和现存世界互为他物的善就是缺乏现实性的“应然的善”。
其二,主观性。从善的“内部的规定活动”[1]133——良心方面来说,黑格尔指出,虽然良心是自由意志的内在定在,是善的内部的绝对的自我确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善的抽象空洞性,使善变成了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然而,仅仅停留在自身中的反思虽然是主体性的,但同时也是主观性的。黑格尔认为,良心的“这一主观性作为抽象的自我规定和纯粹的自我确信,在自身中把权利、义务和定在等一切规定性都蒸发了”[1]141,普遍物在此对主体来说乃是一种无任何特定内容的形式要求,即“应当为义务而尽义务”[1]136。这种纯粹的义务同良心一样,它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特殊内容,“完全缺乏层次”。“义务所保留的只是抽象普遍性,而它以之作为它的规定的是无内容的同一,或抽象的肯定的东西,即无规定的东西”[1]137,其判断方式也是诉诸不矛盾律和形式上的自我一致。良心和义务的自律性使主观自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但当它将一切感性内容作为他律和特殊的东西加以否定的时候,其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就使之陷入空洞的可能性,康德的自由意志本身也仅仅只是一个内容空洞的、缺乏现实性的逻辑上的“应当”。
其三,或然性。善的具体化和特殊化的良心本身不但具有“抽象性状”,而且依然保有特殊性的因素。黑格尔认为,善是主体的目的,它从理想上规定了主体的行为,“应当”从而成为主体的行动指南。但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除了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外,还是一个天生受外在的必然规律如自然因果律的自然冲动和感性欲望所刺激的存在者。因此,纵使主体从“汩没”于自然进展到了“反思”自然的自由意识,但其主体性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道德与自然的对立性决定了他在根本上无法逃逸与自然任性的必然联系。黑格尔进而警告道:“当自我意识把其他一切有效的规定都贬低为空虚,而把自己贬低为意志的纯内在性时,它就有可能或者把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作为它的原则,或者把任性即自己的特殊性提升到普遍物之上,而把这个作为它的原则,并通过行为来实现它,即有可能为非作歹”。当主体单在自己内部寻找善恶的判断标准时,善的实现就成了或然的,既有可能实现,更有可能沦为伪善的借口和作恶的工具。所以黑格尔说:“良心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道德和恶两者都在独立存在以及独自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共同根源”[1]142-143。
如此,道德只是“应然”的自由意志,即“应然的善”和“应是善的主观性”。道德所实现的仅仅是存在于主体单个意志内部的特殊的善,善的定在只是不具任何特殊内容的形式的良心,人的自由本质在此阶段还没有得以充分实现,其实质只是个别人的主观自由,还不是普遍的、客观的自由。而要实现善和良心在道德阶段的内在缺陷的超越,诚如黑格尔所言:“原在道德中的应然在伦理领域中才能达到”[1]113。
在上述诸多的局限中,道德可能面对的最大诘难之一就是:既然主观意志是普遍意志实现的中介,而“道德的意志是他人所不能过问的”,而一旦主体不敬畏和不服膺道德,那么即使主体存在,道德的价值合理性又从何而来?面对这一辩难,黑格尔纠正了传统道德哲学将道德和伦理混为一谈的方法,强调“道德的观点和伦理的观点是有分别的”[1]140-141,伦理高于道德,自由意志在伦理阶段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以充分的实现,因此是跨越了应然和实然的鸿沟,克服了“应当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主观空洞性而达到了单一物和普遍物、主客现实统一的真理性存在,是具体的普遍性、“意志规定的合理体系”和“自由的理念”,是抽象法和道德的真理。“无论法的东西还是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而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因为法欠缺主观性的环节,而道德则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所以法和道德本身都缺乏现实性。只有无限的东西即理念,才是现实的”。真正无限的东西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指的就是伦理,即“主观性和法的真理”和“自由的理念”[1]162-164。这就是说,伦理因主观性和客观性、权利和义务、应然和必然的真正统一而实现了对道德的超越。只有在伦理领域,特别是在其最高阶段——国家中,自由意志才最充分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本质,而且,也只有伦理实体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因此,道德必然要扬弃自身,向伦理过渡。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24.
[3] 黑格尔.逻辑学:上册[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31.
[责任编辑:陈可阔]
Morality: the "Ought to Be" Free Will
NIU Jun-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Hegel, moral, in which "the single and the common" are interdependent and opposite to each other, is regarded as the self-distinguishment of subjective will. Moreover,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free will is of dual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to morality: restric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other words, the one-another relationship not only decides moral being in the being-for-self stage of free will concept, but also manifests its intrinsic transcendence approach to advance to ethics.
Key words: morality; free will; ought to; et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