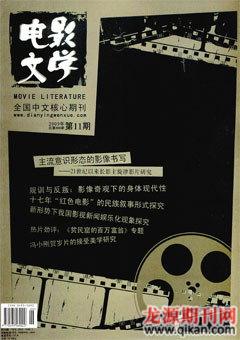“民族寓言”与“政治神话”
余爱春
[摘要]可以说,《芙蓉镇》是谢晋电影中的巅峰之作。在影片中,导演充分调动多种电影语言、手法和技巧,透过历史和现实的表层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核,从民族文化根性和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历史进行重写,建构起幻觉化的“民族寓言”和“政治神话”。
[关键词]《芙蓉镇》;意识形态;政治神话
在谢晋导演生涯中,《芙蓉镇》是让谢晋获得巨大声誉和产生深刻反响的一部影片,是谢晋电影中的巅峰之作。影片很好地秉承谢晋电影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给观众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审美愉悦的特点,充分调动多种电影语言、手法和技巧,透过历史和现实的表层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核,从民族文化根性和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历史进行重写,建构起幻觉化的“民族寓言”和“政治神话”。
一
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常常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实的社会主题契合统一。谢晋就说:“一个比较重大的作品,总归是要跟国家的命运、时代特征、人民关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与以往那些专注于表现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夺权斗争不同,《芙蓉镇》不再拘泥于政治斗争本身的展现与渲染,而是从女主人公“芙蓉仙子”胡玉音的人生遭际和坎坷命运入手,通过恶劣政治环境中人性的摧残、异化与扭曲和多元对立的影像奇观,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状况,在人道主义立场和时代的高度对这段“荒诞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拷问,再造了这段民族苦难历史。
如果说十七年、“文革”时期影片主要表现为简单的阶级对立、敌我对立关系的话,那么,《芙蓉镇》则表现出对立关系的多元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阶级的对立、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又有善与恶、压迫与被压迫等的对立。胡玉音和李国香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她们之间的对立关系成为贯穿全片的主要线索,影片围绕着她们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结构。胡玉音是一个美丽大方、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与丈夫每天起早贪黑、拼命苦干,逐渐摆脱贫困过上了比较富裕生活,成为芙蓉镇勤劳致富的代表;然而,历史和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在于,正是她那合情合理的“勤劳致富”,“四清运动”的到来使她成为批判的对象,被划为“新富农”,导致家破夫亡,受尽十多年凌辱与折磨,甚至连最起码的爱的权利也被剥夺;影片不止于对胡玉音外在的人生悲剧的展示,还深刻揭示出她对悲剧根源的麻木与无知,在她看来她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不是由于极“左”政治运动而是“右派分子”秦书田所致;可见,胡玉音的悲剧既是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更是民族文化的悲剧。与胡玉音的悲剧处境不同,作为政治运动健将的李国香,依靠县委书记舅舅关系步步升迁,由国营饭店的经理一工作组组长一公社主任一县革委会常委,成为芙蓉镇实际上的领导者和政治运动的发起者,她没有女性应有的温柔,有的只是铁的政治。她借革命的名义对无力抗争者任意践踏和伤害,对欲望挑战者疯狂报复,她实际上是一个被极“左”路线桎梏和扭曲了心灵的悲剧人物。特别是她被红卫兵批斗时坚持不与所谓的阶级敌人“黑五类”站在一起,无不弥漫着极“左”路线的阴影,显得荒诞而悲哀,引起我们对“文革”的深沉反思。
与胡玉音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人物是“土改根子”王秋赦,如果说胡玉音被划为“新富农”和“黑五类”显示了极左运动不合理和荒谬性的话,那么王秋赦成为芙蓉镇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新的领导者就进一步凸显了“文革”的荒诞和民族文化中先天的劣根性。王秋赦是一个懒惰成性的流氓无产者,他每天怀揣着观音像在“白日梦”里生活,他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改变贫穷现状,而祈求于政治运动,正是这样的人物反而成了极“左”政治运动的“中坚”,成了芙蓉镇百姓热烈欢迎的“公社书记”;“文革”结束后,发疯的王秋赦仍然敲着破锣“运动啰”的叫喊,无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在王秋赦身上不仅形象地展示了那个年代“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荒谬逻辑和政治运动对人心灵的毒害与异化,而且也让我们认识到了那个时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民族文化的痼疾所在。《芙蓉镇》正是通过人物的悲惨命运和人性的扭曲对极左政治运动进行了透入骨髓的批判,并引导我们对社会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进而汇成一股渴求变革现实的舆论与氛围。
与此同时,对立反差的情境画面和无所不在的援助者也实现着《芙蓉镇》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与传达。影片开头就呈现了一组对立的画面,胡玉音米豆腐摊前热闹繁忙和谐景象与国营饭店冷落清静无聊形成强烈的对照,这虽然有夸张和渲染成分(因为在1963年的农村不可能如此),但导演正是运用这种夸张来强化“大锅饭”和国有经济模式的弊端,暗示小私有经济、自由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也正因如此,影片结尾时再一次呈现米豆腐摊前热闹景观,这既是对前段荒诞历史的否定,也是对新政策和前景的肯定与展望。以及影片中“黑五类”秦书田和胡玉音真心相爱而被判刑坐牢,而李国香与王秋赦偷鸡摸狗的奸情却堂而皇之;胡玉音被划为“新富农”前后的人情反差等等对立反差的情境,无不对缺乏人道的极“左”运动予以了有力的批判与反讽。同时,《芙蓉镇》与谢晋的其他影片一样,影片中有一个正义的化身、党的化身的“援助者”来帮助主人公价值的实现。但又与《红色娘子军》《春苗》《天云山传奇》等影片无限神化或夸大个别帮助者不完全相同,《芙蓉镇》所夸大的既是个别扮演者,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缺席者即改革开放的社会。影片中对胡玉音始终给予帮助的有两个具体的人,一个是正义的化身、党的化身的谷燕山,一个是知识化身的秦书田;而最终使胡玉音等人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利,使芙蓉镇又恢复昔日繁荣景象的,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新社会。这种对极“左”政治运动的批判,对改革开放新社会的充分肯定,无不隐含着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二
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载体,不仅反映和再生产着特定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再现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引导观众在想象中认同并接受其传达的意识形态。郝大铮曾指出:
“电影语言就是电影意识形态范畴中的一种话语因素。电影生产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行为,电影生产通过用什么语言和如何使用语言传递意识形态信息,表明电影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芙蓉镇》中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使观众在想象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感,导演充分调动各种煽情的叙事手段和电影语言。为了使观众不至于对意识形态的传达产生反感情绪,影片并没有对极左政治运动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而是以1963、1966、1979等时间概念把“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历次政治运动作为人物生存的现实背景表现出来,并把笔墨重点投射人物命运、思想、情感和心理冲突上。同时,为了突出影片的悲剧效果,大量运用长镜头铺垫和渲
染气氛。为了突出胡玉音夫妇勤劳致富那场戏,影片在序幕和开头两次使用三分多钟的长镜头对他们起早贪黑卖米豆腐和拼命苦干建新屋进行了渲染铺垫,这样就为后面胡玉音悲剧命运的不合理、不合法性找到支撑,从而使观众产生同情心和悲愤感,在充分认识到极“左”政治运动的荒诞与错误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予以了否定。不仅如此,影片还借助独特的电影语言来反思历史,反思政治运动给社会和人性刻下的伤痛。影片对色彩的运用很有特色,通篇都是那种阴郁的青灰底色,特别是胡玉音知道丈夫去世后独自去坟地的那场戏,不仅使用五分多钟的长镜头,而且始终以灰暗的色调和哀戚的民歌小调贯穿始终,这种凝重、压抑、阴冷的青灰色色调与哀怨、凄凉民歌曲调相附和,把胡玉音失去丈夫之后伤心欲绝、悲痛凄楚和孤独无助衬托出来,既凸显了人物命运的悲惨,强化了影片的悲剧色彩,又加强了影片的政治批判力度,取得了独特的煽情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长镜头和青灰色色调为影片烘托出阴郁悲剧底色的话,那么,闪回镜头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影片产生强烈的差势效果,有效地传递了意识形态信息。影片中多次运用闪回镜头,增强了电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胡玉音被划成“新富农”后思念丈夫那场戏,首先用一个特写镜头突出神情木然的胡玉音,惨淡的青灰色月光映照着她那呆滞可怖的脸,接下来就用充满温暖调子的闪回镜头把胡玉音和丈夫桂桂由相识一恋爱一结婚的幸福时光展现出来,这一悲一喜、一冷一暖的强烈对比,既映衬出胡玉音极度的痛苦、悲哀与孤寂,又折射出极“左”路线与人性、人道的背离。又如谷燕山醉酒后风雪归途那场戏,蒙冤受屈的谷燕山,喝得酩酊大醉踉跄在漫天飞雪清冷无边的夜色中,此时插进一组火红的战斗生活画面,这种冷暧对照闪回镜头,构成一幅凄清悲怆、催人泪下的油画,从而对荒诞的政治运动进行了有力的反讽。同时,象征性镜头的运用也大大深化了影片的主题。石磨和锣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石磨的“使用一废弃一偶尔使用一使用”,既是胡玉音悲剧命运的形象表达,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象征性演绎;而锣由最初的“完好”到结尾的“破旧”,既折射出政治运动的频繁又暗示了政治运动已经“破”了。而最具有象征意蕴要数那座建立在水上破败脏乱的吊脚危楼,它不但是懒汉无赖王秋赦的“狗窝”,是培育民族惰性的温床;而且也是芙蓉镇“四清”“文革”运动的策源地,而“建在水上”本身就说明了历次运动脱离实际,得不到大众支持,暗含了政治运动的荒谬和错误,最后危楼的倒塌,既象征着“四人帮”的倒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荒谬历史的结束,也寄寓导演改造和重建民族文化的美好愿望。可见,影片正是通过独特的电影语言的运用传达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进行批判反思的。
总而言之,《芙蓉镇》可以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形象化解说。影片以直面现实的手法和影像奇观,再现了那段荒谬凄怆的历史,对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深刻的反思,对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予以了审视与追问,获得了独特的政治美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成为“谢晋电影模式”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