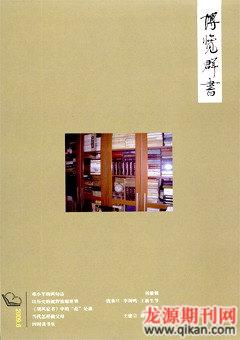解读《花间集序》
杨 明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词总集《花间集》,所收颇有上乘之作,但因大多描绘女性或写男女之情,且其女子多为倡条冶叶,故曾被笼统地加以否定。那是特定的时代风气使然,正如南朝宫体诗曾被一笔抹杀一样。近十多年来,大陆和台湾都有学者对那种做法予以批评。同时,学者们对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也重新加以审视。由于解读不同,观点分歧颇大。这里略抒己见。
这篇序文可分成两段。第一段从开头至“用助娇娆之态”,大意说:自古以来,都以绮靡清丽的歌辞,配上动听的曲调,让歌妓们在酒席间歌唱以供娱乐。这可说是援古以证今,标榜《花间集》之编辑符合传统,为下文所说“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作铺垫。此种以古证今的写法,原是文家惯技。第二段说,唐代以来这种歌唱的风气十分普遍,而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撰写歌词,其作品的水平远胜于旧时所用(即南朝宫体诗及民间受其影响而作的歌词),《花间集》就是精心编选的近时文士之作。此段开头“自南朝之宫体”四句,批评旧时作品,是为了反衬唐代,尤其是唐末五代词作(亦即《花间集》中所收)之高卓。有的学者将四句置于第一段末,恐怕未妥。
序文似是依时代顺序写来,于是有学者认为欧阳炯以史为经,叙述了歌词发展的轨迹;认为欧阳炯首次进行了关于词的历史的探索。此种解读,似乎新颖,实未必然。序中提到远古时西王母唱《白云谣》,郢中歌《白雪》,以及《列子》所说“响遏行云”的典故,不过是借古代故事以表明动人的歌唱由来已久而已,哪里是认真地述说歌词发展的历史?接着说到“杨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那是指南朝《吴声》、《西曲》之类。《诗三百》和汉魏乐府,在歌曲历史上十分重要,但欧阳炯都跳过不提。若真是有意述说历史,那是不会如此忽略的。
有的学者认为“杨柳大堤”、“芙蓉曲渚”中包括汉晋歌词,那是误读。下面略作辨析。
杨柳:汉代李延年所造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此外古乐府有《小折杨柳》,相和歌有《折杨柳行》(见《乐府诗集》卷二十二《折杨柳》题解),古辞均久已不传。晋宋时官家音乐机构的曲目虽还有《折杨柳行》,但仅取其曲调而已,所用歌辞的内容与杨柳毫不相干。(《宋书·乐志三》载西晋荀勖整理的清商三调歌诗中有《折杨柳行》,歌辞为曹丕所作《西山》及古词《默默》。又《乐府诗集》卷三十七《折杨柳行》题解引《古今乐录》,云宋齐间王僧虔所著《技录》中《折杨柳行》歌此二篇。按《西山》言求仙,《默默》咏史,均与杨柳略无关涉。知其歌咏杨柳之古辞久已失传。)又南朝梁鼓角横吹曲有《折杨柳歌》、《折杨柳枝歌》,曲调、歌辞均来自北国。又《西曲》有《月节折杨柳》十三首,自正月至闰月,都是五言五旬,而在第三句下有“折杨柳”三字,其实是歌唱时的和声。其歌辞内容,乃男女相思欢爱之意。如二月歌:“翩翩乌入乡,道逢双飞燕。劳君看三阳,折杨柳,寄言语侬欢,寻还不复久。”以上是汉魏六朝时代有“杨柳”字样的歌曲名称。欧阳炯所说“杨柳”指的是哪一种呢?他既然说“杨柳大堤之句”,自以指《西曲》的可能性为大,因为这里“杨柳”和“大堤”并提,应具有相关性,而“大堤”即见于《西曲》中的《襄阳乐》,萧纲因之有《大堤》曲之作(为《雍州》十曲之一)。当然,欧阳炯这里不过为骈文行文的需要,故将“杨柳”、“大堤”并列,我们不必太过拘泥,甚至不理解成曲名,而解为歌辞中字眼亦可。(应该是常见的字眼;若只是偶一出现,那就不具有代表性,恐怕欧阳炯不会那样行文。)但总之理解为《西曲》,或理解为南朝乐歌中的语词,是最为融洽的。
芙蓉:《吴声》、《西曲》歌辞中言“芙蓉”者非常之多,几乎可说是南朝乐府的一个显眼的特点。或比拟女子之美丽,或在所谓“风人体”中引出“莲(怜)”字。(参王运熙先生《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原载《六朝乐府与民歌》,后收入《乐府诗述论》)芙蓉即莲花,南朝乐歌中咏采莲者也甚多。欧阳炯所举“芙蓉”,也应是就南朝乐歌而言。华钟彦先生《花间集注》举《古诗十九首》之“涉江采芙蓉”,恐未确。虽然今人考证以为古诗来自乐府,但古人多不将古诗视为歌辞。且此处所用事典应具有代表性,汉代歌诗中“芙蓉”极少见,举一条偶然出现的“涉江采芙蓉”以当之,亦觉未惬。
曲渚:《吴声》、《西曲》产自长江流域,水乡自多洲渚,歌辞中亦有“后渚”、“兰渚”、“桂兰渚”、“水渚”之类语词。梁武帝所作《江南弄·采莲曲》的和声,便是“采莲渚,窈窕舞佳人”。(见《乐府诗集》卷五十《采莲曲》题解引《古今乐录》)萧纲《雍州》十曲中则有《北渚》一曲。欧阳炯言“曲渚”,当指此类,“曲渚”与“大堤”语相对偶。《花间集注》以何逊《送韦司马别》“送别临曲渚”之句当之,亦似不确。何氏此诗,未闻曾入乐歌唱。
欧阳炯举出杨柳大堤、荚蓉曲渚为言,既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词语使人想起《吴声》、《西曲》,又描画出美丽的风景画面,很有水乡情调。而且偶对工整,声韵和谐,其文字技巧是很高明的。
从以上辨析,可知笼统地将此段文字说成是述汉魏六朝乐歌,又从而认作是回顾词史,其实是不确的。
欧阳炯这样行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是忽略了《诗三再》和汉魏乐府,而属意于南朝乐歌。这不是偶然的。南朝乐歌的歌辞,多描绘女性,歌唱男女之情,风格清丽婉转。因此这里实际上反映了词为艳科的情趣、观念。从“唱云谣”至此,虽然从远古说起,看似依时代顺序行文,却并非回顾词史,而是为《花间集》张目。
序文中又一费解之处,是“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四句如何解释。这是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这四句当然是对梁陈宫体以及倡女歌妓的歌唱持批评态度,问题在于批评的是什么。“言之不文”,主要是针对那些流行的歌辞,认为那些歌辞不够精致、文雅。此点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秀而不实”则较难理解,意见分歧。有的学者说是批判梁陈宫体浮华虚美,内容空洞,是批判宫体之冶荡淫靡,甚至认为这一批判继承了自居易《与元九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实在令人难以首肯。序文中明明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纤纤之玉指”“用助娇娆之态”,又说“香径春风,宁寻越艳”、“红楼夜月,自锁嫦娥”云云,而且都是以正面肯定的态度说的,怎么会是反对香艳呢?《花间集》中所收,固然有逸出女性题材之外者,但毕竟以刻画女性美丽、抒写男女之情为大多数,与宫体诗并无根本区别。有的学者强调《花间》词写女性,感情真挚,具有同情态度,故不同于南朝宫体。但那也只是一部分作品如此,纯以欣赏态度刻画女子之美艳的,为数正不在少,甚至也有描写床笫衽席之间者,这与宫体并无不同。更重要的是,强调某些作品感情真挚、同情女性,那是今人的认识;欧阳炯已能将抒发真挚爱
情和玩赏女性二者区别开来,并且抑此而扬彼吗?他已具有歌颂深挚男女之情而鄙视、批判冶荡之作的自觉意识吗?试看《花间集》所收他本人的作品,如《南乡子》之“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环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描绘倚门卖笑者的美艳,纯是一种玩赏的态度。至于《浣溪沙》之“幽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更何其冶荡。他怎么会在序里批判南朝宫体之玩赏女性呢?
那么“秀而不实”究竟作何解释?幸而欧阳炯在《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中用过类似的说法,可供玩索。其言日:“六法之内,唯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文载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盖以气韵乃内在之生命,故为质为实;形似系内质之外现,故为文为华。无形似则觉其技巧拙劣,即“文”的方面有缺;无气韵则如剪纸刻花,显得不真切实在,即“质”的方面不足。我们揣测其思维逻辑如此。《花间集序》的“秀而不实”,也就是“华而不实”。(《广韵·宥》:“秀,荣也。”荣即华、花。《论语·子罕》“苗而不秀”朱熹注:“吐华日秀。”)欧阳炯之意,盖谓宫体之类所描画者,有如土木偶人而不生动,不真切。我们试将梁陈宫体之作与《花间》词对照,则《花间》之栩栩欲活、如在目前,确是远胜于宫体。论者或谓《花间》之作能表现女子之心理、情感,这一优点,自亦为欧阳炯所体认。但他并非如今人那样从同情妇女之类思想性的角度加以比较、评价,而是从艺术表现的角度出发。总之,《花间集序》的批评宫体、娼风,绝非批判其描画女性冶荡香艳。毋宁说《花间集》中作品,其主流部分恰是继承宫体,而后来居上,艺术成就更高。这样说并不否认《花间集》描写女性之作在思想性方面也有胜过宫体处,只是说欧阳炯并未如今人那样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同时,梁陈宫体也自有可取之处,并非都是轻佻色情。如果为了强调《花间集序》对宫体的批判,强调二者的对立,遂将之笼统指为冶荡淫靡,也是失实而不公平的。
附:《花间集序》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荚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竟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甘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