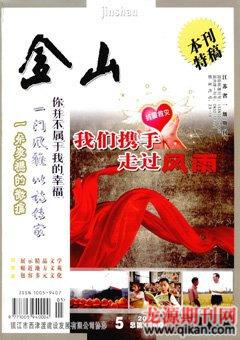我是村长的爹!
纯 芦
“哗啦”,随着刺耳的声响,我翻身坐了起来,捅一下老伴儿。随即我们就明白了:我家又被砸了玻璃,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抬手去开灯,不亮,肯定是电线被掐断了。
姥姥的!我骂了一声,起身要下床,老伴儿一把拉住我,掐了我一下说,别出去,等天明吧。我说有啥害怕的,你看咱家这窗户门,就是八国联军也进不来。老伴儿说,还是等天明大宝来了再说吧。
姥姥的!我又骂了一句,别跟我提这个畜生!老伴儿又掐我一下,我忙改口骂,奶奶的,大宝这个畜生。
大宝是村长,我是他爹。
老伴儿拽着我不撒手,我只好又躺下来。老两口儿四只眼睛瞅着房顶,说话。
说我们的儿子大宝是如何的众望所归,以全村百分之九十的票数当选了村长这个干部;说我们的儿子大宝是如何的信誓旦旦,高举拳头说就是玩了命也要让村里人都奔小康;说我们的儿子大宝是如何的大义灭亲,把两次偷村里变压器的堂弟坏三儿送进了派出所;说我们的儿子大宝是如何的勇敢机智,迫使三年没有上交果园承包费的三大肚子补齐了欠款;说我们的儿子大宝是如何的不畏强权,顶住压力撤换了带头偷电的电工,就是那个乡长的小舅子二吧唧的职务;还说我们老两口子拉扯儿子大宝和他三个姐姐的不易……我和老伴儿都觉得,像我这样六十六岁的人了,应该到了享清福的时候了。
最后我说,都说六十六吃块肉,我看我他娘的没肉吃!
天就亮了。老伴儿说,你去把大宝找来,这村长咱不干了,要不非让人给吓死不可。
我说你先做饭,我去找那个畜生。
走到外屋门口,我拉过那条特意买来拴狗用的大铁链子,打开那把大铁锁,又打开小链子上的一把小号的铁锁,推开用钢金铸成的防盗门,走到院子里,抬头看了一下墙头上面的电线,断了。不用问,准是三大肚子那伙人儿干的。
我又看了一眼两边的铁窗和中间的铁门,不由得鼻子发酸。
院门上有一张纸条,歪歪斜斜的几个烂字:大宝,你小子小心點!落款是:你爹。
姥姥的!我又骂了句,我才是大宝他爹。回头看了一眼院里,老伴儿没有在。我倒背着手,向大宝家走去。
儿媳妇正在做饭,问爹有事儿呀?我说我找大宝。
儿媳妇说他一宿没有回家,快麦收了,领着人儿修那两眼机井呢。
我回头到地里去找,修机井的人说大宝刚走,村里新买了两台收割机,他被人喊去了。
我又走回村里,人家说村长刚走,村西头的三奶奶老了,他去帮忙了。姥姥的,瞎子不叫瞎子——忙(盲)人儿呢还!
没找到儿子大宝,只好回家。回到家,我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就像是耕了半天地的老驴,呼哧带喘的,唉!老了。我跟老伴儿说,一会儿吃完饭我去集上买肉,你做点儿好吃的,晌午把大宝叫过来。我又说,今儿晚咱睡觉不上锁了,大门就敞开着。
老伴问为什么。我说,姥姥的!不,奶奶的……我是村长的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