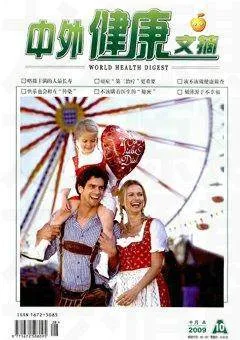换一种坐标去生活
于 丹
我感觉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坐标,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惯性。
去年9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那里的草原水草丰美,雪白的树干,金黄的叶子,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有碧蓝碧蓝的大河穿过去,非常震撼。
我们开着一辆三菱越野车,按说可以呼啸草原,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但是,我们开得不是很快,经常刹车。为什么呢?就是有牛啊、羊啊,有时候一群一群的,有时候三三两两的,有的时候它们在聊天,有的时候就停在那儿不走了,这时候我们的车就只能停下来了,等到它们晃晃悠悠地离开了,我们的车再过去。
我看着牛羊的时候,就觉得它们的身体跟水草、河流之间有一种默契,而且是非常默契。我觉得它们就应该如此从容。这是它的地盘。它是主人。一辆外面闯进来的大车显然是一个侵犯者,你没有理由催它,也没有理由烦它,这个时候你是卑微的,你只能以一种谦卑之心,等着它,静静地侧道而过。
在北京堵车的时候,二环路、三环路,跟停车场似的,狂按喇叭,骂骂咧咧的,还站起来指着前面骂。那个时候我们很嚣张、很猖狂,我们觉得被人占用了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团队,都在一个繁忙的城市讨生活,谁被耽误一点时间火气就大得很。但是,在一片安静的草原上,像呼伦贝尔草原,为什么你面对牛羊会宁静下来?因为你换了一种坐标,你是以牛羊的方式在自然里面完成一种唤醒。
我觉得在呼伦贝尔草原那几天特别高兴,我经常在地上打滚,经常趴在地上,然后闻青草的味道。后来我觉得,有一种学习,就是人回到一种本初、朴素、天真的状态去学习,学习牛羊热爱青草,学习溪水流过大地时候的亲近,学习每一个春天都有花开、每一个冬天都有雪花飘下来——去学习在最本初、原始的状态下,在那个坐标体系下看见自己。
我觉得,人在一些改变了坐标的地方,判断方式也是会变的。有一次在云南丽江,那天晚上,我们在四方街上逛小店,之后着急去看音乐会。当时陪我的是丽江电视台的台长,这个小伙子是农科大学毕业的,他早已习惯了都市的紧张节奏。我们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有三个胖胖的纳西族老太太,把路堵死了。她们特胖、走得特慢,她们三个人晃过来、晃过去,我们怎么借道都过不去。小伙子就过去用纳西语和她们打了几句招呼,意思就是借个道。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笑眯眯地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话,然后小伙子就“啊”了一声,站在那儿了,老太太就接着走了。他说,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原来老太太说的是:小伙子,咱们所有人从生下来就往同一个地方走,早去也是去,晚去也是去,既然都是去,干吗不慢慢走啊。
今天我们都在说文化,像北京这样的首都,还有我们的广州、上海,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的大都市,但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唯一的坐标却是狭隘的、社会的。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习惯于在使用价值上做判定。但是换一种坐标呢?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向牛羊学习还是像仙女一样静默地给自己一小时,其实都是在转换生命坐标,是在新的坐标里面给自己一种生命保鲜的理由。
(纳水摘自《时文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