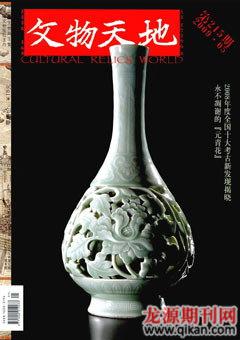中国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五)
杨伯达
第三章明古玉辨伪——文献的考察
二、《遵生八笺》
——晚明养生怡性鉴赏清玩的百科全书
我们了解明代伪古玉的碾琢情况,主要通过高濂《遵生八笺》中的有关文字。高濂,字深甫,别号瑞南道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明万历初年尚在世,生平亦无考。高氏少婴赢疾,复苦聩眼,有“忧生之嗟”,故又“癖善谈医”。明著名戏曲家屠隆称其“家世藏书,博学宏通,鉴裁玄朗”。高氏为明诗人、戏曲家,工乐府,“雅好古”,广为收罗,又是一精明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著有南曲《玉簪记》《节孝记》及诗文集《雅尚斋诗草》。《遵生八笺》为其杂著。
《遵生八笺》是高氏一生向疾病抗争的延年之术、却病之方的成功总结,“其内容之全面、资料之丰富、知识之广博、议论之详审,在同类著述中实为罕见”(《遵生八笺》出版说明,巴蜀出版社,1988年)。全书共十九卷,五十余万字,分为八章(笺),将赏鉴清玩作为养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来论述的是第五章,即《燕闲清赏笺》。该笺记录了他闲时鉴赏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的心得体会及“真知确见”,并辨证器物之是非。其《论古玉器》文字不长,约1400余字,但其内容十分丰富,分别论述玉材、玉器品种、汉宋古玉、吴中伪玉及水石等若干细节,是我们研究明代伪古玉的极为重要的依据,十分宝贵,值得当今的收藏家、古玉研究家们一读。现分为玉材、玉器、汉玉、宋玉、伪古玉等十个部分略作介绍,以供参考。

1、玉材似多
“今时玉材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块劈爿玉料,谓之山材,从山石中锤击取用,原非于阗昆冈西流砂水中天生玉子。色白质干,内多绺裂,俗名江鱼绺也”。
今用特别爆破法取玉,可供读者参考。
“原非于阗昆冈西流砂水中天生玉子”。
和田玉出于东西连亘长达1100公里的昆仑山北坡上,原生矿分布多处,均在雪线或其上,终年冰封,取玉之难可想而知。由于自然风化解体,外侧玉矿部分与原生矿脱离,因水力冲击流到山坡或至河滩,采集者称为“山流水”“水玉”或“子玉”。出产水玉的主要地点是今和田白玉河(玉龙喀什河)及墨玉河(喀拉喀什河)。疑高氏所谓“天生玉子”即指此二河中的“子玉”。
“江鱼绺”是山玉中的一种,即“色白质干、内多绺裂”的山玉,不便雕琢,难以成器,大多是劣质玉。
2、玉色贵贱及玉之等次
“高子曰:‘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以黄为中色,曰,不易得,以白为偏色,时亦有之故耳。今人贱黄而贵白,以见少也。然甘黄如蒸栗色佳,焦黄为下,甘清色如新柳,近亦无之”。
“碧玉色如菠菜,深绿为佳,有细墨洒点,有淡白间杂者次之”。
“墨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类之”。
“红玉色如鸡冠者可贵。三玉世不多见,都中亦宝重之”。
“绿玉类碧色,少深,翠中有饭糁者佳。外此七种,皆不足取矣”。
高濂品评玉色等次,似以产量多少、“不易得”及“时亦有之”为取合,主张崇尚黄玉,这在我国玉色品评上是少见的。他以甘黄色玉为上,羊脂玉次之,以黄为中色,以白为偏色,这些论点体现出高氏遵循传统的五行观。他所指的甘黄色玉就是蒸栗色玉,以此色为佳,焦黄为下。他提出个人的玉色见解之后,又叙述了“今人贱黄而贵白”的时尚,他以为是“见少”之故,但从我国玉色褒贬的总情况来看,还是以贵白为其主要倾向,而贵黄玉的看法是高濂个人的五行观及偏爱所致。在高濂心目中,玉色的排列应是甘黄、羊脂白、甘青、碧、墨、红、绿等七种色玉,除了这七种玉之外的其他色玉“皆不足取矣”。高濂所提的七种玉料,除了红玉之外,均在今和田玉中可以找到标本,当系和田玉而无疑。
3、玉器品种
高濂指出:“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即“玉,神物也”,颇有神秘色彩。他所指上古,包括三皇五帝至两汉,起自石器时代,跨过青铜时代,以迄铁器时代,时间跨度长达8000年之久。高氏例举圭、璧、黄琮、璋等礼器,璁、珩、双璜、冲牙等佩饰,蓐、秘、鹿卢、螭琥等剑饰,指南人、蚩托、轴辂饰诸具、弁星蚩牛环、螳螂钩、辘轳环、蟠螭环、商头钩、双螭钩、玉套管、璩环、带钩、拱璧等王侯舆服之饰,以及琉珥杂佩、步摇、笄珈、琼华躁玉等后宫夫人之饰,还有玉玲、玉填等殓尸玉。上述数十种玉器的定名与功能、分类,是否正确,不必苛求,尤其无图形可供对照,确亦很难与出土的古玉对应比较,亦不便于进一步地开展研究工作,不过,作为晚明收藏家的玉器名称和分类,仍有其参考价值。
高濂又说:“又如以玉作六瑞、宝玺、刚卯、明当、玉鱼、玉碗、卮匝、带围、弁饰、玉辟邪、图书等物,何重如之?”从宝玺、刚卯、卮匝等器型判断,应为汉代之物,已无上古之珍重,故云“何重如之”。“后此失古用玉意矣,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管、笛、凤钗、乳络、龟鱼、帐坠、哇哇、树石、炉顶、帽顶、提携、袋挂、压口方圆细花带板、灯板、人物、神像、炉瓶、勾钮、文具、器皿、杖头、杯盂、扇坠、梳背、玉冠、簪珥、绦环、刀把、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
上述玉器型饰,都是唐宋以下几个王朝的玉器,与今天传世玉器吻合。其中帽顶为元代玉器,当然电不排除含有明初的玉器。
高氏古玉分期,在当时的条件下分清上古(三代以前至汉)和唐宋以下至明初的两大段,可能是他从观赏古玉中得来的认识,以今天的考古发掘出土玉器衡量,两大段落的划分及其器型,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仍有参考价值。
4、汉玉做工的特点
高氏崇尚汉玉,对其碾工给予高度评价,他是分为器物和铭刻两类进行品评的。他列举了所见的两件汉人中圈、一件细碾星斗,谓其“顶撞圆活”,“螭虎云霞层叠穿挽”,“圈子皆实碾双钩,若堆起飞动”。我们虽已不可能见到这三件玉器,但从其字里行间,仍可体会到汉玉之精妙。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
“双钩”是中国绘画的专门术语,据《中国美术辞典》释为:“用线条钩描物象的轮廓通称“钩勒”,因基本上是用左右或卜下两笔钩描合拢,故亦称“双钩”,大都用于工笔花鸟画。又旧时摹拓法书,沿字的笔迹两边,用细劲的墨线钩出轮廓,也叫“双钩”。双钩后填墨的称为“双钩廓填”。
高氏在评汉玉时,借用绘画的语言表述他对汉玉做工的看法,所指包括平面和立体两种,如汉玉图像之双钩,是指平面图案的阴线双钩。南越王赵睐墓出上玉璧的外廓兽面纹,均用粗细、深浅不同而又富有旋转韵律的双阴线碾成,与工笔双钩类似。隐起、起突的图像,如龙、虎、螭、铺首等形象轮廓,亦为双钩,刚柔相济,巧夺天工,均足以称妙,
亦非汉工莫能为电。工笔画的双钩,反映画家的功力及修养。土雕亦不例外,从其双钩也可了解玉工的技艺水平的高下。从玉器本身来说,双钩做工起于殷,此后沿续至今。
历代玉器的双钩,也应有其各自的特点。高氏指出,汉代双钩之妙在于“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曾无滞迹”。“游丝白描”一词,也是借用绘画语言以表述汉玉做工。中国绘画以毛笔勾勒,小再敷彩者称为“白描”。绘画用线粗细不等,形态有别,画史上将最细的墨线称之为“游丝”。游丝本为蜘蛛等昆虫所吐之丝,其丝多飘游于空中,故称游丝。元代夏文彦评东晋顾恺之作品时云:“笔法如春蚕吐丝”也是指顾恺之用线细如春蚕吐丝一般。不论“游丝”也好,“春蚕吐丝”也好,均言其用线细如丝发而又自然流畅。“滞”有凝意,即指其游丝白描绝无凝聚而不流通之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用笔得失称:“又画有三病,皆系用笔,所谓三者,一目版、二日刻、三日结……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畅也” (《图画见闻志》第一卷)。此“滞”与上述“结”字意相同,也就是说汉人碾法,好像画家游丝白描那样,毫无凝结不能流畅的缺点。
高濂又称汉玉:“其制人物、螭块、钩环并殉葬等物,古雅不烦,无意肖形而物趣自具,尚存三代遗风”。
高氏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看到广州南越王赵昧、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等墓出土的西汉殓葬玉的系列的全套组合,但其所举汉玉,不仅包括人物、动物、器物,还包括殉葬等玉器,亦相当全面。其格调为高古典雅而不繁琐,更无凡俗之气,不想追求形象上的准确,而自有生动之趣。这与我们今天所见西汉玉器的风格基本吻合,但其尚存三代遗风的评价,需要具体分析,如果说高氏所指三代是传统的夏、商、周的话,那么汉玉正是抛弃了三代玉器风格而创造了新风格。当然,也可认为汉玉尚存三代遗风的说法,主要是指西汉玉器继承了楚国玉器的某些艺术基因的史实。
高濂关于汉玉铭刻的评价如下:
“又若刚卯有方者、六棱者,其钩字之细、其大小图书碾法之工,宋人亦自甘心”。
他在此说明汉代刚卯、严卯上的文字阴钩极细,用眼力几难辨识,以致后人以为昆吾刀所为。其笔道细劲,似联非联,飘逸含蕴,似有若无,如何刻法,至今仍是一个谜,后人仿者均不能如意。所见传世伪作不下数十,均不能达到下真迹一等之高水平。高氏云汉刚卯有六棱者,迄今尚未见有所出土,唯上海明陆氏墓出土一件八方刚卯,见其铭文,可知其为后世之作,亦非六棱。汉代“大小图书”即今天所云之图章,字体有小篆或隶体,碾法有阴阳,即朱白两式,均工整严谨,潇洒流丽,亦非后世所可模仿。属于前者有“皇后之玺”,属于后者为“赵妾婕好”印,其碾文的主要特色是笔道细劲刚健,字迹工整秀雅,确是我国铭刻玉件的典范。高氏认为宋人无力仿效,也只好甘心作罢了。
5、高氏评宋玉之长短
高氏对宋玉的评价也是非常客观的,一方面他客观地指出宋玉的变化和优势,另方面通过对汉、宋玉作的比较,也指出宋玉不及汉玉之处。
他对唐宋以下玉器的总评价是:
“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碾法如刻,细入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
言唐宋以下玉器“碾法如刻”,基本符合出土宋玉的砣工,指出宋玉用砣如运刀,宛若刀刻之流利自然,这也是他对宋玉碾工的准确概括,但细如蚕丝和须发及无劣隙,亦无不合规矩之败笔,其工整精致已达到顶极和尽头,不能再细、再工的至高推崇,迄今尚不能得到证实,有待今后继续观察。
紧接着他又说:
“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不特制巧,其取用材料,亦多心思不及”。
高濂以为宋玉工善于继承发扬古人之工巧,反衬后代玉工之愚拙,使其弱点暴露无遗,明玉工拿宋人也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我们今天用出土的明玉与宋玉相比,尤其明中叶以后墓葬出土的玉器,其作工之“生拙”,也正为高濂上述评语作了注脚。关于宋工用料的问题,将在下段专门讨论,在此接着看看高氏是怎样将汉宋玉器之长短加以比较观察:
“若宋人则刻意模拟,求物象形,徒胜汉人之简,不工汉人之难”。
高氏指出宋玉工“刻意模拟,求物象形”,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从出土和传世宋玉来看,宋玉工竭尽全力,模拟当时绘画和雕塑两门艺术,做到“求物象形”,达到形象准确生动。宋玉的这一特点和优点,在高氏眼里,只不过是胜过汉代简洁概括的简工玉器,而不能追求汉玉可望而不可及的难以攀登的艺术高峰。他再进一步说:“所以双钩细碾、书法卧蚕则迥别矣。汉宋之物,人眼可识”。关键在于汉的“双钩细碾”及“书法卧蚕”(疑其意是指刚卯字体)是宋人无法做到的,故汉、宋两代玉器,迥然有别,一见便可分辨,在鉴定上已非常有把握了。
6、宋代巧作
高濂在推崇宋玉工在利用玉材之妙时云:
“其取用材料,亦多心思不及”。
宋玉工巧用玉材,使明人自叹不如,可知宋工用玉,能充分发挥其质地、色泽之优势,制作出形神毕肖的玉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巧作玉雕。高氏同时列举了六件这类作品,如:
①宋张仙像:张仙可能是八仙中倒骑毛驴的张果老,然此玉雕像仅只张果老一人,身高一尺,折合今约22厘米,亦不算太小。将“其玉绺处布为衣褶如画”。玉行中有剜脏藏绺的做工,也就是将玉材中的黑点磨掉,将其原有的绺伤加以掩饰,使其缺点减少到最低程度。这就是玉工人人皆知的通常做工,本不值得一提,但在“藏绺”这一工序中,将其玉材上的绺纹用作衣服的皱褶,使其飘逸流畅,妙如绘画,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普通玉工难以做到的。
②宋玄帝像:玄帝即主镇北方的玄武神,往往头作剃顶、披发、蓄须的威武形象。而高濂所见之玄帝像,以一块有点斑的白玉琢成,“取黑处一片为发,且有额起,面与身衣纯白,无一点杂染”,制成一件高六寸的黑发、白面、白衣的玄帝像。用我们今天的理解,这就是一件比较单纯的黑白两色的俏色玉雕。
③宋子母猫:比俏二色的玄帝像要复杂得多。此玉为以白为地杖的花色玉,计有白色、黄黑相间的玳瑁色、纯黑色、黑白杂列以及黄色等多种色彩的俏色玉雕。以此花色玉琢碾成长九寸的子母猫,以白玉部分琢母猫,以玳瑁色、纯黑色、黑白杂列及黄色部分碾作六只子猫,负于母身,“取其形体扳附眠抱诸态”。高濂深晓其俏色的根由,即“因玉玷污”,却能“妙用种种佳色”,令其子母猫动态自如、栩栩如生。这是迄今所知最复杂的俏色玉,虽然我们不能见其实物,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窥宋代俏色玉的多彩倾向及玉工追求现实的艺术观。
④宋墨玉大殃:其“全身地子、灵
芝俱黑,而双螭腾云卷水皆白玉,身尾初非勉强扭捏”。此玉黑地白章,宋工以黑地作地子和灵芝,用白章作双螭、腾云及卷水三物,仍属二俏色玉雕。
⑤宋玛瑙蜩蝉:“黑首黄胸,双翅浑白明亮”,为三色俏作玛瑙器。
⑥宋缠丝玛瑙弥勒像:以红、黄缠丝作袈裟,以黑处作布袋,而面、肚、手、足皆白,应是俏色大肚弥勒坐佛。
在高濂所举六例巧作材料中,计有复色玉四件、玛瑙两件。玉有有绺玉、黑斑白玉、花色玉及黑地白章玉等四种,玛瑙有三色及白地红黄缠丝等二种。前一件为遮绺做工,后五件为俏色做工。高濂所见“种种巧用”玉材的巧作玉达“大小数百件”之多,而且水平均与上举六例相当,他感叹地说:“近世工匠,何能比方?”这种说法不是褒宋贬明,而是对宋明两朝巧作玉的公平评价。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宋代是我国巧作玉器空前发展的时期,无可置疑也是它的顶峰期,至明已趋衰落。
高濂对宋玉特色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所言“宋人则刻意模拟”便一针见血地点到了宋玉的要害。
7、古玉沁色
高氏是鉴赏家、收藏家,一生过手的古玉难以胜数。他以为古玉中“存遗传世者少,出土者多”,“古之玉物,上有血侵,色红如血,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谓之‘尸古,如玉上蔽黄土,笼罩浮翳,坚不可破,谓之‘土古”。他还列举了半裹青绿的玉殃和周身青绿的定窑二瓶,以说明“此必墓中与铜器相杂,沾染铜色乃耳”。可见高氏深知出土玉器在墓葬中受染,有色红如血的“血侵”(亦名“尸侵”),还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的“尸古”及“玉上蔽黄土、笼罩浮翳、坚不可破”的“土古”(亦称“土锈”)。上述三种锈侵代表了晚明玉器收藏家对古玉沁色的看法,比起清人有关沁色的品种数量的记载要少得多,说明此时藏玉者对古玉沁色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朴实而不夸张的早期阶段,也是可信的。
8、关于明代伪古玉的制造地点与方法
高濂确知明代制造伪古玉的地点及其加工方法,这对我们研究明代伪古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现籽原文摘录如下:
“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
上述短短的四十一个字便勾勒出明代伪古玉的制作地点、器型、玉材、方法及目的。“近日”是高氏健在之前不久的一段时间,前面介绍高氏于万历初尚在世,而此“近日”应不晚于万历初年,或定在嘉靖时期较为妥当,即1522年至1566年。
“吴中工巧”:吴中即吴县,今苏州。苏州专诸巷系明代玉作集中地,至清代益隆。“工巧”即玉工技艺精湛。
“模拟汉宋螭块钩环”:螭是龙九子之一,汉代螭纹为虎首,有长角,兽身,长尾,故称螭虎,因其穿云驾霭、盘屈缭绕,亦称蟠螭。帝后印均有蟠螭为钮,似唐宋年间之龙,已成皇家专用图案,所以汉代帝王玉多有蟠螭纹,以螭饰的殃、钩、环便成为明玉工的模拟对象。螭虎纹沿用至清代,宋玉偶亦可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明代所制伪古玉是以汉、宋两代的螭纹装饰的殃、钩、环三种玉器为主。
“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苍黄色玉即青色玉肌中泛出淡淡黄色的玉材。杂色玉与白、青、黄碧、绿、墨等色玉不同,而是由二三种甚至四五种颜色相混杂的玉材。边皮包括边角下脚料、玉之表皮、围岩及玉表面风化蚀变的材料。葱玉即葱白色、透明度不佳、质地较干的劣质玉。带淡墨色玉即玉内含黑点(碳素),分布不匀或数量不多的青玉,颇有旧玉的味道。上述五种可供制作伪古玉的玉料都是劣质玉,价格低廉,不便碾琢时作玉。从现存明伪古玉来看,所用玉材实不限于上述五种,凡是带有旧玉味的劣质玉材都可用来制作伪古玉。
“如式琢成”:上述“模拟汉宋螭殃钩环”是“如式琢成”的一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按图碾琢,如从《三礼图》《考古图》《古玉图》等刊有古玉的图书中取样,亦可如式琢成。
“伪乱古制,每得高值”:如式琢成伪古玉,使古玩市场上的古玉真伪混杂,难分难解,扰乱视听,以假充真。古玩商将伪古玉高价出手,获得高额利润,大发横财。“伪乱古制,每得高值”就是制造伪古玉者的最终目的,不仅明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9、钩碾不可仿
高氏讲完明代伪古玉的情况之后进一步指出:
“熟知今人所不能者,双钩之法,形似稍可伪真,钩碾何法拟古?识者过目自别,奚以伪为?”
他告诫人们要注意观察,形制上相似往往稍可伪真,容易混淆收藏家视听,尚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唯有双钩之法明人所不能为。钩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用何种钩碾之法也是不可拟古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书画伪作往往可以做到形似“稍可伪真”,但笔法是不可仿的,有的书画鉴定家称其为“笔性”,而笔性因人而异,别人也是无法学到手的。
能够识别钩碾法之不同的,也只有经过多年玩赏鉴定文物、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专家,也就是“识者”,他们才能“过目自别”。
10、“土锈尸侵似难伪造”
高濂以为苏州玉工伪造土锈尸侵似是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做不到的,因而他在记述苏州玉工所制伪古玉时,未提烧古和染玉之法,这可能反映了那时苏州玉工尚不善造伪沁;或许苏州已用人工烧造伪沁之法,但住在杭州的高氏尚不知晓,所以未提出伪沁问题。
11、“混玉”之石材
明代伪古所用玉材已如上述。除了用劣质玉作伪古玉之外,还有以石混充作“玉”料制伪器的,如:
“有种水石,美者白能胜玉,内有饭糁点子,可以乱真”。
这种水石产于何地,属于何种矿物,有何专名,高氏均未言及。其美者色白,能胜过玉石,可冒充白玉,内有白米饭粒状的小点子,似玉之白脑,以其乱真,有着更大的欺骗性。
“又如宝定石、茅山石、阶州石、巴璞、嘉璞、宣化璞、忠州石、莱州石、阿不公石、梳妆楼肖子石,俱能混玉”。
宝定石:疑其为保定石,可能是今曲阳大理石(亦称“汉白玉”)。其他八种石或璞,均为该地的似玉之美石,详不可考。梳妆楼肖子石:即是用石料粉烧造的人工玉,称为“硝子石”,即曹昭所讲的“假水晶”,有暗青色、黄青色和白色。硝子石不适于在大作坊烧造,多在城市内的梳妆楼(即银首饰楼)加工烧造,小批生产。
各地美石、璞及硝子石(人工玻璃),均可混充玉材制作伪古玉。由此可知,明末伪古玉的用料,除了劣质和田玉之外,尚有美石、璞和仿玉玻璃。
通过对上述《新增格古要论》《遵生八笺》这两本古玩全书中有关玉器鉴定与辨伪的分析研究来看,有明一代,自曹昭到高濂,其辨伪侧重点由玉材(石类玉、混玉之石、罐子玉)扩展到器型,并进而抓住“钩碾”这一关键,揭示了“钩碾何法拟古”的作伪的薄弱环节,指出汉宋玉器的“双钩”“卧蚕”“求物象形”均是无法仿制的。此时收藏家还不甚喜爱沁色,至少在文人逸士类型的收藏家之中,还未看重沁色,认为“土锈尸侵似难伪造”,他们尚不知已有作伪沁者,故不将沁色作为辨伪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明人古玉辨伪的基本情况,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整理研究明代传世古玉,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