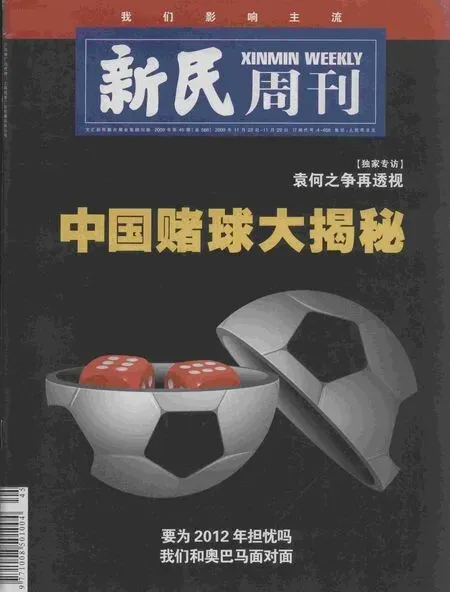林怀民:磐的哲学
王悦阳
林怀民用舞蹈跳出的悠悠岁月,也正如水墨着色的磐一般,既拥有固态坚实的外表,又富于水性灵动的内在,百态缤纷。

62岁的林怀民,把自己人生一大半时间“瓜分”给了云门,云门舞蹈也为林怀民的生活添上了五彩斑斓的色彩。都说岁月不饶人,这样的自然规律在林怀民身上似乎一点不起作用。一身黑衣、黑裤、黑皮鞋、黑边眼镜的他坐在阔大的扶手椅上,时而舒展身姿,时而蜷成一团,活生生的一个大男孩。在他黑色细框眼镜背后的双眸,光彩烁跃、眉飞色舞,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说到会心处眸中熠熠,独具个性的话语也一如既往的感性如诗。
林怀民准备带着《行草》走遍中国大陆。他的视线凝重地落在宣传海报上墨水挥毫与黑衣舞者的舞姿组合而成的“磐”字上,咧开嘴大笑起来。当初,林怀民创排完《行草》时,找到了自己在台湾的好友、书法大家董阳孜女士,想请她帮忙写一个“磐”字作为舞台布景的一部分融入整个舞蹈中去,“因为‘磐的结构和字义所表达的就是一种非常稳健的态度,最能压场。”出乎林怀民意料的是,一个月后他来到董阳孜家中“收字”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满墙壁的“磐”字,“大概有两三百张,当时我真是挑花了眼”。
董阳孜的“磐”成了《行草》现场唯一一块非投影的实体道具。有趣的是,每每有人同林怀民谈起《行草》,他总喜欢提起这件趣事同众人一同分享,因为“磐”所表达的不但是《行草》这出舞蹈的精华,更是林怀民自己的艺术哲学。
即将上演于东方艺术中心的《行草》,是一出以中国书法为灵感的作品,在一方被灯光渲染的有如宣纸一般的白色舞台上,穿着黑色服装的舞者,犹如蘸满墨汁的毛笔,用身体动作自由书写,时而狂放、时而内敛、时而挥臂猛旋、时而优雅曼妙。在巨大的白色银幕上,王羲之、怀素、张旭等历代名家的书法,以惊人的巨大尺寸,动人的细节,恢宏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我的字其实烂透了。到现在我最怕的就是别人让我写字。说句玩笑话,大概由于小时候练字练怕了,于是才有了《行草》三部曲吧。”虽然排演《行草》的目的在于“以舞蹈为跳板,让书法有呼吸”,可林怀民总不愿意称自己是真正懂得书法艺术的人,只是想用舞蹈,来与千百年前的字魂对话。而林怀民用舞蹈跳出的悠悠岁月,也正如水墨着色的磐一般,既拥有固态坚实的外表,又富于水性灵动的内在,百态缤纷。
寻找自我的云门
上世纪60年代末,已在文坛颇为著名的林怀民毅然逃离了正处于文化戒严时期的台湾,只身远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研读写作。然而,身在异乡的寂寞孤独让林怀民感受到了莫大的压抑,舞蹈教室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港湾。“舞蹈就如同一个陷阱,一旦你走上这条道路,再也欲罢不能。”
1972年夏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怀民放弃了可能成为美国职业舞者的机会,收拾行囊离开了美国,去欧洲寻找自由,这也是林怀民人生的第一次流浪经历。可是,自由永远只属于爱琴岛的雄鹰,当他站在雅典的机场,眺望着即将搭乘返回台湾的飞机时,一种怅然若失的伤感油然而生,林怀民这个大男孩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而且哭了很久。
当时的台湾,文化牢牢地被禁锢在政治的枷锁之中,任何艺术题材都不可碰触现实和历史。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大批从大洋彼岸涌入台湾的西方文化产物如同最烈性的伏特加,麻醉着台湾青年们的精神世界:最流行的绘画是抽象派油画,流行音乐只听披头士,在文学上就得数乔依斯的《尤利西斯》……现实如同林怀民之前想象的一般残酷,但留学的经历和流浪的生涯让崇尚自由和理想的林怀民萌生了改革的念头。刚巧,回到台湾的第三天,林怀民遇上了一群舞者,这些人无不抱怨台湾没有一个职业舞团,甚至连业余舞团都没有。一番话说得林怀民血脉贲张,立即作出了决定:那就干吧!
林怀民有众多身份,除了云门创始人之外,他还是一个作家。要知道,在云门建团之初,林怀民的稿费曾经是维系云门生计至关重要的收入,“云门组建后,最现实的问题莫过于募款,我是云门的螺丝,从来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很多事情我都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但我跟写东西的人不一样,还不能一股脑儿地闷在家里写作。”为此,林怀民总笑称自己从不是一个艺术家,而仅是一个工匠,一个整天在编篮子的手艺人。
初建云门之时,为了打破社会上“男孩子跳舞不正常、女孩子跳舞不正经”的极端保守思想,林怀民大胆地脱下衣服,露出赤裸的肌肉。如今回想这段记忆,他难以抑制地喜从心生,一只手掌捂住嘴巴笑了良久后,神采飞扬地说道,“我想,我跳得不太好吧。你看我这个外形,既不像许仙,要跳法海又嫌个头太小。我跳的舞连自己都不敢看,现在想来真的很侥幸,幸亏那个时代没有发明录像机……”
从《白蛇传》的目眩神迷,到《红楼梦》的斑斓绚丽,云门舞集的开山之作无不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展开,这也就等于是云门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化现实作出了一个反抗。云门组建同年,在台北中山堂第一次公演中,三千张门票售罄,连黄牛票都一票难求。然而,台上的林怀民却感觉自己糟糕透了,他歇斯底里般地突然停下,朝向台下用闪光灯对着舞台狂闪的观众们抱歉道:“对不起,我们落幕重来。”正是这种对舞蹈的严谨至极,近乎苛刻的态度感染了所有的台湾民众。
出逃和回归
龙应台曾在评价林怀民时说,30年来,林怀民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在试图改变穷孩子文化当中的局限。正是因为云门的一夜成名,林怀民萌生了更多疯狂的念头:将云门舞集打造成台湾的文化窗口,超越时空与地域的界限,向台湾民众乃至世界民众展示古今中外的舞台艺术。
云门不但邀请李环春和郭小庄与云门同台演出昆曲《夜奔》与《思凡》,还把屏东排湾族原住民最原汁原味的舞蹈带进云门的实验剧场。当然,这些并非是云门干过最疯狂的事情,林怀民甚至别出心裁地将日本雅乐与云门舞蹈结合,搬上舞台。对于这些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创举,林怀民非常自豪:“一方面我们也对这些艺术深感好奇,因此把它们引入学习。同时,我们又把它们推荐给社会,你想连雅乐这么生僻的艺术都能演满四场,这才是云门真正的魅力所在。”
80年代中叶,名噪一时的林怀民彻底陷入了工作的泥沼,他同时肩负着另一个“恐怖”的差事:创办台湾艺术学院的舞蹈系,两厢的忙碌让他全无宁日,心力交瘁。而云门的舞者们也同样难以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舞蹈本身,一些结婚生子的舞者想回家看小孩,上班的时候先买了菜,搁在冰箱……
林怀民扪心自问,再这样在云门打拼下去还有什么结果?既然心思已经不在舞蹈,不如同舞蹈做一个彻底的诀别。当做完最后一场演出的那一刻,如释重负的林怀民收拾起行囊,离开了台湾。
再一次恢复自由的林怀民,来到香港,一门心思地做起了客座教授。当他厌倦了为人师表的生活,林怀民独自一人背起包包,来到大陆,从西安、洛阳、兰州、敦煌,一直走到了上海、苏州,“那时,我把自己脑海里所有想去的地方都走遍了。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去杭州。”数十年后才有机会首次来到杭州的林怀民,乐呵呵地嘲笑自己“当时大概脑子坏了”。这段经历让他收获了无数奇观轶闻,也让他对大城市给旅人带来的孤寂之感体悟得淋漓尽致,“当时我来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变得不知所措”。
最让他收获良多的是敦煌。创立云门之初,他曾执著地追求充满创意、天马行空的艺术。如今,他看到了不懈追求的美,也让林怀民诞生了重组云门的念头。有一次,林怀民去观摩敦煌壁画,他在石洞中看到许多白发苍苍的画师,就着微弱的灯管,临摹墙上的壁画。当他仔细观察这些画师面前的画板时,他不禁一惊,无论从笔法还是色彩上,这些画师笔下的画都与千年来的壁画如出一辙。这一周,林怀民每天都会去洞里观看他们绘画,“这些画家从20世纪50年代到了敦煌研究和临摹,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像一块石头一般,仍然守在那里,不肯离去。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当自己有所摇摆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在洞窟中间依然执著的白头发长辈们,于是内心有时候会觉得很惭愧。”
脱下中国符号
1991年,带着渴望和惭愧,林怀民重启了关闭三年之久的云门,回到了云门舞者的身边。“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团里度过的,即使那些大着肚子的妈妈级舞者们都不会离开云门,他们或者拿起相机担任摄影,或者坐在办公室里处理行政事务。”林怀民坦言自己最爱妈妈级舞者,“她们的身体经受了惊天动地的裂变,一下子就什么都懂了,对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百分百的了解,所以动作特别漂亮。”
更为可喜的是,林怀民确实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东西——艺术上的突破。
2001年起,林怀民由书法美学汲取灵感,编出了备受国际舞评赞誉的《行草三部曲》首篇《行草》。在编排《行草》的过程中,林怀民发现,尽管风格各有千秋,历代书家都同样以专注的精力,飞墨行“舞”,字里行间,尽是书家运气的留痕,“像王羲之的字,是那样的有魔力,就如同在欣赏昆曲一般,大方和妩媚,仿佛在向后人述说魏晋风流的那些往事。可是当你自己去阅读那些文字背后的含义,却往往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姑母去世了,自己生病等等,这些令人难过的现实生活,居然隐藏在一纸秀丽、典雅的文字中,令人纠结的心境顿时油然而生;而最悲惨的当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他那肆意横飞的点划,加上枯笔的笔触和留白想象,给人的激动与感动实在难以言表。虽然书法隔了千年的时光,但它讲的却都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所讲述的都是人与人的一个个鲜活无比的故事,看着它们,让人时时刻刻就想要拥抱它、触摸它、安慰它、佩服它。看着它,就好像跨越时空和古代的大师对话,我常常会因此而感动得流下泪来。”
于是,林怀民延聘名师,让云门舞者长期习字,再去面对放大的书法投影进行即兴表演。舞者吸收书法家的“精气”,用身体动作来临摹他们的挥洒书写。这样的练习,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动作,既有精密细致的慢动作,也有类似武术般的猛烈攻击。这些,最后都成了《行草》的舞蹈素材。“有时候,我觉得《行草》三部曲仿佛是云门对悠久辉煌书法艺术的一曲挽歌。”林怀民用略带伤感地语调说道,“我们写毛笔字时,感受到的是掌握时空的感觉与气度,期待着一分天人合一的美感,享受着一种气韵生动的意境。跟今天用电脑打字的感觉截然不同,电脑没有感情,没有笔触,更不会像宣纸那样泛出好看的水晕,真是一个能把人逼疯了的空间!”
另外,林怀民也实现了自己最初对《行草》的期冀:对于中国符号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相比早期的《红楼梦》、《白蛇传》等满台都是中国符号的作品,《行草》以及《行草》三部曲,只是保留中国艺术的形态,强调高度凝炼化的表达,除了在背景中加入中国书法的线条,其余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现代的表现。这种现代与古典的结合,不但丝毫没有损失中国味道,在舞台之上反而显得各外相得益彰。
30年间,云门舞集已从最初那个由满腔热血的海归青年一手打造的现代舞团,成为一个社会公器、中国现代舞蹈的符号,而林怀民本人更是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英雄人物”。然而,悬置于头顶之上、天花乱坠的美誉和赞歌丝毫没有改变云门和林怀民的艺术哲学,他们永远在彼此实验中携手前进,共同成长,“我正在着手编排新的舞蹈,这出舞蹈的名字叫做‘听河。”话到此处,林怀民的神思自顾自地变得凝重起来,他双手托着脸颊,陷入了沉思,“虽说叫‘听河,但不会出现任何实体的水的形态。我现在的想法是用影片来表现许多不同的水的表情,从《西游记》的故事说起,但还不知道要怎么实现,所以非常苦恼,还好有充足的时间容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