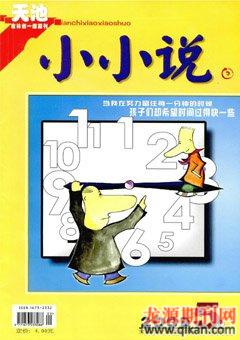停水
李艳霞
在一个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就像一只小鸟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从灌木丛林迁居到了乔木丛林。我乔迁的新楼坐落在一个城市开发区铁路的旁边。
入住新楼进进出出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在这个小区里生活,我仿佛与世隔绝了似的,如果不是铁路上行驶的列车经常发出轰鸣的声响,我以为这里一定是一个世外桃源。
我什么也不必担心,没有人会来打扰我。入住新楼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懒散地走到卫生间,挤上牙膏,操起杯子对准水龙头,竟没有一滴水流出来,这可坏了,停水了!没有水就没法刷牙洗脸,这可咋去上班?我下意识地向窗外张望,突然发现人们提着大桶小壶向着同一个方向奔去……
我也提着水壶下了楼。路口,有一间看守铁道的小房,院子里,挤满了打水的人们。因为小房的院子里有一眼人力压井,这时它成了整个楼群的希望。
这样的井在城市里已经太少见了,它不太好驾驭,只有熟悉它,了解它的脾气和秉性才能够驯服它。人们舞舞咋咋地操作着,好半天水也没有引上来。
这时,从小房里走出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把井抽子拽出来,重新安装一下又放进了井管里,然后用力地往下压,终于将井水压了出来。
人们看到井水上来了,都跃跃欲试。不管年老的,年少的,看上去体面的还是寒碜的都对那男子陪笑脸。男子不管谁的笑脸灿烂还是谢辞动听,他优先帮助的是那些年老的担水者。对于年轻人,他就站在一边指导他们压水的技巧。
就在人们认真地盯着水井,争取提前打上水的时候,突然楼群里传来了一阵呼喊——来水了……来水了……人们一听到来水了,压水声嘎然而止,有的扔掉水壶里的水,纷纷向楼上跑去……
小院子内被倒掉的水糟蹋得不成样子。此时的男子和他的井把子一样被冷落在那里。他只好自己动手把井抽子再拽出来,如果不拽出来,用不上两小时,井管子和井把子冻在一起,那麻烦可大了。
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匆忙跑掉。我暗自想,人,咋能这样,用人的时候眉开眼笑,现用现交,用不着了不理不采。他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平,忙解释,人家都挺忙的,行啊!说着,他伸手从冰冷的井管里拽出那个井抽子,然后又去打扫被大家弄得脏兮兮的院落。
不久后的一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由于维修自来水管网,临时停水了,人们又挤在那眼水井旁。
这回大家似乎对这种情况具备了充分的应急措施。有人给那位男子递烟,有的跟他搭讪套近乎,还有的说认识他的七大姑八大姨,男人表现得一点也不反感。
因为大家对驾驭水井有了丰富的经验,男子把水引了上来后,大家便各自动手交替着压水。男子在一边维持秩序,让大家不许夹塞,按照顺序进行。
我的前面排了足足有二十几位担水者,其中一位提着一只五十的塑料桶正在接水,她不慌不忙地等待水慢慢地流入桶内。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再等两小时也排不到我。八点钟还要签到,我很着急。我对那位男子说,能不能让我先来,不然我会迟到的。我以为男子会破例让我夹个塞。
男子听了我的理由,并没有破规矩,而是把我的水桶接过去走进了小屋,灌满后递给我。我心中充满了感激,走出院门的时候,还回过头来说了一声谢谢,以后有事尽管吱声!
很快,管网正常送水,谁还会去回顾路口的那眼水井?一天,当我快要下班的时候,邮政快递窗口来了一位顾客,要求邮寄一份快递。我心里说,都下班了,咋不早点?我却本能地递给他一张信封。他指着其中的一栏说,同志,填在这对吗?我低着头,态度有些冷漠,那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我指了指窗口上贴着的式样。
可我还是怕填错了……
你咋这么磨讥?我的话让他有些惊诧。
你不认得我了?
我抬起头,冷冷地望着他,想不起曾经在哪见过。
忘了吧?铁道口……你来打过水……
他的提醒让我恍然大悟,面红耳赤的我,尴尬地接过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