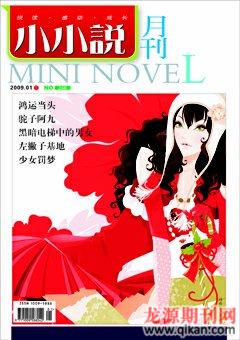休渔
王明新
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左老汉已经用摩托车驮着几十米长的挂网来到了海边。风平浪静,海面上有一层淡淡的轻雾,蓝得如女人脖子里的纱巾。半个月亮倒映在水里,随着海水难以察觉的晃动,水中像有了一串月亮,亮得晃眼。左老汉从摩托车上将挂网卸下来,背在身上下了水。挂网下面有网坠,上面有浮漂,网下在水里,直直地垂在那里如一道篱笆。再有个把小时就该涨潮了,那些银亮银亮的梭鱼就会随着潮水往外走,然后钻进左老汉的网眼里。那些网眼设计的不大不小,鱼们钻进去,一呼吸,两鳃正好卡在网眼里,进退不得,被左老汉收进鱼篓中,这就是一家人的衣食,孙子孙女的学费和左老汉终日不离身的酒葫芦里的酒了。
如果是平时,海面上早已是桅杆林立,船儿竞发,热闹非凡了,但现在正是渤海湾的休渔期,整个海岸静悄悄的。因为从三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是梭鱼、鲅鱼和黄姑鱼的产卵期,这些年由于无限制地捕捞,鱼肥水美的渤海湾,已经越来越清汤寡水了,别说是本来就珍稀的银鱼、斑鰶鱼、日本鳀鱼已经基本绝迹,就连最常见的鲅鱼和梭鱼也越来越少了。过去一网下去捞上来,总是沉甸甸的拽不动,现在网里是越来越轻了。政府实行休渔制度,村里的几十条鱼船都停了下来,这本来是件好事,可左老汉就是在家里休不下去,他想别人都在家里睡大觉,正是自己发财的好时机。
这是一片平缓的浅滩,左老汉向水里走了近30米,水只没到大腿根,还要向里再走十多米,水差不多没过小腹才能下网。左老汉身上的皮裤一直套到胸脯之上,隔着皮裤左老汉感到了水的凉意,身上这里那里,如无数个针尖刺进皮肤,深入骨髓。又走了一会,左老汉开始把挂网下在水里,他一边下网,一边顺着海岸的方向慢慢移动。几十米挂网沉重地压在左老汉身上,他想快点把网下完,那样自己就轻松了,可是网太长,网坠和浮漂总是纠缠不清,左老汉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将它们一点点解开。不知道什么时候雾变得浓了,一团一团从黑黑的海面上滚过来,濡湿了左老汉的头发和胡子,左老汉用手一摸,摸了满把的水。左老汉顾不上这些,他不停地摘网下网,摘网下网,无意中他向海边上看了一眼,海岸不见了,他满眼里都是雾,浓得如一堵厚实的墙。左老汉没有多想,继续忙着摘网下网。
身上越来越轻了,终于下完了最后一寸网,左老汉长舒一口气,摸出酒葫芦来头朝天咕咚咕咚灌了两大口,烧酒像一粒粒烧红的炭块打着滚滑入喉咙里去,最后落入胃中,变成一股股热气,从汗毛孔里钻出来,浑身说不出的舒畅。开始涨潮了,左老汉感到潮水像调皮的海豚一下一下顶他的屁股,从他的两腿之间钻过去,在他那个地方摸了一把。左老汉无声地笑了一下。现在左老汉要做的就是回到岸上去了,回到岸上坐下来,喘口气,抽两袋烟,再喝几口烧酒,身上就有了力气,然后他就可以下到水里顺着挂网把那些卡在网眼里的鱼儿摘下来,放入鱼篓中了。天亮之前这些工作就可以全部完成,然后神不知鬼不觉骑着摩托车去早市,老婆子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把鱼放下就可以回家了。老婆子卖鱼,他回家吃老婆子为他准备好的早饭,然后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上岸之前左老汉满怀希望地看了一眼他下的网,应该是白白的长长的一串浮漂,弯弯曲曲在海水中起伏,可是左老汉什么也没看见,他下的网去了哪里?左老汉不相信这个事实,再看还是没有。不只他下的网,左老汉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他什么也看不见,眼里除了雾还是雾,浓得化不开的雾。
左老汉有几十年的捕鱼经验,过去在海上他也遇到过这么大的雾,但那是在船上,再说还有别的捕鱼的弟兄,遇到这样的大雾他们只好停止作业,不然船会触礁,大家抽着烟说说笑笑,等待雾散。现在海水里只有左老汉一个人,他分不清东西南北,只好凭感觉摸索着向外走。走了一阵,他发现水越来越深了,他怀疑走错了方向,调个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可是凭着潮水的流向,他觉得现在的方向仍然不对。他只好站下来,让自己冷静冷静,辨别一下方向再走。浓浓的雾从左老汉眼前飘过去,哪里能辨别出方向来呢?左老汉挥舞着双手想把雾赶开,可是赶走这些又有另一些填补进来,怎么赶得过来呢?左老汉累得气喘吁吁,到底没把雾赶走。涨潮声渐渐大起来,潮水像是去赴一个约会,一浪赶着一浪不断地涌上来,水渐渐没过了左老汉的肩膀,又没过了左老汉的脖子,左老汉真的慌了,可是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后来左老汉双脚够不着海底了,他只好游泳,几十年的闯海生涯让左老汉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左老汉倒是不怕,他游啊游啊,可是总也看不到岸。
大雾直到下午才渐渐散去,左老汉没有回家,人们也没找到他的尸体,左老汉消失得无影无踪,左老汉去了哪里?从此他也像许许多多的人类之谜一样,无法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