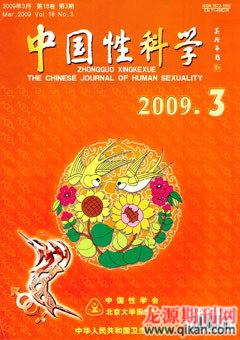合法抑或合理:中国同性婚姻的两难处境
章立明
[摘要]作为一种性取向,同性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民族、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阶层中,男男同性恋群体的性行为方式容易造成疾病传播的高几率。一些西方国家承认同性婚姻,旨在保护他们之间长期的伴侣关系。在我国,承认同性结婚等于解构二元对立的性别文化,而且多种性关系的存在,使异性婚姻成为艾滋病痛毒扩散的温床,同性婚姻陷入既不可能合法和也不舍理的两难境地。中国第三部门在应对艾滋病危机时,应将同性恋纳入关怀视野,最大化地降低其高危性行为的风险指数。
[关键词]同性婚姻;两难处境;技术防护
男女两性在人类生殖中的功能分化是大多数社会人类再生产的基本方式和家庭婚姻制度存在的前提,恩格斯说:“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分工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限于性器官,也可以扩展到第二性征,或者相反,对整个有机体和社会产生影响”,例如婚姻就是“一个男人(男人们)与一个女人(女人们)之间持久的联结,赋予配偶互相专有的性权利和经济权利,赋予由婚姻而生的孩子以社会身份”。涉及婚姻的几个普遍要素包括:(1)性交的权利和义务;(2)经济的责任;(3)得到法律或习俗的认可;(4)婚生孩子的社会身份。如果说婚姻只是单纯的性与经济的结合体,那么,婚姻这两个要素不会因其主体由异性变为同性而有所改变;随着最新生殖技术的发展,妇女的性行为属性和生育属性得以分离,使婚姻成立的要件就剩下法律或习俗的认可了,或者说同性婚姻也必须以“结婚双方负有一定的为社会所承认的权利和义务为前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承认同性婚姻等于解构二元对立的性别文化,而且婚外性关系与一夫一妻制婚姻相伴共生,一对一的异性婚姻模式并不能阻断艾滋病病毒的扩散,同性结婚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庞大的同性恋人群加大了艾滋病病毒的扩散风险,第三部门联合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开展宣传倡导和同伴健康教育项目,从技术层面降低高危性行为的风险指数,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社会应对同性性行为的最优化选择。
1西方的同性恋与同性婚姻
1869年,同性恋(Homosexuality)一词最早由匈牙利作家本克尔特在一篇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文章中提出,随后,由德国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克拉夫特一埃宾引入病理学研究领域,成为精神失常或者性反常这类临床术语的代名词。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从性犯罪一性变态一承认同性婚姻的漫长过程。
1.1作为性取向的同性恋
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具有长期性、偏爱性的明确指向,而不是偶然发生在同性之间的境遇性性行为,它与异性恋和双性恋一样,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取向。同性恋“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一般为2%~5%”,怀特姆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现象;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因为同性恋倾向并不会因为某个社会对它持严厉的否定态度而减少,也不会因社会规范的宽容而增多;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就会产生同性恋亚文化。
金赛以及其他学者的跨文化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同性恋不是一种特异的行为模式,不是由什么特殊的社会结构所产生,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人类性行为的基本形式。
1.2同性的世俗结合与法律实践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使同性结合趋于规范化的主要手段是风俗、伦理和法律,婚姻可以分为世俗婚姻和法律婚姻。人类学家证实,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类社会中都存在世俗认可的同性结婚案例,肯尼亚西部的南迪人的女一女婚姻被看作是这一婚俗的典型代表。因为性别文化重新定义了两性的生理性别,即某个性别为女性的人可被定义为男人,或某个性别为男性的人可被定义为女人,所以,同性个体之间的婚姻被视为正当的、正常的,这种婚姻的目的在于提供男性继承人,人们承认她的女性丈夫是在这些条件下出生的每个孩子的父亲——社会和法律意义上的父亲。
在现代社会,一般情况下世俗婚姻和法律婚姻是重合的。荷兰、丹麦等5个国家制定同性婚姻法案,其他很多国家或某个国家内的部分地区制订了家庭伴侣关系的相关法律,保障同性恋者在结合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它们主要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完全享有异性恋婚姻权利的同性婚姻。如1988年12月,丹麦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法律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该法案规定,同性婚姻中的配偶双方在遗产、继承、住房津贴、退休和离婚方面,享有与异性婚配相同的权利。2004年3月,英国政府颁布《民事伴侣关系法案》赋予同性恋者婚姻的合法权利,同性恋者可以前往登记办公机构签署一份官方的民事婚姻文件,即可享有与异性夫妻相同的法律权利,组建自己的家庭,该法案赋予同性恋伴侣在医院的近亲地位权利,允许同性恋者成为辞世伴侣的养老金受益人,并在继承伴侣的房产时免缴遗产税,决定分手的同性恋伴侣也必须经过法庭裁决进行离婚。
第二种是公民结合,它是一种介于同居与婚姻之间的新法律关系,它对组成家庭的双方界定比较模糊,但又明确了相关的权利与义务。1999年,法国通过《公民互助契约》使包括同性伴侣在内的非婚伴侣可以享有已婚家庭同等的权利。2000年,美国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签署法律,允许同性伙伴之间的公民结合。2002年,挪威、瑞典、冰岛、德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某些地区相继认可同性结合登记注册,赋予其大部分传统家庭所享受的权利。2004年3月,马萨诸塞州通过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但承认公民结合,赋予同性伴侣部分权利。2004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法案,赋予同性恋者及同居人士的公民结合可以享有与合法夫妇等同的法律地位。
西方同性婚姻实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特别是酷儿理论的支持,酷儿指称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挑战了传统的非男即女的两分结构,对异性恋的自然性提出质疑,强调同性恋等各种边缘群体的正当性,认为同性恋非关“正常”与否,它是一种正当的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
2中国同性恋及同性婚姻提案流产
1991年以来,我国同性恋经历了非刑事化、非病理化的过程,同性恋研究、同性恋与公共政策关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同性婚姻提案孕育而生,但是二元对立的性别文化导致同性婚姻提案无法顺产。
2.1处于立法空白的中国同性恋
以同性恋人口在人群所占的比例3%~4%(取中位数)估计,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在3900万~5200万人之间,对于这个人数庞大的群体,成熟的社会需要某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如平等权、人身安全权、名誉权、隐私权等,而要解决这些合法权益,就需
要明确其法律地位,只要在法律中将家庭的定义(结构、形式)扩展为由通常的异性夫妻和子女等组成外还包括同性婚姻形式所组成的家庭,则一切均可迎刃而解。但是,我国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的立法空白,已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普遍歧视,使同性恋群体面临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压力。一项关于同性恋者被歧视的调查显示。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过自杀行为;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
其次是难以管理高危同性性行为,使同性恋群体面临疾病压力。我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2004年11月,卫生部门公布一项最新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男性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吸毒人群,截止2005年9月,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性传播占32.4%。
尽管同性恋不能等同艾滋病,但因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和法律保障,同性恋者无法建立类似一夫一妻的稳定性关系,造成同性恋者成为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对我国同性恋者的调查显示,有将近90%的同性恋者希望或曾经希望建立富有情感的单一伴侣关系,但由于性取向不被认可,大部分的同性恋者最终不得不走进异性婚姻,因此,艾滋病的传播地点已从主要在家庭外传播发展为在家庭外和家庭内同时传播,即当夫妻间的一方在家庭外染上艾滋病后,又在家庭内通过性接触把HIV传染给其配偶。在性交中,妇女被男性感染的危险高于男性被妇女感染的危险,“男性感染者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女性的危险是女性传给男性的2倍”,其中以男配偶传给其女配偶为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母婴传播,表现为艾滋病疫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流行病学传播特征。
越来越多的专家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出发,建议国家承认同性婚姻,从法律上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使同性恋者建立一对一的稳定伴侣关系,从而减少性病等疫情传播的可能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12个欧洲国家的数据资料得出结论:这些国家在1989~2003年允许同性恋结婚,结果危险陛性行为显著减少,同时为预防一些性病传播的社会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2.2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流产
2002年,李银河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专家意见时,提出同性婚姻的问题,建议将婚姻法中的“夫妻”一词改为“配偶”(性别不限),并向政协会议提交《同性婚姻提案》,建议在修改《婚姻法》时增加关于同性婚姻的条款,或设立独立的法规,准许同性婚姻,也就是说,允许同性婚姻,或者推进家庭伴侣关系,都将大大改善中国同性恋人群的处境,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附议人(30位代表)而未能成为正式议案。天涯杂谈对该提案发起声援活动,签名支持《同性婚姻提案》,该帖点击超过15000余次,跟帖数超过1500个。此后,李银河又两次发起相关主题的提案,均以失败告终。
就目前的争论情况来看,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实现。反对的理由并不仅仅是以生育角度来说事那么简单,在此之后还有更深的原因:如果承认同性婚姻,就抹平了男女两性的生理性别,从而混淆了男女两性的社会行为,使得性别区分变得毫无意义,“某一符号或象征只有跟其他某个对立符号或象征辨别开来时,才获得意义”,它们作为孤立现象并无意义,而只有作为集合体的成分时,才有意义,如《女诫》所说:“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无男女之分,也就无须强调强弱之别。在异性恋婚姻中,“单独的男人或女人,都成了不完全的一半,只有同另一方结合才能找到完整”,因此,在“人有男女阴阳之性,则自然有夫妇配合之道。阴阳化生,血体相传,则自然有父子之亲”中,无男女阴阳的自然区别,就不用夫妇配合的圣人之道了。
也就是说,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就等于解构了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性别文化,社会通过一整套系统和机制,使得个人在其中习得男或女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特征,接受性别规训,表现出与社会规范的要求相一致的男性或女性的性别特征,性别文化机制的最大作用就是区分男女,不仅是在生理层面,而且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进行男女的区分,从而形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同一种族和阶级的男人高于女人”。“一切分类活动都按此系统以对比偶的方式进行,可表示为一种单纯的二项对立(高与低,左与右等),一旦不能再形成对立关系时,分类也就终止了……由于同样的理由,超越这种二项对立将既无用处又不可能”,如《曲礼》所说:“男女不杂坐,不同榄,不同巾栉,不亲授。叔嫂不通门,诸母不漱裳……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没有男女对立,何来内与外、长与幼、高与低的行为约束,就会形成“姑姊妹女子与兄弟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的礼崩乐坏局面。
3中国同性婚姻的合理性与技术防护介入
中国同性婚姻要想获得法律承认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是否同性婚姻合法化就能化解艾滋病疫情扩散的威胁?答案是否定的,同性婚姻陷入合法与合理的两难窘境。也许在现阶段,从技术防护角度的介入是关注中国同性性行为的最佳路径:学术界专家和同性恋团体尽力促成同性恋群体和主流人群的交流,争取社会的宽容和理解;教育同性恋者坚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使安全性行为的观念被接受,主动争取得到尊重的权利。
3.1中国同性婚姻的合理性
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不仅是婚姻双方,还有因缔结婚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以及对双方行为、责任的约束,从性关系的专属性意义上说,要求婚姻双方互相尊重、彼此忠实等。传统的婚姻理想是,所有婚外性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一个人应当通过婚姻建立家庭,一个人经由婚姻确立对另一个人的持续的性接触权利,同性婚姻就是想通过婚姻责任否定性滥交,客观上减缓了艾滋病及其他疾病的传播。事实上,很少几个社会——大约只有5%的社会——禁止所有婚外性活动,因此,在法律和习俗皆认可的异性婚姻中,婚外情(性)、买卖春和多偶(二奶)一直是作为一夫一妻的补充形式存在,其中所引发的患病几率与艾滋病的流行病学传播途径是相一致的。
全世界艾滋病流行的发展表明,婚姻和稳定的单一性关系并没有保护妇女免遭艾滋病病毒感染,而且婚姻和同居关系下发生的性行为的频率要比不在一起生活的男女高。目前^们比较容易获得的有效减少性交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方法就是男用避孕套,但是,在很多国家不同文化下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婚姻或者固定的性伴关系中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其他性关系;在对性服务妇女的研究中也发现,性服务妇女与客人使用避孕套的频率高于与男朋友/丈夫的使用频率。
尽管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曾起过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法律在调整人们社会关系功能上
的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将法律作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力量更不可取,因此,同性婚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特别是其无法重构性别文化结构,因为男性常常把多性伴、不安全性行为视为男子汉的象征、特权和自由,使自己和性伴处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之中。
3.2技术防护介入
中国第三部门在应对艾滋病危机时,不是以艾滋病为由指责排斥同性恋群体,而是将同性恋纳入关怀视野;通过宣传倡导和行为干预项目,最大化地降低其高危性行为的风险指数。
3.2.1宣传倡导项目从1990年以来,学界出版了数部专著研究同性恋问题,召开了多次有关同性恋的专题研讨会,部分媒体对同性恋问题也开始予以正面报道,同性恋者开始以健康、积极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逐步让社会公众接受并尊重同性恋群体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如1992年,潘绥铭对北京等4城市同性恋性者的行为进行调查,该项目被列入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同年,李银河和王小波的同性恋个案访谈研究专著《他们的世界》出版。1994年,张北川同性恋理论研究专著《同性爱》出版。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对把同性恋道德化、疾病化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从伦理学角度论述了艾滋病与性及性少数人群的关系。199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直面转型期社会》一文,对潘绥铭在中国艾滋病高危群体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给予肯定,并肯定了有关特殊人群性学研究的价值。1998年,《希望》杂志第6期以21个页面推出《认识同性恋》专栏,发表了马晓年等专家和4位同性恋者的文章。2000年11月,“同性爱/艾滋病议题暨《朋友》项目研讨会”在京召开,该次会议实现了我国非政府组织与同性恋者的首次正面交流。2001年10月,《关于同性爱/艾滋病问题的共识与建议》向多学界、媒体发放,文献有约10个学科和社会人士90余人联合署名。2001年11月,“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召开,对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病流行关系进行专题讨论,10余位同性恋者参与会议,2005年,复旦大学为本科生开设《同性恋研究课程》,这是大学教育对同性恋的一种反歧视呼吁。
3.2.2行为干预项目由于受到男性主导型性别文化的影响,如同时具有多个性伴或经常更换性伴,在插入性性行为中较少使用安全套等,导致男男同性恋成为性病艾滋病的易感群体之一。1997年,张北川工作组开展对同性恋的调查研究,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2001~2002年,由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办公室资助的4个针对男同性恋人群的项目在云南、四川、北京和青岛启动。2002年6月,中国艾协对数省市40多位同性恋志愿者进行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如成都同志主导综合干预项目,就是旨在促进安全性行为,降低HIV感染风险。通过性病艾滋病宣传和技能培训,使大多数同性恋者在每次插入性性行为中都使用安全套,项目安全性行为观念得到普及,安全套使用率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