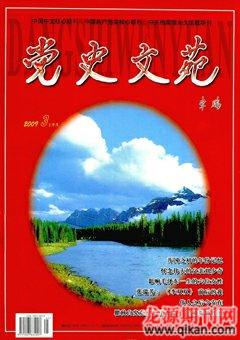张瑞芳:《李双双》前后的我
张瑞芳 王 岚

口述者:张瑞芳
采 访:王 岚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6日,
2008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张瑞芳家
张瑞芳小传:生于1918年。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跟随姐姐参加“民先”活动,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开始党的组织关系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9年2月取道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北平,10月,作为政协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之后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离开北影后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出演新中国第一台话剧《保尔·柯察金》,饰演冬妮亚。1951年10月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主演了《南征北战》、《母亲》、《家》、《聂耳》、《李双双》、《大河奔流》、《泉水叮咚》等影片。电影《李双双》曾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并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
瑞芳老师您好!很高兴见到您。来之前,我拜读了您的自传体新书《岁月有情》,很全面,很真实,也很生动,真没想到您的革命经历这么丰富,更没有想到您还有一位革命的妈妈。
我在书里写的很坦诚,都是真的,包括我的感情生活。其实我妈妈的经历比我丰富多了,她老人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总理曾对我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我娘对党的事业贡献多大,总理心里最清楚,他对娘的评价比对我们兄妹几个加起来都要高!1944年,组织上安排我娘去延安治病。在那里,她见到回去参加整风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娘的精神称赞不已,当面对她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一位中将夫人,像你这样,确实难能可贵。”新中国刚刚成立,日理万机的总理就抽空到北京法通寺的家去看望我娘。我娘去世后,他还为我娘的墓碑题了字“廉维同志之墓”。据我所知,总理为革命母亲题写过墓碑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我娘,另外一位就是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
瑞芳老师,您是我们敬仰的老革命家,老艺术家,一生经历丰富而坎坷,这些都在您的书里得到了体现。我今天来,还是想麻烦您再谈谈解放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的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这些我书里都写了。
是的,我看了,这真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录。解放后,您一开始是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又到中国青年艺术剧团,在话剧《保尔·柯察金》中饰演冬尼亚,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话剧,一直到1951年10月才到上影。到上影前,您还去向周总理作了告别?
我到上影前曾经给总理写过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奉中组部之命,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过了中秋之后十八九号动身去沪,矛盾了很久的舞台、电影问题,不解决自解决了。
我直接收到组织部给我个人的信,决定我的工作调动,恰在我被批准参加土改学习中途,使我觉得很突然,后来方知组织部早有此决定,剧院当局拖延未执行而已。
调动不调动,在我都没关系,主要是思想上解决问题,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我很惭愧我的工作做的太少,多工农兵的打哈哈、思想感情体验太差,对新人物的创造缺少把握,这是我目前最关心、急于下放的原因。年初我们曾有过两个月的工厂生活,使我们这群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收获。工人同志的集体性、主人翁感、对国家人民的负责态度、对未来充满信心等,扩展了我们的心胸和视野,在大踏步前进的欢乐的队伍中,确实觉得个人的事显得多么不足道。
此次参加土改未成,预备到华东局去争取参加,组织部也答应为我写信去,多在生活里锻炼改造自己。希望您将来在我拍的片子中能检查我这方面的成绩。过去您对我鼓励过多批评太少,这是我向您提得意见。
在北京虽然很难见到您,但总觉得随时可以见到您。现在离开北京了,觉得与您分别了,特向您告别问好,祝您健康!小超大姐好!

总理对我一直是很关心的,在重庆时,总理就是我的单线联系人,我的组织关系一直到解放时都在总理那儿。那次我去西花厅,总理留我作了一次长谈,我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坦露了我在感情生活上的困惑、烦恼,总理耐心地听我讲,在倾诉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我明白了要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不仅政治上业务上对自己要求要严,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有共产党员的好品格。
总理在重庆第一次和您谈话时,就勉励您做“共产党的好演员”,那么这次总理又对您提了什么要求吗?
总理对我一直是鼓励的。
您到上影后,拍了不少电影,在影幕上留下从影以来的许多的第一个,第一个工人形象(1954年,在上影黑白故事片《三年》中扮演纱厂女工干部赵秀妹),第一个民兵形象(1952年,在上影与八一厂合拍的黑白故事片《南征北战》中扮演女村长兼民兵连长赵玉敏),第一个母亲形象(1956年,在上影黑白故事片《母亲》中第一次扮演了一位革命母亲的形象),还第一次演了个喜剧人物,就是《李双双》中的农村妇女李双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李双双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这里也有好多因素。1959年后,全国各电影厂都有点不敢碰现实题材的影片,原因就是怕把握不好挨批,觉得还是拍历史题材好,特别是古装戏比较保险。《李双双》几乎是当时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戏中主角李双双是个性格开朗、是非分明、热爱集体的普通农村妇女,她一直斗争的对立面也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而是乡里乡亲,甚至包括自己丈夫身上的落后思想和处世方式。这样的内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拍到一半就下马,还是拍完以后再挨批?
现在的演员尤其是一些出了名的所谓大腕,常常可以同时接演几部戏。而您为了演李双双,从1961年7月9日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投入到河南林县的外景地,和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样的日子您觉得苦吗?
《李双双》是部喜剧,但我们拍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到河南林县拍外景,印象最深的是,吃得很艰苦,几乎一天到晚在喝南瓜汤和榨过油后的黄豆渣饼子。
从1961年开始拍摄到1963年影片获奖,这期间《李双双》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听说当年拍完后在厂里只是作为一个中等片子看待的?

《李双双》是1962年公映的。事实上,在拍《李双双》之前的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史称“新侨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前一个会上提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史称“文艺十条”,后一个会上提出《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在这次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特别号召电影要创“四好”,就是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而故事好成为被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这样一来,“典型人物”的塑造,就成为电影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那就是既要把握政治上的平衡,还要在艺术上表演精湛。我们拍《李双双》的时候正好是在这当口,虽然说不上是“新侨会议”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可以把这部电影看成是这次会议精神正确的一个佐证。
“新侨会议”后,直到1964年,电影生产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先后拍摄了一批好片子,如《甲午风云》、《阿娜尔罕》、《燎原》、《冰上上的来客》、《早春二月》、《红日》、《白求恩》、《霓虹灯下的哨兵》、《农奴》、《英雄儿女》等等,还有好多。后来,被称颂一时的“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其实也是这个时候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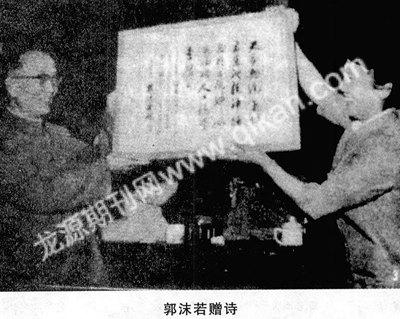
影片是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背景的,在那样严肃的时代背景下,却用轻喜剧的手法来表现当时农村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您演起来觉得有压力吗?
当年按照作者李准的要求,双双的性格就是要豁得出去,可是等我甩开膀子要豁出去的时候,导演鲁韧首先就紧张了,不时地提醒我,悠着点,悠着点!当时我们大家的心态可以用“火烛小心”四个字来比喻,前提是宁可温点,千万不要因为强调喜剧效果而落得个“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由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1968年1月发行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中的批判词为:抹杀阶级斗争,宣扬人性论)。因此在每个镜头前,到最后往往是采取最保险的方案,演起来真不爽,真是难受。好在影片公映前,拍了一段预告片,当时刚刚从学习毕业的吴贻弓在给导演做助理,他支持我放开来演,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双双又气又恨的捶打喜旺,“打败”喜旺后又哈哈大笑。后来影片中几组喜剧味较浓的镜头,原本是作为预告片用的。
周总理也很关心、喜欢《李双双》。
总理和小超大姐都很喜欢《李双双》。1962年6月,我们带着这部片子出访日本,回到北京后,一天小超大姐约我去吃晚饭,总理见到我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我当时心中一喜,又不敢乱猜好在哪里?就试探着问:是不是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总理有点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不能完全这么看,这个影片在艺术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你的表演也有新东西。听到总理对我艺术上的肯定,真是让我从心里感到欣慰!我演赵玉敏和赵秀妹时,总理就对我说:“你演了一个农民,又演了一个工人,都有点样子了。”这期间,我其实也为扮演现实人物有过抱怨,抱怨吃力不讨好,总理对我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不容易,因为人人都能看出他像不像。”可以说,在李双双身上,我的演技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因为在总理眼里,我一直是进步的。而观众对我的评价,就象总理说的那样,结论是还算像的!
1963年《李双双》荣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说明您在李双双身上确实下了不小的功夫。
作为一名演员,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是最起码的,也是应该的。《李双双》在当时能留下这么大的影响,和这部电影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一部尚属成功的现代题材影片有很大关系。不过,能获得全国各地那么多观众的普遍赞扬,也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记得那年我们带着《李双双》来到上海郊区的莘庄人民公社。
听说《李双双》来了,社员们兴高采烈,很多人提前做好工作,纷纷赶到俱乐部,七八百个座位很快就坐满了。在放映过程中,人们不断发出畅快的笑声,很多社员在剧场里就赞不绝口。看完电影,有十几位社员又留下来谈了不少感想。
这部反映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新生活的喜剧片,受到社员们的同声赞好。他们认为影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主人公李双双热爱劳动、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的思想品质,正是我国先进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影片,可以使广大农民进一步认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有位社员说:“我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生活真实,人物真实,演的就是我们庄稼人自己的事,看了很舒服。即使是落后的人物,我也要看。就拿喜旺来说,他爱劳动,只是因为有点怕吃亏的思想而不让妻子参加修渠;他自己没有损公利己的企图,但对别人贪公家小便宜的行为,虽然看不惯却又拉不开情面,不敢阻挡……像这样的人,在我们社员里还是常碰到的。”
有的社员提出:“要向李双双学习!”认为双双有着先进农民的典型性格,她能坚持真理,不怕困难,不向落后势力低头,又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电影开头的一场戏,因为孙有婆拿了公社的几块桶板,双双就和她斗争。有位社员说,李双双这种热爱集体利益的行为真叫人敬佩。谈到影片中评工记分的戏,大家发言就更热烈了。一位女社员说:“我们生产队评工分时,像影片中大风被批评、不高兴转身就跑的现象也有。记工分是容易得罪人的事,人家提议让双双的丈夫喜旺来做,她不但没反对,还动员喜旺当记工员。这样高的觉悟是我们要学习的。”生产队一位女干部:“双双当了妇女队长,在评补助工分时,自己虽有困难,但坚持不要公家的补贴工分,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已经是很难得了,尤其是她反对给不爱劳动的副队长金樵补助,更是了不起。在这点上,我们往往还存在着情面观点。”
好几位社员都谈到,李双双的可敬可爱,还表现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对丈夫她尊重、体贴,而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含糊,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丈夫提高思想。有一位女社员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时说:“坚持真理,不迁就落后,真不容易!像双双就是因为对喜旺进行批评,喜旺赶大车去了,双双哭了。但最后是喜旺终于认识到错误,她胜利了。而我呢?闹到丈夫差点要走,就再也硬不起来了。”说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所以后来我们曾经戏言:现在的演员戏多,过去的演员观众多。在第二届“百花奖”颁奖会上,郭沫若还给我题了一幅墨宝,郭老送我的诗句是: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姊妹,人人竟学李双双。当年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歌唱李双双》也是风靡大江南北。有几次,在北京的交谊舞晚会上,当这首乐曲响起的时候,总理总会向我走来,邀我共舞,这样的时候总会引起全场的一阵欢笑。周总理一边踏着舞步,一边哼着《歌唱李双双》的曲调,还一边说:“这歌词不好记,几段之间容易串行。”那样的时候,可以说是我感觉最欣慰的时候。

拍完《李双双》后,您又忙些什么呢?听说那段时间您获得了一个绰号,叫“赵丹的政委”?
“新侨会议”之后的一年,是文艺界气氛比较活跃的一年,也就是“文革”期间被重点批判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一年。拍完《李双双》回到上影剧团后,当时应云卫为剧团导演了夏衍的著名话剧《上海屋檐下》,赵丹导演了曹禺著名话剧《雷雨》。电影演员没有摄制任务时就排演话剧,这是个老传统,对内是为了不要荒疏演员的业务,对外则是观众特别喜欢近距离地看电影演员演话剧。我那时刚刚结束《李双双》的工作,就轻轻松松地去看《雷雨》的彩排。没有想到很快得到局领导瞿白音的通知,要我随话剧组立即去山东,担任演出队的领队,还幽默地对我解释,赵丹在艺术上“众望所归”没有问题,但组织纪律方面有时连自己都管不住,还要有个人专门管着他,这个职务只有你能胜任了。于是我就当了一回赵丹的专职“政委”,随团巡演,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赵丹的政委”的绰号。在山东演出时,我们总是被观众团团围住,演出前、散场后,剧院门口常常造成交通堵塞,后来不得不警车开道,车门直接顶着剧院门口的台阶,演员们才能顺利下车到后台,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点开演了。回上海后,我的“政委”任务完成了,《雷雨》开始在长江剧场上演,场场客满。记得著名话剧导演黄佐临看了电影演员们演的《雷雨》后,曾说过:你们能否到香港去演出呢?
《李双双》之后,您一直很忙,还拍了好些片子,但有的根本没有和观众见面就直接进入了仓库,比如《李善子》,广大观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部影片。
这部电影是根据朝鲜的一部现代戏《红色宣传员》改编的。这也是我们与邻邦朝鲜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他们排演朝鲜版的《红楼梦》,我们则排演中国版的《红色宣传员》,并且同时改编拍成五彩影片。《红色宣传员》讲的是一位朝鲜农村姑娘李善子,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大公无私,带领民青盟员,也就是民主青年联盟,相当于我们的共青团组织,发展生产,帮助落后乡亲,最后夺取丰收的故事。

李善子好象和李双双很像,您演起来应该得心应手的。
1963年4月25日,周总理来上海开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来看我们的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总理对我们戏的评价是“戏很好,其他同来的同志也说好。”他认为我们的演出水平是高的。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1963年下半年,我们根据总理的建议,组成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访问团赴朝鲜,团长是郑君里。当时主要是想通过拍摄现代版的《李善子》,学习朝鲜写现代戏的经验。去朝鲜之前,小超大姐还接见了我们,特别为我们定下了十六字方针,就是“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客随主便,时间不拘。”到了朝鲜,因为是中国的总理推荐的,所以我们享受到了很高的接待规格,连金日成主席也接见了我们。我们参观了所有外宾参观的项目,我们还要求到《李善子》的原型人物李信子的家乡去看看,后来李信子出来和我们进行了一次座谈。我们还和朝鲜电影《红色宣传员》的女主演宋英爱见了面。那次回国后大半年左右时间,由王炼编剧的剧本终于完成了,我就投入到正式的拍摄中。1965年,片子总算完成了,送北京审查。总理为审查这部片子,还特意调出郑君里解放后拍的其他几部片子,记得我们陪同看过的就有《聂耳》、《枯木逢春》等等,总理还对郑君里说,你是不是太过于追求唯美主义了?有一次,总理又约我和郑君里去西花厅。总理问郑君里:江青同志看过影片了?她说什么?郑君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她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完了……总理听他这么说,也就不再问了。
这部影片前后看过的人有:陈丕显、曹荻秋、曹禹、欧阳山尊、康生、江青、周扬、陈伯达、刘白羽、司徒慧敏、田汉等,但各方权威人士只是看,却听不到他们的反映。我曾经单独问过田汉同志,他也只是对我的表演作了个评价,说我演的李善子比他们演的更朴实。后来,总理还要郑君里和我带着片子到广东找正在养病的柯庆施征求意见,他一见我们进门就对郑君里说:这些年你就听他们的,不听我们的!柯老说的“他们”,当时我并不清楚是谁,只是不停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了一些重要指示。实际上这个“他们”指的是夏衍和陈荒煤,那时他们已经“靠边”了。所以,这部片子又过时了。
那时候已是“文革”前夕了?
是的。当时国内政治已经开始全面酝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准则了。这部片子是人家朝鲜的原创剧本,改也不是,批也不能,再加上那时国际关系比较微妙,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还要讲什么以情感人,互助、互爱和集体主义,似乎也太不搭调了,所以,这部电影也就无疾而终,被送进仓库,连观众面都没有见上。可以说,《李双双》之后,我一直在困惑中忙碌着,而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总理为此还对我说过:瑞芳,对不住了,耽误你两年八个月。
这个时间怎么算?
因为我从话剧《红色宣传员》到电影《李善子》,整整忙碌了两年零八个月。
粉碎“四人帮”后,我一下子又忙了起来,甚至比“文革”前还要忙。电影界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也是百废待兴。我除了拍戏,还多出来了许多其他工作,要招募、培训新学员,指导大型舞台节目、连续剧电视片、专题电影记录片的编导和排演,参与厂里领导层的管理工作……此外,还多出来一大块工作,就是频繁的社会活动,从全国党代会、政协,到上海市党代会、政协,还有妇联工作、外事工作等等,这些活动,对我是一种荣誉和责任,也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所以我丝毫不能怠慢,必须恪尽职守。
前几年您和亲家一起搞了个养老院,在社会上反响很好,现在还在正常运作吗?
正常开着,这都是我儿子和儿媳的主意。他们在国外经常去做义工,就是到一些养老机构去做志愿者,我儿子就想要把这样的理念带回国内。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和亲家一起开办了“爱晚厅”养老院,尽管很累,也不赚钱,但是看到住在那里的老人都很开心,我们也很高兴。
养老院是专对文化、文艺界人士开放还是向所有社会人员开放?
愿意住进来的老人都可以,没有身份限制。只是地方太小了,满足不了更多老年人想住进来的需求,不过,最近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
这是好事啊,可以搞搞大了。您也经常去吗?
经常去看看,和他们一起说说唱唱,大家都开心。
瑞芳老师,谢谢您接受我采访,衷心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