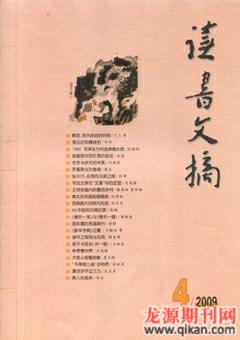西南联大的绝代风流
曾昭抡逸事
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我国化学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曾昭抡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传闻北大聘请他还有一连串奇闻轶事。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服务员,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朱收到那个陌生人的一封信,是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辞职书。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门类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位化学专业优秀的教授,还是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家,他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
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教授还热衷旅行,他在1938年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赴昆明。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为何去缅甸公路考察?一来因为滇缅路是当时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3月11日,曾昭抡由昆明动身,搭乘某机关的便车,踏上旅行的道路。虽然只有10多天时间,但也正如他在游记中提到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因此,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他的《缅边日记》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他多次野外考察,并养成撰写游记和日记的习惯,《缅边日记》是其日记中的普通一种。
据说,曾昭抡研究问题经常到了忘我的地步。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把电线杆误认为自己的同事,急于把新的发现告诉他。类似的情况还有,他离开实验室,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经别人提醒,才把雨伞撑开,而衣服已被淋湿了。
曾昭抡不修边幅,穿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布大褂,有时套一件似乎总是掉了纽扣的粗糙的白衬衫。旧鞋子总是露出脚指头和脚后跟,头发乱蓬蓬的。只有极少数场合,比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才会理发剃须。有一次,为了及时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他从田野考察回来,仍穿着沾满泥点的长袍,带着呢帽,穿着草鞋,他踏上讲台,与化学协会董事会其他著名学者坐在一起。
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当时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于是,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可顾了吃顾不上穿,上课的时候脚上的皮鞋常常破着几个洞,这位肥皂专家也无可奈何。曾昭抡在日记中提到联大教授的生活窘况。1940年7月6日,曾昭抡在日记中记录:“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补贴。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工钱,也一并贴入,同时还当卖东西,以资补助云。”
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是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俞大絪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曾氏夫妇俩关系颇为紧张。她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据说,曾夫人坚决要求,凌乱邋遢的丈夫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
曾昭抡虽然是曾国藩的嫡传后人,但他打破了忠君思想,毕生追求民主政治,是中国民主同盟最早的中央委员。
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留学英德主攻考古专业,归国后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国际考古学界很有名望。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在大理设工作站,曾昭燏曾在此从事考古工作。1941年,曾昭抡考察缅甸公路时经过大理,兄妹相逢。曾昭燏在此从事考古工作,她为曾昭抡介绍大理的掌故,一起游览大理城西北角的三塔寺,看南诏旧城遗址大理的古碑。
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等职。曾昭燏对中国考古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不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并且极力反对将出土文物运往台湾。1949年4月14日,她还联合其他人士公开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收回。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然而,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曾氏家族和俞氏家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受到打击和残酷迫害。1957年,曾昭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降级下放武汉大学。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他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遗憾的是“文革”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而在曾昭抡去世前,他先后失去了妹妹和夫人。
1964年3月,曾昭燏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抑郁症。12月22日,她从南京郊外灵谷寺灵谷塔跳下身亡。
1966年8月24日,北大西语系俞大絪教授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张奚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八字胡须,衣冠楚楚,手不离杖,做事一丝不苟。
张奚若是一位可圈可点的教授,西南联大正是拥有这样的大学者,才能称之为“大”———大学之“大”,大师之“大”。如果没有这些个性独特的教授,“大”就无从体现。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教授,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引领了时代风骚。张奚若(1889-1973),原名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现代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
在易社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张奚若的精神素描和生活肖像。他写道:
张(奚若)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有位同事回忆,他是条“硬汉”。然而,他演讲时,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极富魅力。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概论”课堂上,他狡黠地故作无意发表风趣的评论,然后继续他的讲演,好像没听到学生们的笑声。
称张奚若为“硬汉”,不是联大时期张的同事,而是张的朋友———诗人徐志摩。徐志摩非常欣赏张奚若的个性,他认为:“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个“硬汉”怎样给学生上课呢?张奚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也在北大兼职授课。有一次,他在北大上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早上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左右,然后在下午三点继续讲,直到五点结束。张奚若能包容各种观点,但明显偏爱民主思想。臣服于黑格尔严苛的批判,但他讲授卢梭时充满激情,极富感染力。据何兆武回忆,英译本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列宁《国家与革命》是张奚若指定的必读书。
在西南联大,他任政治系主任,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和吴晗讲课一样,张奚若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抨击腐败,针砭时弊。
让我们听一听张奚若在课堂上发出的声音,据何兆武回忆:
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鄄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
张奚若还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牢骚,是针对他的同事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当然,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何兆武和听课的学生,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1941年,冯友兰的学术新著《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
张奚若的课在联大也是以严格而闻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者并不能得高分,因为他最欣赏独立思考,哪怕与他的观点对立。考试成绩公布时,在80到100分这一档几乎没有人,有些人的成绩却在30到50分之间徘徊。有一个让学生谈之色变而又无限倾慕的掌故。1936年秋,只有八位极为勤奋的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他却给张翰书(后来成为台湾立法委员)九十九分,外加一分得了满分。这件事在北大、清华,包括两校校长在内,人人皆知。
抗战初期,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发现重庆的当权派“独裁专断、腐败无能”,意识到这个参政会不过是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装点门面,就拒不参加。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事实上,张奚若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而引起的民主运动中转向。不归属于任何党派,是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1946年1月1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张奚若为此致信重庆《大公报》发表声明,宣称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这个声明,也具有“硬人”的风格:“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初,就在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
张奚若是英美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乐于告诉学生,“人家说胡适之中了美国的毒,我就仅次于胡适之了。”战时,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坚定分子。课堂上,张奚若告诫政治学系学生要成为社会改革者,而不是紧盯着官府职位。这是针对报考政治学系的新生说的,他大浇冷水———想当官的不要来,即使四年,也培养不出政治学学者,大学只是教给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他说,大学毕业如果做不了社会改革者,那至少要成为正派的政治学者,即便当平民百姓也比一心想做官强。
张奚若在北大、哥伦比亚和伦敦经济学院受过教育,英语流利,法语尚可,张奚若绝对见多识广。妻子杨景任是陕西省遣送留学的第一位女生。夫妇俩极为好客,经常英汉并用,与博学的客人交谈。联大最优秀的英语讲师之一李赋宁在这种交流中脱颖而出———使他对自己的专业和异域文化更加熟悉。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金先生的这番话,贴切地概括了自己“最老的朋友”。
张奚若最令人可敬者,莫过于他的直言的风骨。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联系到张奚若的言行,我们不得不慨叹,像这样的“棱角先生”、这样的“硬汉”,只有到历史中寻找了。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十元钱呢。
在此一提,叶公超和他的夫人袁永熹。上世纪30年代初,叶公超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袁永熹喜结良缘。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直单身的吴宓教授常在叶公超家中吃饭,并和叶家的孩子嬉戏。感受到家庭生活之乐趣,多少对吴宓的生活是一种补偿。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叶公超)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叶公超的追求者———引者注),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吴宓不但爱慕陈仰贤,而且也欣赏袁永熹。许渊冲曾在叶公超先生家见过叶夫人,他在《一代人的爱情》文中写道:“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许渊冲提到的袁永熙,就读联大经济系,是地下中共党员。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读联大时,和就读于联大地质系的陈琏(陈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再回到“叶公超太懒”这个话题上来。有人认为,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懒”。1941年叶公超离开西南联大,到重庆外交部任职。那一代学者从政,鲜有成功的个案。连王云五也说,自己从政不过是客串。叶公超的这个转型,很难说成功,倒是接近悲剧。
联大教授爱昆曲
在战时的昆明,联大的教授爱好昆曲。笔者收集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先来了解一下昆曲。昆曲原称昆山腔,简称昆腔,最初是江苏昆山一带民间流行的南戏(宋、元时流行于南方的一种戏曲,为区别于北方的元杂剧而称为南戏)的清唱腔调,数百年来对许多地方戏曲都有深而且广的影响,是我国最古老的声腔之一。因此,一般文人学士都喜欢把昆曲作为古代戏曲音乐的活化石来欣赏、品味。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之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昆曲知音,浦江清、许宝马录、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人,他们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并任社长,定期雅集。
在战时的昆明,从北平而来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不乏爱好昆曲者。我们不妨透过老舍到昆明访问时的日记,看看联大教授们战时的文化生活。
许宝马录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地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叁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老舍文中提到的联大教授,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钱晋华女士是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著名语言学家,在联大开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的夫人。罗莘田是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罗常培去世后,老舍在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他唱昆曲:“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查浦江清1943年日记,也见有教授们唱昆曲之记载。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
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对唱曲要求高,故有“不甚佳”的评语。
去电台唱《游园》的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去了重庆,从《梅贻琦日记》可知,梅贻琦出差到重庆,张充和常来拜访,有时,为梅校长清唱昆曲。
与昆曲相比,查阅到的联大师生与京剧的资料少。但毫无疑问,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们喜欢京剧,像杨振声、梅贻琦等人都爱好京剧。
秦泥执笔的《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纪实》文中提到,当时娱乐活动极端缺乏,1941年春节,学校放假唱了几天京戏,戏班子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自己组织的。在叙永分校就读的张之良在《我的大学生活》文中也写道:
春节到了,由杨振声教授支持唱了五天京戏。记得有一个剧目是《苏三起解》,是工学院姓王的同学主演,他在北平时,从小在家请家庭教师教戏,所以表演唱腔均好。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参加中印空运工作,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选自《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刘宜庆 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