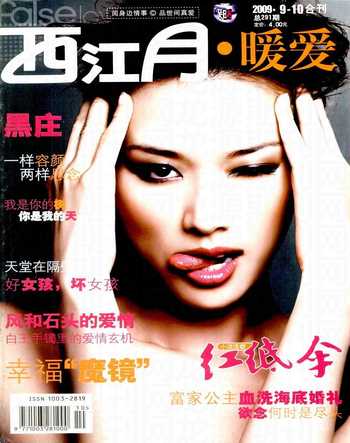红纸伞
谭 易
[上期回顾]娇蕊被和张灯的纠葛在红纸伞中灰飞烟灭。墓园中一个神秘的面相丑陋的哑巴老人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在所有的神话和传说中,鸽子都是爱的信使,和平的象征。
这群鸽子的白天而降,无疑给清凄的墓园平添一份爱意交融,一份悠闲恬静的意象。清明时节或者天气晴和的日子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凭吊了亲人们的墓碑之后,总要徒步走到哑叔的小屋前,看绿色的坪地上灰灰白白的鸽子起起落落;一些胆大调皮的孩子,一些颇具雅趣的女学生,还走上前来随着鸽子的蹦跳而蹦跳,欢呼雀跃。这样的时候,哑叔就拿起笤帚去清扫园中的尘屑,默默地,决不张扬,决无怨尤,一任世事如水,一任红尘多娆。
哑叔的小屋就筑在墓园里居高临下的那块悬崖畔上。
高高的青石台阶水光滑溜地绕下来,从墓园中间斜穿而过,底下就是涧溪,有小桥。
在1952年的那个秋夜,在那样一声沙哑破败的秋雷过后,哑叔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风声雨声,听到了风雨雷电之中那一声划破雨夜的婴儿的啼哭。
哑叔点燃了小屋的光亮,照耀一园的清凄。
守墓半年,哑叔闭眼能识墓同路,只需披上那件草蓑衣,打上那盏气死风的雨灯;只需沿着那条滑溜溜的青石小径直走下去,三百六十级台阶,左转。
盘亘错节的古槐。
小桥流水。
石桌石凳。
哭声嘹亮……
第四节玫瑰精灵
那是一个婴儿。
四个月大的样子,粉嘟嘟的一团肉,裹在花团锦簇的襁褓之中,石桌之上。在霹雳闪电之中,在一抹苍白刺眼的光线里,看得见襁褓上绣着的一团红玫瑰。小家伙猛扯着嗓门在哭,挣红了脸,眉眼秀气。是个玫瑰花瓣一般的女孩儿,她的身上罩着一把红纸伞。弄不清这风雨交加的墓园,怎么会长出一朵红纸伞来?怎么会生出一个玫瑰精灵?就像一棵鲜蘑菇,一根小草,在夜雨的滋润里,窜出地缝。
也许一切就发生在火光电石的刹那,发生在不为人知的瞬间。也许一切明明白白地发生了,那一刻大地在痉挛,黑夜在撕裂,墓园里的亡灵们也闭上了眼。也许哑叔心知肚明,哑叔不说,谁也不知道。只是那满目的红,刺痛了哑叔的眼。红纸伞,在小桥流水的叮咚声中;红纸伞,在古槐树的观望里;红纸伞,在女孩儿声声不绝的泣音里。如水的竹骨,如水的伞面,绣满绿色的国画。还有一阕《蝶恋花》的断句:
四季风雨四季秋,望断红尘,谁染霜天晓?
第五节秋晓
那个生命,像一枚带露的玫瑰花瓣,又像一只还未长出羽毛的乳鸽,带着初涉人世的莽撞,轻裹在一块雪白的柔缎之中,外面覃着绣满了红玫瑰的襁褓:一把红纸伞,在风雨交加之中,为她遮住寒冷:而眼泪和哭声是与生俱来的,像极了女孩儿花蕊一般的娇嫩和伤心。
她的名字叫秋晓。是哑叔根据那阕《蝶恋花》的断句首尾两句末字相连而成。在那个秋天的雨夜,哑叔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幼小的生命。当哑叔粗糙的手,捧回那份诚惶诚恐的颤栗:当哑叔的一袭草蓑衣,在红纸伞的摇曳中,一步一步地延展着雷电的呻吟:当崖畔上的墓园小屋畅开了扑面而来的风露情怀,接受一阕妄自残缺的所有的动心与心动,所有的心爱与爱心,便全交给了这片墓园;所有的故事与传奇,都随风雨而至,由一把红伞笼罩的缘字说尽。
哑叔重新拨亮了灯捻儿,让那盏灯亮到极致,那个孩子在第一抹光明巾睁圆了眼睛:哑叔又点燃了一支蜡烛,让烛光的扑闪去撩起棚壁的温暖,那个孩子在第一丝温馨中咧了咧嘴:哑叔又打开了惟一的手电筒和仅有的一盏风灯,让刺目的光柱和雪亮的灯影穿透雨夜的沉闷,那个孩子在光影交叠中绽开笑靥。当满屋都是光明、满园都风住雨息的时候,哑叔撑起了那把红纸伞。哑叔转动着伞柄,让红伞绿画和《蝶恋花》像梦一样地飞旋,哑叔看见那个睁圆了眼睛咧开了嘴巴绽开了笑靥的孩子突然问咯咯咯咯乐红了脸。哑叔的红伞旋转着,映出一片火红的云,映出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精灵永恒不变的天。女孩子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成长。在小屋有限的空间里,哑叔腾挪出了一个小小的属于女孩的世界。
五坪大的地方,素色的墙面,四处点缀着脱脂脱水处理过的红玫瑰,永不凋谢,留着这个季节枝头上的最后一抹灿烂。与它相互对应的是斜搭在摇篮上的那块披风,白色的缎子,绣着一团一团的红玫瑰。秋晓的摇篮是哑叔用黄藤竹枝银柳条编织而成,镂空的菱形图案,滚边纠扭是一溜“回”字型纹理,缠绕着“万”字型的龙脊,底下铺了松松软软的清火败毒的菊香屑和苦艾叶。那块如雪轻柔的缎子是一直贴身铺盖的,冷时加了织锦缎的玫瑰披风。而红纸伞是一直罩在摇篮上的,秋晓在咿咿呀呀之中对着它笑,也对着它哭,哭哭笑笑都是赏心乐事:而一旦远离它,就似有千般焦躁万般不安,好像是她的灵魂,揪扯着混沌如梦的前生和诚挚如初的牵念。
这一年的冬雪如期而至。墓园寂寥,小屋却温暖如春。秋晓在哑叔的抚育喂养中长成了唇红齿白的乖宝宝模样,一双眼睛黑黑亮亮扑扑闪闪的,却不知咋的再也不哭不笑,神情郁悒,表情肃然,似乎有着愁结不断的心事和不可名状的忧伤。而小小年纪所表现出的这些情绪又分明是荒诞不经的。她常常一个人对着那顶红纸伞发呆,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国画,眼睛里的意象一会儿深远,一会儿悠长。那一天下大雪,厚厚的积雪封住了小屋的门,哑叔还躺在床上,四周一片静谧。突然就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你见过红纸伞吗?”哑叔吓了一跳,这是谁在说话呢?起来推了窗户,外面是一片白雪皑皑,鸽子在巢里唧唧咕咕,几只小麻雀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无人踏雪,雪地无痕。于是又关了窗户,重新在被窝里躺下。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你见过红纸伞吗?”哑叔被吓得毛发都支楞起来,就再也不敢睁眼,屏心静气地,捕捉那声音的来源。红纸伞罩在摇篮上,有酣酣的眠声,女孩儿还在睡。其它再无动静,也许是错觉吧?
第二年的春天没有雨。只在清明节的那一天降下一场又浓又湿的雾来。早晨打开门扉,就有如烟如云的潮气滚涌而进。哑叔听到秋晓在摇篮里轻轻咳嗽:“哎呀真呛,这么早就开了门。”哑叔被惊得目瞪口呆,不敢回过头去。突然想到去年冬天下大雪的日子,那样一声惊为天籁的声音:“你见过红纸伞吗?”哑叔知道了这是相同的声音,都是秋晓。
这样的女孩,是人?是鬼?是狐?是仙?哑叔陷入一种深深的迷惘之中。而秋晓的声音却在身后清晰地响起来;“你见过红纸伞吗?”
哑叔回过头去,只见秋晓正从摇篮里爬起身。那块雪白柔软的缎子,轻轻缠绕在她身上,她光着脚丫,光胳膊露腿地,脸上是一种天使般的圣洁与美丽。那把红纸伞被她高高举在头顶,云遮雾罩之中,是那种超凡脱俗的孤绝和飘忽难寻的诡异。
秋晓说:“你见过红纸伞吗?它有如水的竹骨。如水的伞面,绿色的
国画。”秋晓说:“红纸伞的故事就在那幅绿色的国画上,那是九个女孩的故事。”秋晓说:“你知道我是第几个女孩吗?”
此时的秋晓只有十个月大小,此情此境之中究竟是人是鬼是狐是仙,究竟有过怎样的荒诞不经,就像这个早晨挥不去散不了的雾气与烟云,飘飘洒洒地弥漫于哑叔的记忆里。没有人有机会向哑叔当面考证,或者那一切果真是他的冥思妄想或者错觉呐!重要的是那一把红纸伞是真实存在的,墓园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有一个细节是最能经得住考证和盘究的,那就是秋晓是在这一年的清明节自己爬出摇篮学会走路的。那一天来墓园祭奠亡灵的人们都看到了这一幕。十个月会走路没什么稀奇的,十个月会讲红纸伞的故事却显得极不可信。还有一点墓园附近青云小学的老师和同学可以做证,那就是秋晓在十二岁时才入学,那时她是小哑巴。没有人知道秋晓是那个九生轮回的故事中的第几个女孩子,却有人知道哑叔在放飞鸽子的同时也放飞了一个秋晓。
第六节和鸽子一起飞
秋晓懂得鸽子的语言。发现这个秘密的不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哑叔,而是清明节那天墓园里的一帮扫墓人。秋晓是在那一天的大雾弥漫之中自己爬出摇篮的。
秋晓摇摇晃晃地走出崖畔上的墓园小屋,走出哑叔的惊舁表情的时候,太阳正透过古槐树鹅黄转绿的树冠,千丝万缕地照射下来。她的柔软挡风的自衣和红纸伞,便在七彩阳光的折射中呈现出一种虚意幻奇的景致。浓雾浊烟是在一瞬间散失殆尽的,鸽子却缘定三生,急急忙忙地赶来。它们从墓园的各个角落,从树梢上树杈上扑愣愣地飞落,在小屋前的坪地上聚集。它们先是接受检阅似的组成方阵,然后就表演似的在低空迂回而飞。
人们是在走进墓园的第一眼就看见了漫天飞舞的鸽群,看见了那个手擎红纸伞的小女孩的:而女孩随意的一个动作,一个手势,都有成群结队的鸽子积极响应,一片片灰云,一片片白云,起起落落之中,自有默契,灵犀相通。
所有的人都围拢而来,沿着麻石小径走向守墓人的小屋。
那个小女孩俨然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手里转动着伞柄,让那一抹耀眼的红红绿绿飞旋出迷离的映象,而所有的鸽子迷惑在这一抹映象与迷离之中:后来,小女孩有点累了,放下了手里的伞,鸽子们便在她的头顶上,肩膀上,手掌心上停落了,围绕成一个圆;小女孩扬了一下她的手臂,所有的鸽子便哗啦啦一轰而起,在高空的气流中鸣响了漫天回旋的哨音:谁知女孩儿又举起了红伞,向远处招了招手,那些渐飞渐远的鸽群就拖着由远及近的哨音噼噼啪啪地全飞了回来。人们看见小女孩在欢快跳跃,人们听见小女孩在欢快跳跃的同时发出了唧唧咕咕的鸽子的呢喃。
哑叔站在人群的熙熙攘攘和惊乍感叹之中,亲眼细瞧了这一切的发生。有点搞不清楚,那顶红纸伞,那伞下的白衣女孩,那种和鸽子一起飞的飘飘欲仙的感觉,翱翔的感觉,是否又是错觉?
只是这一年的清明节,许多到过墓园的人都目睹了这一幕情景,那个小女孩,就住在守墓人的小屋里,不到一岁的样子,却挟裹着无从捉摸的一身神秘,他们说那或许就是妖气或者巫气。
第七节哑女
哑叔的耳边总是回响着那句话:你见过红纸伞吗?每到下大雪的时候,或者起大雾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总是敲击着他的耳鼓。哑叔终于肯定了这一切只是他的错觉,是一片痴幻中的幽思冥想。因为他再也没有听见她开口说任何一句话。
当秋晓真正变做哑女的时候,她迷上了画画。那时秋晓才只有三岁,她就那样无缘无故拿起笔,无缘无故地画起了画。
秋晓的处女作足画在墓园小屋里的白墙上的,一把伞。
哑叔弄不明白这个女孩子怎么就突然间迷上了画画,怎么就轻而易举地画出一把伞来?那简练的手法,明快的线条,精美的构图,在很随意的勾勒之中脱颖而出的绘画才气,着实令人惊叹。尤其是伞面上影影绰绰显现出来的几个女子的图案,特别具有国画的味道。哑叔忽然想到两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云遮雾罩的墓园小屋,似梦非梦之中小女孩描述的红纸伞绿国画:“那是九个女孩的故事。”哑叔不由得去数那图画中的女子,不由得呆了:真的是九个。耳边好像又响起那样一声佻俏的问:“你知道我是第几个女孩吗?”
秋晓真的是伞面上的女孩吗?为什么她总是喜欢这样的一把红纸伞?这一切,究竟是前生的预兆,还是后世的轮回?是一场劫吗?一把红纸伞,不仅是雨夜墓园哭声嘹亮的一个遮蔽,更有一个故事存在。
那是秋晓自己的故事,哑叔的故事。谁也走不进,谁也猜不着。好像冥冥之中总有什么是已经发生了的,有些已经预先感知了结果,只等着一个过程,去牵起好多人的心事。到底是些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心事呢?是那支悠悠吹奏的笛吗?
第八节笛
秋晓和哑叔同时听到了那声笛音。这一年秋晓已经十岁,披一头柔柔长长的秀发,嘴唇未点而含丹,一张小脸苍白得近乎透明,凝脂一般,望上去吹之可破,弹之欲碎:乌漆漆的大眼睛,似罩着千重愁万重怨,隐在那样孤苦无依的忧郁神色里,像是凝住了几世几劫的痴情和伤痛。秋晓依然不会说话,却懂得和哑叔用文字和绘画交流感情。秋晓喜欢一个人在墓园的每一个坟冢之间游游荡荡,喜欢打着她的红纸伞站在小桥边听涧溪的淙淙,听流水的轻吟——那儿有一棵四季萧萧的古槐,有青青的草和麻石的桌凳。秋晓喜欢躲在古槐树的背后,面对着蜿蜒而过穿越墓园的青石小径,画一幅终年不变的画——那是她心里的故事,情景中的灿烂。那个白衣少年就是在一个雨后的黄昏,踩着满地潮湿,匆匆走进墓园,走进她的眼睛。那一刻钟,正有耀眼的夕阳透过薄薄的天边云,霞光万道地射出,一条彩虹横空而过,一头挂在遥远的天际,一头挂在墓园的树梢;那一刻钟,所有的鸽子都在墓园里飞起来,抖动着它们被雨水打湿的翅膀,噼噼啪啪飞出林地,漫天的鸽哨在空中回响,漫天的云霞在起伏翻滚:那一刻钟,秋晓正在画她的飘渺的心事——红纸伞有两把,一把画在白色的画板上。一把遮住了扑面的潮湿。而所有的动心就从这一刻开始了。随着白衣少年匆匆走进墓园。随着那一声悠悠扬扬的笛音。
第九节水粉画
那个少年开始频频地出现在墓园里。相同的黄昏,不同的日子,无论是色彩斑斓的盛夏,还是黯淡邈远的秋季,总足一身纯白的衣裳,手里一枝竹笛。当他一步一步地踏着青石小径走过来的时候,他的颀长挺拔的身材和清秀俊美的面孔,便出现在秋晓的画板上。秋晓画起淡彩淡粉的水粉画。恬淡的调子,闲适的心情,清新的韵致,色彩感觉全是红白黄绿的写意和典雅舒缓的晕染。秋晓终于走出了红纸伞的孤寂意境,让阳光的亮点也随着这个美少年的出现。折射出内心的姹紫嫣红。心事就在一瞬间变得空明澄澈起来。一如笛音,悠悠扬扬
直往心窝里去,所有的震颤都穿心而过——好像记忆里的一个老朋友,娓娓道来生命里亘古不变的熟稔;好像一滴水,晶莹剔透地滴落在心海中,就此融进那无边无际的涟漪。迷惘不再有了,灰色的天空不再有了,心事告别了阴冷的墓园,告别亡灵的牵念。而眼泪是后来才有的事。是那日的午后笛声又起,委婉的笛音随着画板上的阅读,一次次沉醉不归:是漫天的鸽哨也驱散不尽的少女情怀。一不小心就打翻了红白黑绿的颜色,乱了心,也乱了画板上的描绘;是第一次蓦然回眸的惊悸,感觉里全是涧溪的水流,静悄悄沁透着纯真。
少年在桥栏上坐下,背倚着一脉涧溪,任流水淙淙,横笛而吹。近在咫尺。秋晓却再也不敢看他。只好躲在古槐树的阴影里,看调和的颜色,捏不住抚弄丹青的那一支笔。那一把红纸伞已被她悄悄收起,远离孤绝,远离身世,远离伤逝的心。
第十节读
这一定就是命运里千呼万唤的那个人了。不然,为什么,当他出现的时候,久雨的天空会有那样一种瑰丽,灵性的鸽子会为他而腾飞,笼罩了前尘后世的红纸伞会为他而悄悄合起。不然,为什么,当他的笛声响起的时候,她会觉得那是自己的心泣。少年一如既往地在墓园里出现。风雨无阻的四年过去,秋晓成了十四岁的少女。他们在各自的领地里吹笛做画,一个是小桥流水,一个是古槐石碑,中间隔着很近的距离。他们不相往来,不曾交流,也从不缺席于每一个日落黄昏。秋晓喜欢在这样的情景中画淡淡的水粉,把每一声笛音都画进她的画里。
那少年绝世英俊,剑眉星目的样子,个子一年比一年高,有了茸茸的胡须和喉结突生的男子气:当他吹笛的时候,嘴唇总是抿得紧紧的,一双眼睛很湿润,忧郁地盯着长笛上红璎珞的飘带,不肯转移视线。而当他停止吹笛的时候,总是静静地抬起头,目光游离,转过墓园里高低起伏的坟冢,参差不齐的十字架,大小不一的石碑,看守墓的哑叔,拿着扫帚默默地清扫落叶,蹲下身来极有耐心地喂养鸽群。当他看到秋晓的时候。他不禁惊诧于这个墓园里长大的女孩夺人心魄的美丽,那是一种令繁华失色、让星辰黯淡的眩晕。当她披散一头长发,在古槐树的阴影里安详作画的时候,她那苍白清秀的小脸,流淌着无由的幻灭神色。似是凝聚了太多的伤心太多的绝望:红唇是她惟一的亮色,却从不说一句话,不露一丝笑意。她就是一尊恬静而优雅的雕像,弄笔做画的专注表情即使写在脸上。也在画笔传神之时幻化出幽迷。她在画什么呢?她知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一幅水粉画?少年斜倚在桥栏上,沉沉地想着心事。
他无法把这美丽的少女和那个丑陋的守墓老头联系起来,他们是一对父女吗?曾经看见他们在小屋前的坪地上给鸽子喂食,老人穿一身灰色制服,目光柔和地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盆谷粒和麦麸:女孩穿着简单而随意的白衣裳,把手伸到老人端着的盆里。捧起黄的谷粒白的麦麸轻轻一扬,那手臂扬起的侧影像仙子般轻盈,表带迎着起起落落飞旋而来的鸽群翩然起舞。这样一幅父女喂鸽图,他看过之后就再也不能忘记了。潜意识里总想搞明白,这样的女孩子,她是怎么出现在墓园里的?她是不食烟火的吗?她真的是哑巴吗?她那样冰雪聪明的模样,怎么会是个失聪的人?那么她是不愿意说话了?或者是她整日面对一个真正的哑巴,自己也从此退化了说话的功能,变成了另一个哑巴;或许她已习惯了无声世界的寂寞,把完美的自我封锁在沉默寡言的外表下面:或者,只是因为她找不到可以跟她说话的人。
无论她是不是哑巴,她都是可爱得让人生怜的女孩子。看她那么忧郁地走过墓园,看她苍白的脸颊,赢弱的身体,看她终日沉迷于画板的执著,他怎么也想不透,小小的她,究竟有多少缠绵的心事淬心的秘密压在心头?一阵鸽哨掠过天际,扑愣愣,一群鸽子从树梢盘旋而回。守墓的老头在一片霭霭暮气中敲击着鸽盆,喂鸽子的时间到了。
女孩子收拾起画板,从他的视线中走过。
第十一节忘尘
秋晓经过墓园小桥的时候,那个少年还在桥栏上发呆。秋晓就是在经过桥栏的时候,被他一把捉住了手。
“你叫什么名字?”少年问。秋晓在一瞬间涨红了脸,手被钳住,无法挣脱。“快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少年稍微有点霸道,捏着她的手,执着地追问:“我不相信你真的不会说话,快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秋晓是一字一句听清楚了少年的发问,心里的挣扎像小鹿在跳跃着,好多好多的愿望和焦虑像突然长出了翅膀,想飞,却怎么也飞不出胸膛。她想说我叫秋晓,我能听见世间任何一种声音,我不说话是因为我的心还在沉睡。可这些无声的话语只是一群扑腾着翅膀的小鸟,在她心头乱飞乱撞,却找不到飞向天空的路。而画夹和画稿却在这个时候散落一地。少年的肖像散落一地。一颗男孩子的心,就这么被幸福地撞击了一下,不敢辨认纷纷扬扬的画稿上淡粉淡彩的自己。
秋晓默默地蹲下身去。拣起散落一地的画页。那是她四年的心血,是她成长的岁月里眼之所见心之所依手之所属的一切:是初相识的心动,是不相忘的回眸,是漫长的等待中每个黄昏的殷殷衷情,是小桥流水笛声笛韵的心醉。不仅是画,更是一种心语,一种切肤的痛,一种前缘未了的债与殇。眼泪就那样夺眶而出,再也擦不干。
少年不敢太霸道了,俯下身子捧起了女孩的脸,心里那么幸福,有无数的喜悦和欢快,撞击着,撞击着,继而又被她的眼泪打湿了,淹没了:“告诉我,你画了多久?这么多,这么多的我?”秋晓抬起了头,伸出四个手指头。少年怔住了:“啊,四年?!”
秋晓点头。少年明白了,从见面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画这些画了。那时候,她总是打着那一把红纸伞:他不知道她正躲在伞下画他,他只记住了红伞下她苍白得凄楚而绝望的脸。现在,红纸伞已被她悄悄收起来,画在画板上的,纷纷扬扬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一个从她视线里穿行而过,在涧溪小桥横笛而吹的陌生少年。少年扶起了秋晓,凝视着她的眼睛:“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秋晓拉起他的手。在他手心一笔一笔地写:秋晓。男孩子笑了:“秋晓?!多好听的名字!”“你能说话的。”男孩说:“你一定能说话的。你一定要学会说话,一定啊,一定!”男孩在秋晓的手心写下他的名字:钟望尘。
第十二节醒
仿佛有根针向心窝子里轻轻刺去。秋晓只觉得微微一疼,竟愣住了,但觉得钟望尘这三个字好熟悉,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又像曾经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过。抬起头来,只见那名叫钟望尘的少年已经走远。他刚才站立的地方有亮晃晃的东西在闪耀,捡起来一看,是一枚徽章,印着“北国艺术学校”的字样。秋晓知道那一定就是他上学的地方。她以前总看见他把它戴在衣襟上的。秋晓怔怔地愣了半天,若有所思。她在心里一遍遍地呼唤,小声地呼唤:“望尘望尘望尘望尘望尘……”一路跑回家
去,胸口处,心窝里,一直隐隐作痛,却又痛得那么亲切,那么温柔,痛得她想哭,想笑。秋晓第一次有了如此强烈的痛觉和更为强烈的想说话的欲望。蜷缩在小屋里属于她的小小角落,突然间就看见了那把红纸伞,它已被冷落得太久了,也像她一样蜷缩在角落里,蒙了灰尘,黯然神伤。拂去浮尘,秋晓将红纸伞慢慢撑开,又慢慢合上:慢慢合上,又慢慢撑开;后来索性用两手搓转伞柄,让伞在头顶飞旋,让绿色的国画在头顶飞旋,让《蝶恋花》的断句在头顶飞旋:
四季风雨四季秋,
望断红尘,
谁染霜天晓?
秋晓,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来自这把伞。可是,总觉得还有什么滞留在红伞面上,是什么?是什么呢?望断红尘望断红尘望断红尘望断红尘望断红尘望断红尘望断红尘……猛地,秋晓愣怔住了。她好像被突然唤醒,望——断——红——尘,不就是望尘吗?望尘。望尘!望尘的名字也写在这把小小的红纸伞上,夹在“四季风雨四季秋”和“谁染霜天晓”之间,夹在秋晓的名字中间。
秋晓的心在一瞬间被震撼了。她深深地动容,并且隐隐地感知到,在那九世轮回的前生故事和断句谶言的今生今世中,她就这样和那个名叫望尘的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秋晓觉得自己的心就像沁透了清明的细雨,无数的幻像和奇特的心念,都在风雨潜入的刹那,勃勃而发。一种对外面天空的向往,一种对墓园外那个陌生世界的好奇与憧憬,一种强烈地想要走出去的冲动她那颗伴随着墓园里的亡灵一起沉睡了十四年的少女之心,蓦然惊厥,苏醒,积聚了太多太久的愿望,也在这神采飞扬的刹那张开了翅膀,飞出胸腔。而那枚校徽就一直攥在手心里了。钟望尘的名字也一直攥在手心里了。连同那句“你一定要学会说话,一定啊,一定!”的叮咛。墓园的故事,一片芳菲。
第七章绿唇儿
其实/荡涤在心头的/也许只是那样一些/只因突然撞入/而撕裂的风景/那样一个/任凭阳光的灼射/而悸动的瞬间/那样一种
走出了瞳孔里的映像/却再也走不回来的/流逝/那样一句/和生命一样挚情/和岁月一样千古/的呢语/最真的/最美的/最好的/最初的和最后的/一片/天空
第一节红云
关于红云的断想来自于钟望尘的一个梦。那一天正是他的十六岁生日。他的母亲把那串祖传的红璎珞挂在他的胸前。
母亲告诉他:“你可别小瞧了这些璎珞,它足由好多块有生命的玛瑙石组成的,每一块红红的石头都代表着祖上的一个女人,每一个女人都用血泪浸染过它。它是有灵性的,知冷知热的。”钟望尘感到一抹冰冷的湿润直贴着前胸往心里去,用红丝线串着的那些宝贝石头,就沉沉地悬在心窝,坠向心底,止他想起陈年往事里的那些阴魂不散的传说。这串红璎珞,母亲是当做十六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他的,据说是传家之宝,也是消灾辟邪的法器,可它却同时勾起钟望尘心里阴森森的恐怖回想。那样一种紧贴身体的冰凉,那样冷冽入心的惊怵,让他觉得自己像是触到了死人的脸。真想把它扔了,可母亲的一片拳拳之心又让他不忍丢弃,母亲眼中的慈爱,母亲的忧殷期待,像一双充满温情的手,轻轻地婆娑着他内心的惊惧和躁动。那串璎珞后来被钟望尘挂在长笛上。长笛是他的随身之物,是他生命的图腾。他就这样带着长笛和迎风飘拂的红璎珞,开始了他十六岁的生日之游。这一天他游了老虎滩又逛了燕窝岭,沿着滨海路的崎岖小道一直走到傅家庄的海滨浴场,最后又斜穿过金沙滩后的山路,攀上那座白塔山。
钟望尘就是在白塔山的山顶发现了山下有一片墓园。
那一瞬间,风云变色,山雨突来,天地间一片滂沱,然后就有一片红云漂浮在眼前挥不去。再后来,就有一道彩虹挂在那片墓园的上空。钟望尘足受了那片红云的指引才找到去墓园的路。
乍晴还雨,从树缝隙筛下千丝万缕的阳光,也筛下千丝万缕的潮湿,雾蒸霞蔚,雨意朦胧。钟望尘沿着蜿蜒的墓园小路,走过那个小女孩的凝目注视,靠在桥栏上横笛而吹的时候,那道彩虹还没有褪去,有一缕阳光正投射在长笛上的红璎珞上,淡淡地晕染过去,铺展在眼前,又向远处辐射,形成一片夺目的云!钟望尘这才明白,自打登上白塔山,就一直漂浮在眼前的那片红云,其实就是红璎珞的光影,是那些冰冷的玛瑙石在阳光下的幻像。
光影交叠之中思绪渐远,笛音却在一瞬间轻漾。
所有的幻觉都应运而生。
思想在张扬,涨满了朦胧的渴望;
乱云飞渡之中,总有无数晕染不尽的意象飘然跃起,在刺目的红云中氤氲升腾隐在黑夜里的哭声,潇潇的风声雨声,枯枝般的手颤巍巍地伸出,在真空中不知要试探着捕捉什么,却终于什么也捕捉不到:灿烂而殉情的花树,摇曳了满地缤纷的花瓣,追往前世的梨花似雪、杏花如浪,倾城的槐香所有的幻觉都是红云的幻觉,仿佛被谁有意无意罩上了一层透明的红玻璃,在里边的看得见外面,在外面的却看不见里面。钟望尘觉得自己也像是被罩在里面了,躁热和窒息步步围困,毛发被汗水浸透,一如小鸟被打湿了翅膀;他只有执着地吹笛,任笛音飘散到红云外,让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呼吸,让每一次呼吸都酣畅淋漓。
这片红云到底昭示着什么?
是红璎珞故事的回光返照?还是墓园中亡灵愁绪的再现?
为什么,它总是折射出最脆弱最感伤的情境,把心碎成一团愁烟?把笛音也揉进心泣?
而心灵的震颤分明是为了墓园而轻吟低唱,是站在山顶对着那片红云就已发出的喟叹—似是盟约而来,秉声寻觅;依稀熟稔,却又模糊了的容颜。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心灵的导引,让千年万年的惶惑追逐着红云在梦里梦外停不住地飞好像飞到天的尽头了。猛抬头,却依然是满眼的红云。
而墓园也是有感应的,用心认得的,就像从小就玩熟了的老地方,聒噪而飞的鸽群是梦里展开的一双双翅膀;守墓的老头让人猜不出年纪,又丑又凶的模样却有着金子般的好心;那个躲在古槐树后面的女孩子,她分明就是邻居家的小妹婊呐,她有。把红纸伞,映着他的红璎珞,映着墓园里红彤彤的云。
而所有的关予红云的断想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当晚回去,钟望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重又回到那红色的玻璃罩中,梦见一只鹦鹉在外面猛烈撞击着红玻璃罩想要进来。隔着一层厚厚重重的红云,他看不清它的颜色,但它眼神中有那么楚楚可怜的郁悒,那扑扇着翅膀急切地想要闯入的焦虑,那忧心似焚的苦难神色,像极了他心里的一个人;而它一定是看见了他的,一定也读懂了他噎在喉咙里的那一句话,他们互相认识,互为老朋友,互为灵魂的知交。
这个梦,日夜痴缠,困扰了钟望尘整整四年。
四年中,他全部生命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找回这个梦,找回梦中依稀相隔、脉脉相望却总也捕捉不住的精神寻恋。他在无数次的寻觅中陷入恍惚,在无数次的恍惚里走进墓园,看春夏秋冬的芳菲与落索,看守墓人遗世独立的清凄与落寞,看冥界中的亡灵们凝在草尖上的烟色幽魂,是怎样在每一个日落黄昏的时候,随着夜幕的步步紧逼,步步寂寞步步孤独着开始跳舞。他被那个水粉画一样的女孩子迷住了,被自己朦胧而脆弱的感伤困住了,走不出脚底下的小桥流水,走不出如泣如诉的笛音,走不出那把藏在古槐树后面的红纸伞。
只有执著而忧郁地吹着他的长笛。
每一声笛音都是为她。
他希望有一股清泉从他的笛声中流淌开去,一直流到她的心底:
他希望这清泉在她心底卷起如雪的浪花,绕过鲜花盛开的绿洲,收获灿烂纯情的花季;
他希望她从此有歌声有欢颜有笑语,那些歌声那些欢颤那些笑语会穿透她生命里所有的沉滞,所有的忧伤。
他不知道这四年中,女孩子也在默默地关注着他。
他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融化在了那个女孩子的水彩画里,
他不知道原来爱也是有感应的,他在她的画板上横笛,她也化做他的笛音。
终于有一天,钟望尘明白了这一切。
终于有一天,钟望尘看见了那只美丽至极的鹦鹉从红玻璃后飞了出来,静静地停落在他的面前。(未完待续)
下期提要:
风雨夜里送来的女孩秋晓被身世神秘面相丑陋的哑叔收留后,在哑叔的悉心照料下悄然长大。她在墓园里遇到了前生今世要等的人钟望尘,两人史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请继续关注下期《红纸伞》连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