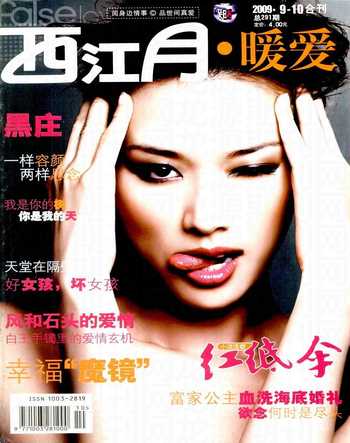我是你的树,你是我的天
讷 言
1
她是那种精明又干练的女人,每天抱着小算盘算账,算天算地,小日子算得风流水转。可是我们家的日子总比别人家过得差一些,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孩子,我们家却是四个,所以她作为母亲的角色至关重要。
她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我是你们魏家的一棵大树,离开我,你们全完蛋。我很崇拜她,带领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整天围着她转,她说:向西,我们就向西。她说:向东,我们就又转向东,像她的尾巴一样,如影相随。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我开始讨厌她,讨厌她粗着嗓门说话,引得满街人都侧目,更讨厌她为一分钱与小商贩一直争到面红耳赤,回到家后还喋喋不休地自语:险些吃了大亏。
原来她很吝啬,没多少文化,性情还特别暴躁,没有一点温柔贤淑的味道,完全不像女人。这是我十三岁时对她的印象。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遗憾,觉得有她做母亲,是一件很遗憾而又不光彩的事情。
2
她在一家兵工厂上班,干繁重的体力活,收入不错。她见我一脸不悦的表情便大嚷:我拼命挣钱,还不是为了你们四个催命鬼,不识好歹的东西!她的巴掌随着责骂,风声凛冽地扑过来,我像兔子一样从屋里跳出来,奔向花树缤纷的小河岸。
可是,两个妹妹手拉手地牵着小弟弟追上了我。大妹妹吸着鼻涕说:妈妈让我们跟着你,中午别忘了给弟弟煮鸡蛋。说完,从脖子上取下那枚用红毛线系着的家门钥匙,郑重其事地交给我。我把钥匙扔在地上,恶狠狠地用脚踩,尘土在四周飞扬起来,载着我的美梦悄然而落。
我明目张胆得带着弟妹们疯玩了一天,并且偷她的零钱买烧饼吃。晚上,她的责骂声像山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我振振有词地反驳:谁让你不生儿子不罢休,多生了我们姐妹仨,重男轻女的老封建,活该我们大家一起受累。话一出口,自己首先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她也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巴掌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屁股上,一边打还一边骂:翅膀硬了啊,敢顶嘴,打死你这个赔钱货。
我从家里逃出去,义无反顾地跑进黑漆漆的夜色里。这个家一点也不温暖,一日三餐,她总要分着吃,弟弟吃好的,我们姐妹三个吃差的,中秋夜里分月饼,弟弟自己吃一个,我们姐妹三个分吃一个,我们姐妹不过是托弟弟的福来世上的,我发誓再也不回去了。
当愤怒的气焰渐渐被夜色吞没,月光里摇曳的斑驳树影像鬼影一样晃来晃去,我多么希望她的声音能从背后突然响起来,唤我的乳名,叫我回家。等啊等。终究是越来越深的失望。一个人坐在空旷的田野里,我记住了有一种感觉叫孤独。
沿着逃跑的路线潜回家,她正坐在灯下做针线,抬起眼皮瞄了我一眼,目光里没有一丝担心和牵挂,我掀起被子躺在妹妹身旁,泪水流了一串又一串,从此,与她有了无法沟通的隔膜。
3
对她的厌恶,像我青春期的情怀,不知不觉便丝丝缕缕地涨满了心头。
邻家阿姨在我背后指指点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几乎想毁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有了几乎与她一模一样的容颜。我想摆脱她,却又不得不向她伸手索取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她总是洋洋得意地从裤带上解下铜钥匙。神秘兮兮地打开梳妆台里的小木箱,一张一张往外捻着钞票,节奏缓慢,动作凝重,像是在故意考验我的自尊心。
我急不可待地一把抓过钞票说:以后双倍还你。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跑开,留下她在一片秋风里恨恨地骂:喂不熟的白眼狼。
等我长得再大一点,发现她常在背后偷看我,猝不及防地回头,她惊慌失措地躲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向别处,一瞬间,我竟也不知所措。
虽然遗传了她的容貌,我却出落成了与她迥然不同的女子。我的含蓄低调与她的张扬虚荣,造成了巨大反差,让我们像隔着玻璃的两个人,通透却又不着边际,我再也不是那个跟在她身后的小尾巴了。
我忙着升学,结婚,生子,一路欢歌,离她越来越远。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她很守妇道地不再管我的闲事。我像一只脱了线的风筝,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4
有一天,她突兀地来了电话,我赶去时,父亲突发脑溢血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从未见她那么伤心过,哭了两天两夜,一直哭到休克过去。第三天,她睁开眼睛,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走到灵堂,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泪光在眼睛里一闪一闪的,她说:葬礼的场面要风光,但不能多花一分钱。我的心被她翕动的嘴唇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她一转身坐进太师椅里,不眨眼地注视着亲友渐渐散去,然后甩出硬梆梆的一句话:给我报报人情帐。我感觉她变成了比石头还要坚硬的女人。
她变得更加吝啬,越来越不近人情,弟妹的婚事办得潦潦草草,并且迫不及待地把新婚的弟弟赶出去住。磁到不顺心的事就给所有的孩子打电话,喋喋不休地诉说陈年旧事。我讨厌她的电话,三言两语应付几句就匆匆挂断,转过身去忙自己的事,月底的报表等着交,孩子的防疫针要去打,我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哪有时间听她千篇一律的回忆录。
她还是在一个深夜来了电话,惺忪着双眼看见是她的号码,抓起话筒,刚要发火,却听到她抽抽搭搭地哭。
我以消防队员的速度赶到她住的家属院,勇敢地攀过铁栅栏大门,冲进房去。她抱着梳妆台里的那个小木箱蹲在墙角瑟瑟发抖,见我进来,嘴唇撇了撇,孩子一样委屈地哭起来,眼泪哗哗的像小河一样流淌,哭着哭着却又捂着嘴吃吃地笑起来,笑得浑身颤抖。
她精神失常了,医生说是最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神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没有治愈的可能。
从那天起,她像个孩子一样需要人监护了。
5
小木箱里装着她半辈子的积蓄,打开来,有一叠厚厚的遗嘱,是她歪歪扭扭的字,她把自己的财产分成了均等的四份,分给我们姐弟四人。遗嘱的最后,她特意声明,如果真有一天逃不出家族病的遗传,她选择我作监护人。
我站在父亲的遗像前,泪如雨下,父亲走了,她的天塌了,于是急不可待地打发弟妹结婚成家。她早就料到自己会疯掉,所以一切便趁早了,她有家族病史,这个秘密她没告诉任何人。
我告诉弟妹:我要接她回去同住,给她养老。她住进我家里,顽皮又固执,与我的儿子争零食吃,无花果埋在枕头底下,山楂片藏在衣橱里,晚上一个人坐在床上咯吱咯吱地吃,见我进来,慌里慌张地背过手去,看我的眼神就像我三岁的儿子。我拍拍她的肩说:我是你的树,离开我,你就会完蛋。她懵懂地点头,我转过头去,泪水在眼里打着转,以前那个泼辣的俊媳妇怎么转眼间就老了呢,多么怀念,她举着巴掌追赶我长大的那些岁月,没有她率真直白的严厉管教,我怎么会有今天这样与众不同的精彩人生?她一直爱我,只不过是以咄咄逼人的方式。
我拉着她的手上街,带她去最热闹的菜市场闲逛,让她选爱吃的东西买回家去烹饪。她像尾巴一样跟着我。有孩子般的信赖和崇拜,我用哄儿子一样的口气叫她吃饭睡觉,原来,我爱她也可以有母爱滋味。
在这个世上,除了亲情,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时间在作祟,短短的三十年,我和她就调换了位置,我长成了树,她变成了藤。好在我们一直都缠绕着,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深深地爱着。
编辑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