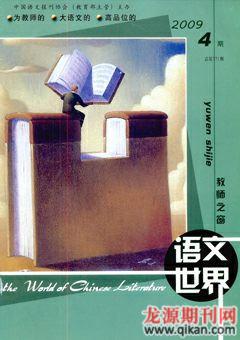画家李桦
何宝民
拜访李桦先生是在1983年的秋天。那时候,出一趟差,日程总是安排得很满。请叶圣陶为《中学生阅读》杂志题签、聘请顾问、约稿……就是一次北京之行的任务。“我的读书生活”栏目准备发点画家的文章,老画家旧学新知根基扎实,吴冠中、黄永玉、李桦等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上世纪70年代末,李桦先生曾连续发表随笔《西屋闲话》,他就成了我组稿画家的首选人物。
李桦住在北京东城银闸胡同。那天下午,为找这条胡同已经费了点周折,找到了再顺着胡同往北走,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过滤”,又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某号。这是一座三合院,院落不大,栽有两棵丁香树,还搭了一座葡萄架。西屋平排三间,是李先生的书房和住室。他的《写在〈西屋闲话〉之前》中这样描述:“总面积只有二十四平方米。我把一间作为寝室,其余两间当作书斋。这个只有十六平方米的书斋是很小的,五六个客人就把它挤得水泄不通了,但这正是一个促膝谈心的好去处。西屋书斋的陈设十分朴素:横靠着东面玻璃窗下,摆着一张大桌子,这是我读书、写字、画画的地方。桌旁有一套沙发,中间摆下一张矮茶几,用来招待客人们。靠在墙壁,尽是书橱,另有一架钢琴,这样就几乎把空间占满了。……这个纵然是陋室,却也如刘禹锡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李桦先生,一位朴实之至、精神健旺的矮个子老头,广东人的面相,一双深蕴着智慧的锐利的眼睛。他让我不要拘束,随便一点,说,朋友们学生们来,都是这样的。于是,一杯浓茗,一支香烟,我们就放声闲谈起来。
先生1907年生于广东。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李桦是集合在鲁迅先生身边的木刻青年群体的一员。他们参加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用线条和画面喷涌生命的激流。读他的画作,我印象最深的是《怒吼吧,中国》,1931年的作品。一位被蒙着眼睛、捆绑着的男子,象征处于危难的中国。他要挣脱绳索,要拿起武器去战斗,寄寓了画家燃烧的激情和痛苦的期望。木刻刀法尖锐奔放,人物骨骼肌肉的紧张和富有爆发力使人仿佛可触可感。鲁迅1934年12月18日致李桦的信中称赞他:“先生的木刻的成绩,我以为极好。”同一天,在致金肇野的信中也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我以为最好的是李桦和罗清桢。”李桦用木刻走进美术家的殿堂。
访谈中我请李先生谈谈读书求学的生活。
“我不是出生于书香之家。我家几代没有一个真正读书人。”他说。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小学毕业以后,无力升中学。在职业学校学了一年,15岁就到无线电台当了练习生,后升为报务员。除养活自己外,还要帮助家庭。第二年,广州市创办了第一所美术学校。李桦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去报考,果然被录取了。但是,这却使李桦面临一个极大的难题:上学吧,怕丢掉电台的职业。同时,也没有学费。再者,怎样说服父母,不伤他们的心?放弃上学机会吧,他万万不甘心。左思右想,最后下定决心与命运拼搏,勤工俭学!
当时电台的工作是24小时四班倒的,李桦自愿担当别人都不愿上的夜班,以便腾出白天时间去美术学校上课。这样,人们休息的时候,正是他要工作的时候,每天只有五六小时睡眠,更不要说休息与娱乐的时间了。这对于一般青少年说来,无疑是件极痛苦的事,然而,少年李桦却十分愉快。这样坚持4年,直到毕业。
60年前的往事,李先生至今仍然记忆清晰,足见刻痕之深。
他说:“我在美术学校时,除学习画画之外,比别人更爱读书。这是因为亲身体会到读书机会的难得,所以能提高读书的自觉性,逐渐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李先生聊的这些,大都写在他后来寄给我的短文里。文章的题目很不一般:《我为读书而奋斗》,刊登在1984年《中学生阅读》第三期。
李桦还是中国藏书票的元老。1934年,他在广州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曾创作藏书票,并寄请鲁迅先生指教。谈话中,先生拿出自用的藏书票让我观赏。他的作品构图简洁,刀法粗犷,有的吸收汉画像石或瓦当的纹样,富有装饰趣味和民族风格。1984年年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票研究会成立,李桦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谈话不知不觉的已近3个小时。告别时李先生问我是怎么来的之后,一定要送我一段。步出小院大门,不是向南走我来时的路,而是径直向北走去。诧异之间,紧随着他拐了两个弯,走了不到百米的距离,豁然开朗,已出了胡同。我大呼:这不是沙滩吗?隔着街看到了斜对面老北大的红楼。原来银闸胡同的北口就迎着五四大街,这里与我住的招待所近在咫尺。我来时走的是一条绕个圈子的冤枉路。
李先生莞尔而笑,眼神里闪出一丝童稚的顽皮。我想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明白了吧,这叫“别出蹊径”。
李桦(1907~1994),祖籍广东番禺,生于广州。1926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后留校任教。1930年夏曾赴日本川端美术学校深造。1931年回国,从事新兴木刻运动。曾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胜利后主持全国木刻协会工作,当选理事长。1950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版画系主任,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有《李桦木刻选集》《木刻的理论与实践》《西屋闲话》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