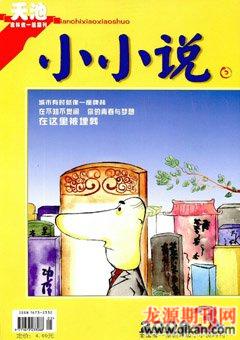芝麻枪
张玉洪
战斗!激烈的战斗!是在午后大人们下了田时打响的。三蛋、臣子、小五、发子、生、还有我,在激烈地战斗着。那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街巷游击战,我们双方充分利用草垛、墙角、歪脖子树、碾台、磨道当战壕和掩体,战场上掺杂着一些鸡们、狗们、猫们、鸭们,它们时而紧张,时而厌厌地观战着。我们的枪,是田三叔家的芝麻杆。
那年月很少有人家种芝麻。可田三叔家就种了,而且一种就是三分地。碰上了好年景,芝麻丰收了,芝麻杆一人多高,包裹着芝麻粒儿的荚子拇指肚大小,三分地割了足足有五担。田三叔将芝麻一溜儿竖排在屋墙下晒,烈日下晒上三两天,那些半青半黄的荚子就裂开了嘴儿,露出虱子般大的黑粒儿。地上铺了包袱皮,将芝麻杆头朝下倒提着,用木棍轻轻敲打,黑粒儿就会“哗哗”地淌下来。三分多地的芝麻,能收几十斤芝麻粒儿。几十斤芝麻粒儿!在那个年月,拿到集市上能换几百斤黄豆哩。
田三叔很不幸!田三叔万万想不到好端端的几十斤芝麻一眨眼就没了。
战斗打响前,田三叔家屋墙下那一排排狗腿粗细、笔直挺拔的芝麻杆,分明就是为我们预备好的枪嘛!我们如果不拿起这绝好的武器上战场,那就对不住它们。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
芝麻们很不幸!芝麻们一万辈子也想不到竟然有一天被人家当了枪使。它们的两辫荚子被阳光刺进去,“噼啪”爆裂开来的声音,有点放荡般地夸张。
我们不管这些!
我们要战斗!
我们需要枪!
芝麻,在它们的主人田三叔还没来得及将它们袒露出来的粒儿收进仓里、袋里的时候,这些无辜的、黑黑的、小小的东西,就被我们挥舞着、上下翻飞着撒进了草垛里、墙缝里、尘土里……
其实,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些小黑东西就是我们的子弹,更没想到这些小黑东西还好吃,而且是那么好吃。我们拿着芝麻杆,挥舞着,喊叫着,蹦跳着,将这些子弹“嗖嗖”地射向敌方。它们倒也卖力,纷纷扬扬射进对方的头发里、眼睛里、鼻孔里、嘴唇里……在战斗进入最艰苦的白热化阶段,敌我双方展开了拼刺刀、肉搏战。我的战友小五壮烈牺牲了。小五牺牲的原因是:正当小五张大嘴巴喊“冲啊!冲啊!”的时候,敌人将一串子弹射进了他的嘴里。
小五倒下后,嘴巴“呱唧呱唧”地嚼着什么东西。敌方一看小五倒下了还不愿意死,就不干了,强烈抗议着,并挂起免战牌威胁我们。
四仰八叉躺在地上的小五抬起头来赶忙解释说:“不是我不愿意死,谁叫你们把子弹往我嘴里射来着,嘻嘻!没想到这子弹这么好吃,越嚼越香,香死我了!”
敌人三蛋听了,疑疑惑惑地将手中的芝麻杆倒过来,小手掌摊开接住一堆黑东西放进嘴里,“呱唧呱唧”地嚼起来,嘴里咕噜道:“哎呀!真香啊!”
战斗,在发现了子弹好吃以后结束了。还没过够战斗瘾的发子见我们一个个倒提着芝麻枪往外倒子弹吃,气愤地骂我们是伪军、汉奸。我们根本不在乎发子骂什么了,我们在大嚼特嚼那些子弹。
傍晚降临的时候,田三叔家屋墙下的芝麻,所剩无几了。
尖利的嚎哭是在快吃晚饭的时候,响彻村子的上空的。姐姐问娘是谁在哭啊?从地里劳作刚回来的娘说:“是你田三婶。三分地的芝麻全被人糟蹋了!芝麻可是稀罕物哩。唉,太可惜了!”
娘这话让我一口粥没咽好,呛得眼泪鼻涕全出来了。娘问我咋着了?我慌慌地掩饰道:“粥太热,烫着喉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