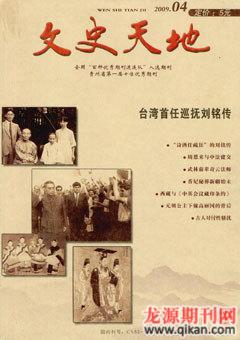宋太祖之败笔
张 贺
学过历史的人对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再熟悉不过,但对于他释兵权之后的相应政策及酿成的后果就鲜为人知了。
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儿子柴宗训只有七岁,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既掌握着禁军又统帅着出征军,兵至陈桥驿被诸将“黄袍加身”、“拜呼万岁”,成为大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担心别人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或其子孙“禅位”,就和丞相赵普商量“欲息天下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赵普向他建议对执掌军权的将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此计一出,正中赵之下怀。
961年,赵匡胤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顺利解除禁军诸将兵权,为进一步实施“杯酒释兵权”的杰作开了个好头。接着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侍宴饮,用同样的办法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这一做法较其他朝代开国帝王削减兵权的做法确实更为文明,也确实消除了他不十分光彩“登基”的危机感。但是他下一步的动作及所造成的后果与其“久长之计”的目的又是相左的。
赵匡胤任命石守信为节度使,却不让他赴任,而是待在京城,过着只拿俸禄不管实事的悠闲生活。宋朝采取这样的官僚制度,便形成了一个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和种类繁多的官禄。“杯酒释兵权”使武官形同虚设,名义上是节度防御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只是依照品级领俸禄。实际管理军政事务的官员由朝廷临时差遣,并无指挥军队打仗的权力,因为是差遣,像是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对武将如此,对文职官员也分为勋职和管事的实职,实际管事办事的被称为职式差遣的人,也都是流动性很强的。
赵匡胤接着又在兵制上进行了改革,分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乡兵、藩兵不常有,也不训练,都是有名无实的军种,禁兵是皇帝的卫士,一部分驻守京城,另一部分镇守边防要地,但要经常移防换地,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兵无常将,将无固兵”从而达到防止他们联合叛变朝廷的目的;厢兵是各州的守军,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是从农民中抽出来的壮丁,名义上是地方守军,却没有一点战斗力;藩兵是招募来守卫边防的,但大多是空名额。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北宋诸帝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北宋时期的武备变为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遣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兵不强国何以强,以至于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并给中国历史上平添了一个最为软弱、战争最为频繁的朝代,到北宋末年还上演了钦、徽二宗为金兵所掳的靖康之耻。这也许是宋太祖赵匡胤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