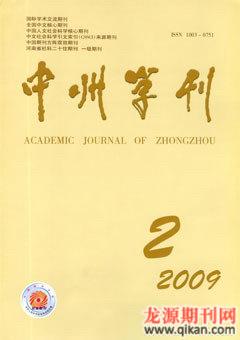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
李有光
摘要:从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去观照当代“于丹现象”引发的有关传统经典的阐释论争,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不过是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博弈的延续与回应。中国经典的理解史和效果史告诉我们,对待文化经典必须尊重以原意观为中心的“我注六经”式的历史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而对待文学经典又必须沿用以多元论为中心的“六经注我”式的相对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不仅如此,崇圣尊经的文化传统及其具备的形上之维和终极价值已经注定了任何偏离经典本旨的任意解读最终只会因为冲淡了经典的权威性而导致对经典的解构与颠覆。
关键词:传统经典;原意观;多元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226-05
如同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性一样,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也同样构成了人类所有文化经典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由央视打造的“于丹现象”及其引发的如潮争议,我们就不难明白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解释方式其实在中国经典阐释史上并不鲜见。的确,在传统属于我们之前我们早已属于传统,今天各种有关经典的阐释之争都不过是传统的延续和回应,它们组成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化经典的解释史。实际上,从最早的汉代今古文学派之争到当代的“于丹解读”与“解‘毒于丹”,本质上都不过是解释学的原意观和多元论之间的长期博弈,其论战的烽烟当然缘起于那种为我所用的主观阐释和“保卫作者”的客观阐释间的针锋相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古文学派之争就是汉代两种阐释学之争。概要说来,今文经学倾向于政治性,讲阴阳灾变,讲微言大义,往往就原典借题发挥,建立了一种‘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古文经学则倾向于历史主义,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力图申说经典的原始意义,建立了一种‘我注六经的诠释模式。”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很容易发现,20世纪西方现代阐释学仍然是在沿着这样两条清晰的阐释模式和线索发展。“一是以赫施(E·D·Hirseh)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家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只能是作者的意义,并且‘总是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以此为前提,赫施进一步提出阐释‘应该强调对作者意图和态度进行重构。……现代阐释学发展的第二条线索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主要代表。在这里,解释被认为一定是读者和作品各自视野交流融合的产物,意义不是先于阅读、读者理解的自在之物,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的生成物。”应该说,中西方这两种大同小异的解释思想和方法正如同火车的双轨,承载着人类一切文化经典向着本原性和丰富性的方向不断前进。
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解释学史上,有关经典的理解与阐释的方法论争常常是由多元论的一方在实用目的驱使下首先发难的。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代表董仲舒完全将先秦经典纳入到自己的政治批判目的和阴阳灾异的阐释框架中,作为历史文本的《春秋》、政治文本的《尚书》、伦理文本的《礼记》、哲学文本的《易经》甚至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经》都被解释为各种阴阳变数和灾异现象的记录与预兆。一方面“君权神授”论赋予了专制制度先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天人感应”论又企图以上天的绝对力量来遏制君王的绝对权力。事实上,今文经学派不仅使用讖书和纬书这些神秘化的阐释文本来实现自己的现实需要,就连对文学文本《诗经》的理解也几乎都是运用单调的“美刺”阐释模式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正是不满于今文经学这种随意的穿凿比附,古文经学派才义正严词地提出“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开始了“念述先圣之元意”的捍卫经典本来面目的斗争。针对今文学者制造的所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以大量谶纬之说衍生的洋洋洒洒的无稽之谈,古文学者鲜明地倡导“全经”即完整准确地理解与阐释经典的观念,祈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的语言训诂的解释。无论如何,与今文经学家相比较,古文学者“更注重探求元意,更注重语言解释,更有求真精神,更有严谨态度,因而其方法也更可靠”。同样,针对宋明理学那种脱离文本依据的借题发挥的阐释和微言大义的理解,清代朴学又高扬正本清源、考信实证的解释精神,坚决维护经典文本的原始本义,坚持所谓“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
看来,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种理解方式、两种解释思想之间的博弈与较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喜的是,在传统文化的精髓断裂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新千年里,借助“第一媒体”电视无孔不入的魔力,由“于丹现象”引发的新一轮历史主义解释和相对主义解释的争论烽烟再起。无论这场回应历史的论争结果如何,从文化传承的宏观视域观照,它都值得我们隆重关注并以欣喜之情对此推波助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于丹的实用主义解读态度仍然是挑起争端的导火索。众所周知,于丹将《论语》改造成了一份指导人生、有益于励志的“心灵鸡汤”,用以抚慰那些在激烈的竞争时代失败、失落和失衡的普通人,从而开启了传统经典的当代通俗化和普及化的道路;而易中天品读三国则干脆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来阐释经典的内涵,在赢得阵阵笑声和掌声之余走上了一条娱乐化和时尚化的途径;刘心武的《红楼梦》解读则又是巧妙利用了受众与生俱来的探秘心理。在寻绎秦可卿原型的同时揭开了尘封的宫闱秘事,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理性地评价当代这股方兴未艾的经典解读热潮?它是“六经注我”的多元阐释观念形成的传统惯性的自然延续,还是当代大众文化解构中心与颠覆崇高所特有的阐释现象?建立在为我所用、自由发挥基础上的品读到底是因为祛除了经典的权威性和真理性而应当被否定,还是因为贯彻了经典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而应当被肯定?对文学经典的理解方式难道一定与传统文化经典的解释思想保持一致吗?正所谓“有什么样的前理解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解,有多少种前理解,也就会有多少种理解”,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提醒我们,只能到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作一番梳理和考证,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观照今天的解释现象并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经学解释学的根本理解模式与阐释思想
什么是解释学?伽达默尔说:“根据最先的定义,解释学是一种澄清的艺术,它通过我们的解释努力转达我们在传统中遇到的人们所说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所说的内容不直接为人理解之处,解释学都在发挥作用。”看来,解释学的原初定义已经指出了它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即解释文本中那些不易为人理解的内容。洪汉鼎先生明确提出解释学的两个主要任务:“(1)确立语词、语句和文本的精确意义内容。(2)找出这些符号形式里所包含的教导性的真理和指示,并把这种真理和指示应用于当前具体情况。”显然,第二个任务的完成有赖于第一个任务的解决,以第一个任务为解释取向的探究型解释学是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的独断型解释学
的前提和基础。同样,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这种探究型解释学的任务和目的,即完整准确地重构和恢复经典的本义及作者的原初意图也被视作经学解释学的根本和重心,尤其在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意识里更是如此。清代《四库全书》在概括中华文化的全部经学成果时有一段重要的总结: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在清代那些有资格、有能力总论全部儒学的大家眼里,汉学代表了注重语言训诂和经典本义的学风,宋学则是强调以意逆志和微言阐发的标志。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地总括了二者的优劣之处,画龙点睛,提纲挈领,因而被认为“是总论中国儒家经典阐释方式的权威论断”。但是,清代朴学却用自己鲜明的学术态度表达了对这两种阐释取向的褒贬和选择,“具有根柢”的汉学由于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而使考据训诂之风迅速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身跨明清两代的钱谦益痛感空疏随意的阐释方式对晚明学风的损害,故而坚决主张清学回归汉儒治经的传统,他说:
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餍而饫之,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抉择异同,疏通凝滞。
应该说,“原始要终”之学在清代已经发展到极致,乾嘉考据大师戴震说:“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经典本义即“道”的曲解和流失,戴震提出了著名的阐释方式和理解目标论——“由词通道”与“十分之见”: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
对清学这种崇尚语言解释和追求十分之见的目的,今人钱钟书总结得很清楚: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
现在看来,清代经学解释学对汉代古文经学的回归和弘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作为对全部中华经典文化的继往与开来,清学的阐释态度和方法显然代表了中国经学解释学主流的根本的取向和重心。梁启超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的确,以解释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以及学术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自居的清代学者谈到宋明理学“师心自用”的解释时总是充满了不屑。其实,清人的骄傲心态根深蒂固。一方面,他们深知儒家话语权威性和真理性的确立和振兴有赖于经典本来面目的廓清与重构。而经典之所以不能遭到曲解和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承载并传达了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在中国学人眼里,经典就是圣贤之道的外化,具有与本体之道同等的高度和地位,所谓“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地之理”。圣人思想和经典似乎先天地被结合在一起,永不分离,正如东汉思想家王符所言:“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既然如此,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就等于获得了往圣先贤的思想,这就是汉代著名的“读应尔雅”的解释精神:“《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中解释“读应尔雅”说:“‘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读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毋庸置疑,经学解释的“读应尔雅”话语就像文学解释的“诗无达诂”一样,都是历代普遍遵循的基本阐释原则。
另一方面,清人孜孜于通诂考信的动力还在于对传承千年的尊圣崇经传统的坚守。所谓:“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如上所述,圣贤思想和经典的合而为一为后人提供了一条领会最高真理的途径:“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由文化经典达至圣贤思想再达至自然之理和天地之道,这条文明的传承线路经过千年的自觉维系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传统经典和圣贤思想不证自明的权威性和真理性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作用。
西方历史主义解释学家赫施说:“我们应该尊重原意,将它视为最好的意义,即最合理的解释标准。”从经典在中国文化中的至上地位和巨大功用出发,我们更应当尊重经典的原意,也更应当将其视为最好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坚守经典的本真面目就是最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不仅如此,中国历代理解与阐释的效果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经学解释学的根本理解方式和阐释思想只能是且必须是以原意观为中心的语言解释方法和历史主义态度。尽管其间也不断出现了“六经注我”对“我注六经”、自由理解对客观解释、为我所用对考据实证的挑战,但经过一番较量和一段沉寂之后,往往还是立场坚定的后者胜出,多元让位于本义,甚至在很多具备理解能力和解释权力的大儒那里,对经典原意的孜孜以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许,这就是中国经学解释学的本真面目和巨大特色。
二、文学解释学的根本理解模式与阐释思想
与经学解释学以重构原意为旨归的科学性理解和历史主义阐释不同,文学作品自身独特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文学解释学只能是以多元论为取向的诗性理解和相对主义阐释。事实上,类似“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耳熟能详的话语已经使文学解释即个性化的自由阐释变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道理。尽管从哲学的本体层面上我们常说:“所有的理解与解释行为都是公开或隐蔽地在理解历史、文化、传统或现实中去谋求理解和解释人自身,理解因而同时是人的自我理解。”但是只有在对文学艺术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一种向着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的回归,因为艺术作品的独特本质就是传达个人性的自我生命体验。同样,受众对艺术文本的阐释也必须放弃以认知为宗旨的追求,而选择以自我生命回应作者生命的阐释。“只有文学艺术的解释是生命的直接表达和个人性的传达,它不是为了寻求科学的真理,而是为了寻求生命的本原感觉。”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读者,其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是有限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的,这就决定了“每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个人理解永远与作者存有差异,不同读者对作品的个人理解也因体验的个人性而永远保持差异”。因此。所有的自我理解都必然是永不相同且永无止境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自我理解总是在路途中,它走在一条显然不可穷尽的小径上。”
文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创作和接受的固有特征都已经本然地注定了任何试图恢复作品原意的努力以及将作者的意图视为唯一正确理解的想法都是荒诞不经的。张隆溪先
生说:“自柏拉图以来,诗是无意识的创作这一思想回答了文学作品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评论和解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回答了文学解释为什么不能用作者的意图作为判断之标准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诗是诗人在代神说话;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既然连作者尚且不知道自己为何创作以及创作了什么,哪里还有所谓的作者意图和作品原意?实际上,文学文本蕴含了众多的空白和隐喻,它们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在充分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填充和创生。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结构,充满了无数有待具体化的未定点,读者诗评家则各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接受重点;即使在同一个问题上也会见仁见智,发现多样的阐释角度”。这里所言的“审美取向”一般是指读者在长期鉴赏中形成的审美趣味,特里·伊格尔顿说:“我们总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所在来解释文学作品。”而读者兴趣的千差万别显然也导致了理解与阐释的万别千差。正是基于此,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著的那本影响世界的著名教材《文学理论》里作出了定论:
作家的创作意图就是文学史的主要课题这样一种观点,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史的主干是诗歌和诗论。伽达默尔说:“任何解释都带有片面性,它只是针对某个方面,而这一方面却不能自称是唯一的一方面,对诗歌的解释尤其如此。”其实,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诗歌理解与阐释的多元性,并将这种极富创造性的多元解释思想贯彻始终。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就提出了著名的“诗无达诂”论: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迭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从此以后,“诗无达诂”就逐渐为众多学者接受并演变为中国诗学解释学的根本原则。时隔千年,我们从清代学者卢文弨的话里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这种解释思想的传承:
夫诗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读诗者有因诗人之情,而触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诗人之情,而远者忽近焉,离者忽合焉。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试观公卿所赠答、经传所援引,各有取义,而不必尽符乎本旨,则三百篇犹乎三千也。
细心者可能会注意到卢文昭的话里提到“言外之旨”这个中国诗歌特别追求的美学特征。事实上,也正是对“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偏爱和对含蓄风格的青睐,才使得中国诗歌的理解与阐释呈现出气象万千、多姿多彩的丰富景象。当然,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意象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结构的未定性和填充性等中西诗歌共有的文本特性已经充分地预设了理解与阐释的多元性,伽达默尔对此已有说明:“诗歌语言的模糊性回应了整个人类生活的模糊性,它的价值就在这里。诗歌为我们解释出来和指明的东西当然不同于诗人所意指的东西,诗人所意指的东西决不优越于别的任何人所意指的东西。”但是,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言外之意的极致追求却是中国诗歌鲜明的美学个性,它使得中国诗学解释学在多元的阐释取向上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对中国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有一段精妙的论述: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这段话的内涵今人冯友兰先生总结得更直白: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表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应当“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
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篇幅,完全可以开出一长串以“诗无达诂”为总纲的中国文学多元解释的话语系统并逐一展开论述,它自然包括“见仁见智”、“赋诗言志”、“断章取义”、“诗无定解”、“诗无达志”、“诗无定价”……如此等等。但是本文的主旨只是倡明并强调文学解释尤其是中国诗学解释的根本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是以“诗无达诂”为标志的尊重个性理解和自由阐释的多元论,其本质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生命主义的自我理解和诗性阐释,这正与上述所论经学解释学以原意观为中心的“我注六经”的根本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构成了鲜明的反动和对比。惟有论证清楚了这两种针对不同对象的根本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我们才能为下面回到当代围绕传统经典的理解论争和阐释博弈提供历史的规定性和参照系。
三、对传统经典的当代理解与阐释的深度追问
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切本质上始终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传统经典本身就携带着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二者显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离。当我们对传统经典的根本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进行了上述的历史检视和学理分析之后,我们才发现,今天由“于丹现象”引发的围绕解读经典的诸多论争其实都是在孤立地看待经典的当代阐释,至于由10个博士起草的所谓“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一文,也由于其攻击性的激烈措辞缺乏学理性和历史性的探讨而失去了批判应有的理性和深度。简言之,我们应当将《论语》这样的文化经典的解读和《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的解读区别对待。中国经典解释史和效果史告诉我们,对待文化经典必须尊重以原意观为中心的“我注六经”式的历史主义的根本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而对待文学经典也必须沿用以多元论为中心的“六经注我”式的相对主义的根本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事实上,从当代学人对于丹主观随意地曲解《论语》产生的强烈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经典本义的传承和对客观理解的尊重已经演变为中国学术的集体无意识;同样,学院和民间对“百家讲坛”上的《红楼梦》解读和李杜诗歌的多种解读的普遍接受,也充分证明对文学经典的多元阐释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冯天瑜先生说:“由于元典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色,如思想及其表达方式的首创性、主题的恒久性,又由于人类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异代人们的认同意识和文化结构心态内核的稳定性,使得元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局限,被异域异代的人们所尊崇景仰。”质言之,尊经重典的千年传统使得圣贤经典以及由此形成的经学在中国文化中已经具有了信仰的价值和形而上的意义。《四库全书总目》之《经部总叙》开卷即定论曰:“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将“经”定位为天下之公理,应该是对其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的如日中天之崇高地位的客观总结。经典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它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更是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在数千年的艰难岁月里,经典始终处于历史向心力的核心,凝聚并引领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而这种信仰显然依赖于我们对经典的作者——圣贤元意的执着与守护。朱维铮先生说:“倘称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它曾经支配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颁行标准解说的‘五经或其他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这第三个条件的界定可谓深得中国经学之三味。的确。在一个缺乏原创宗教的民族文化里,经学已经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具有了宗教的价值和地位,并在精神生活中起到了宗教信仰的凝聚与提升的作用。
因此,从经典在民族文化中的本体地位和终极意义出发,我们必须对当代“于丹现象”所代表的经典的通俗化和实用化阐释趋向保持警惕。任何偏离经典本义的任意解读最终只会因为冲淡了经典的权威性而导致对经典的解构与颠覆。或者说,离开对经典原意的执着和对崇圣尊经传统的守护,经典在千年传承中所形成的终极价值和信仰功能就会迅速丧失。事实上,经典的“媚俗化”和“快餐化”已经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的流行风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狂潮的一部分,我们不无理由地怀疑这是在利用传统经典、强势媒体和大学教授三重权威来实现背后的商业目的。可以说,当代“国学”热和经典解读热本质上都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强调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建立民族文化的自信感,而大众文化的炒作性和后现代的解构性显然对民族文化信仰的重建有害无益。当然,本文倡导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应当尊重历史性,讲究学理性,还要具备辩证性和针对性,这也是本文论述中始终贯穿的宗旨。
责任编辑: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