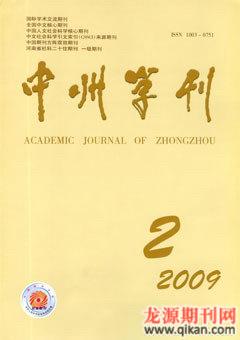晚唐诗人许浑卒年应如何考订
摘要:多种可信史料证明,晚唐诗人许浑于唐大中八年尚在郢州刺史任上,并未“去世”;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二年以后有充分的信史支持;欧阳修主编《新唐书》中关于刘皋被错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记载无可怀疑;由以上证据链证明,晚唐虽可能有两位许浑,但诗人许浑的卒年应确定在成通年间为宜。
关键词:晚唐;诗人许浑;卒年;成通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99-05
近日读到吴在庆、高玮合撰的《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以下简称《新说》)一文,对我在《许浑年谱稿》中所考订的许浑生卒年时间提出了新的辨证意见,拜读之后,我感觉《新说》在考证方法和结论上都不能无惑。
一、许浑卒年必不在“大中十年前的二三年间”
显然,《新说》对许浑卒年的确认很有信心。在全文第二节末说:(许浑)“只能卒于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全文结尾在考辨《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后再一次表达了这个意见,并将“只能”一词换成“必”字,意在强调这一结论的不可动摇。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中十年前三年是大中七年,前二年是大中八年,而这两年许浑的行迹非常清楚,谓此际许浑去世是殊难成说的。
在许浑的生平经历中曾有郢州刺史之任。《新唐书·艺文志》称许浑“大中睦州、郢州二刺史”;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称其(大中)“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十六在许浑名下注云:“大中末为郢州刺史”。王荆公之注是关于许浑刺郢时间的最具体的记载。大中一朝共13年,既称“大中末”是不可能推前到大中七年或八年的,因为果真是大中七八年的话,则应当称“大中中”而不应该称“大中末”了。这一史料在研究许浑卒年问题上应予充分注意,至少不要有意回避。
那么,许浑是何时赴郢州刺史任的呢?这里我们需要梳理一下许浑大中朝有确切记载的一些事迹。最可靠的是许浑《乌丝栏诗自序》所云:“大中三年,守监察御史,抱病不任朝谒,坚乞东归。”大中四年春,许浑在京口丁卯涧村舍自编诗集,秋任睦州刺史;大中六年四月,由睦州任内擢虞部;大中七年分司东都,与河南尹刘瑑过从甚密,屡请为之斡旋,一麾出守,积其薪俸为悬车归隐之资。
大中七年许浑在洛阳的事迹,有《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桥即事十六韵献居守相国崔公兼呈工部刘公》为证。郁贤皓在《唐刺史考‘汴州》中考订刘瑑大中七年起任河南尹,大中六年许浑由睦州擢虞部,而八年已出为刺史,故其分司东都与刘氏交游诗必作于大中七年。值得注意的是,其间许浑又有《寄献三川守刘公并序》云:“余奉陪三川守刘公宴言,尝蒙寻访行止,因话一麾之任,冀三径之谋。特蒙府鉴丹诚。寻许慰荐。属移居履道,卧病弥旬,辄抒发二章寄献。”诗其二云:“半年三度转蓬居,锦帐心阑羡隼旗。老去自惊秦塞雁,病来先忆楚江鱼。长闻季氏千金诺,更望刘公一纸书。春雪未晴春酒贵,莫教愁杀马相如。”这里“因话一麾之任,冀三径之谋”意即希望出守一郡,为致仕后的生活做准备。从“长闻季氏千金诺,更望刘公一纸书”可知,刘瑑对其甚为关照并有所允诺,现在许浑要他付诸行动,向朝廷权臣致信推荐自己。
果然就在大中七年,刘瑑帮助许浑完成了从东都分司官到郢州刺史的运作,大中八年春,许浑就赴任郢州了。在许浑的诸多郢州诗作中,《宴饯李员外》一首写作时间可以确切考订在大中八年。该诗序云:“李群之员外从事荆南尚书杨公,诏征赴阚,俄为淮南相公杜公辟命,自汉上舟行至此郡。于白雪楼宴罢解缆,阻风却回,因赠。”白雪楼在郢州,此诗无疑为许浑任郢州刺史时所作。小序中的荆南尚书杨公指杨汉公,淮南相公杜公为杜琮。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知杨汉公大中六年至八年镇荆南,杜琮大中元年至九年镇淮南。那么,李群之去荆南赴淮南必在大中八年。此为许浑大中八年在郢州任郡守的坚证。
从上述事迹可以知道,大中七年许浑尚未就郢州刺史任;说“大中十年前三年”许浑就已经去世,是和现存史料相悖的;而“大中十年前二三年”中的大中八年,正是许浑初任郢州刺史之年。方干有《许员外新阳别业》一诗,云:“柳絮风前欹枕卧,荷花香里棹舟回。园中认叶封林草,檐下攀枝落野梅。莫恣高情求逸思,须防急诏用长材。若因萤火终残卷,便把渔歌送几杯。多谢郢中贤太守,常时谈笑许追陪。”据此诗所云,许浑这位“郢中贤太守”后来还在郢州所属京山县(晋代称新阳)置了别业。此别业不可能是初仕郢州所建,其时间必在大中八年之后了。顺便提一下,《新说》在为许浑《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重新系年时,也就定在了大中八年。其原文是:“郑祗德大中八年出镇江西,其时许浑正在郢州刺史任上。”既然明明已经知道许浑大中七年绝对在世,并又肯定了他大中八年的仕履,为何又反复强调许浑去世“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呢?这在逻辑上实在自相矛盾,让人很难理解《新说》的文理所在。
二、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到底作于何年?
《新说》为什么会出现明知许浑大中八年刺郢经历的真实性,又出现反复强调其卒时“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矛盾呢?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结为《新说》的作者有意牵合对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写作时间的考订。
顾陶《唐诗类选后序》是唐诗学术史上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涉及到晚唐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去世的史实。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段记载是:
近则杜舍人牧、许鄂(按:当为郢)州浑,洎张祜、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殁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若有所得,别为卷轴,附於二十卷之外,冀无见恨。
这里明确记载了杜牧、许浑、张祜、赵嘏、顾非熊等晚唐著名诗人“身殁才二三年”。有了如此具体的“唐人录唐事”,只要能够确定该文的写作时间,那么这一批诗人的卒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恰恰顾氏的《唐诗类选序》(以下简称《前序》)署为“时大中景子之岁”,而《后序》则未署写作时间。这样,有学者就认为《后序》应与《前序》同样为“大中景子”(景子,即丙子,因避讳改,为大中十年)所作了。如果确实《后序》写于大中十年,那么从这一时间点前推二三年,许浑等人的卒年就可以确定在大中七年或八年了。这就是《新说》的作者为什么反复用许浑卒世“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这种表述方法的原因。
《唐诗类选后序》到底写于何时?这似乎是顾陶在一千多年前有意为后来的唐史研究者设置的一道学术难题。当然,如果出现了杜、许、张、赵、顾等人(甚至哪怕其中一、两位,但最好不要以孤证定论)确实卒于大中七、八年的过硬证明,那这道题实际上就解开了,《后序》与《前序》同作于大中十年之说便能成立。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坚证,而关于上述诸人卒年的讨论,几乎无不是先预立《后序》作于大中
十年说,再以大中十年为界,向前推二、三年来订他们的卒年。这显然不是一种客观求是的方法,如此循环证明,是没有办法解决《唐诗类选后序》到底写于何时这道难题的。
要证明《后序》到底写作于何时,我们应当摈弃一些先验的观念,去寻找所涉及的晚唐作家的后期事迹。事实上,就像我们如果能够切实证明杜、许、张、赵、顾等人(哪怕其中一、两位,同样要防止孤证)卒于大中十年以后,便可否定《后序》作于大中十年之说。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提起杜牧的卒年问题。我曾在较早撰写的《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一文中,对学术界一般以杜牧《自撰墓志铭》写于大中六年来作为杜牧去世于当年的坚证提出质疑,通过对《自撰墓志铭》较为深入的解析认为:“杜牧这一‘死的宣言的内核只不过是一段谶语。其背后是一个梦,一个自以为不祥的预兆。它可以帮助我们沿坡讨源,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生平情况,却不足以作为考订杜牧卒年的依据。”
那么,有没有与杜牧卒于大中六年说严重抵触的史料呢?这可以看以下事实。考《樊川集》卷十七,有《归融册赠左仆射制》。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春正月壬辰……归融卒,赠右仆射(按:‘右为“左”之误)。”《新唐书·本传》:归融,“(大中)七年卒,赠尚书左仆射”。应当注意,《旧唐书》与《新唐书》根据不同材料来源,都明确记载归融为大中七年去世。仅此而言,已使杜牧卒于大中六年之说难以成立了。又,《樊川集》卷十七有《令狐定赠礼部尚书制》。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十年十月,桂管观察使令狐定卒,赠礼部尚书。”《樊川集》卷十八有《卢博除庐州刺史制》。《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十年四月癸丑,以刑部郎中卢博为庐州刺史。”《樊川集》卷十八有《郑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陈州刺史等制》。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晋阳令郑液为通州刺史。”以上四篇制文均署为大中六年后作,最迟至大中十二年,俱有正史记载佐证,时地相符,无异说,无确切的反证。这些是考订杜牧卒年问题无法回避的系列史料,也是考证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写作时间的重要依据。
《后序》的写作时间,还有更可靠的有关唐代的出土文献提供证明。胡可先教授近年来专注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收获甚著。在《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一文中提出:“有关唐代的出土文献可以订补现存文献的阙误与促进作品研究的深入。”其中举《杨牢墓志》为例。该墓志亦见于《千唐志斋藏志》,称“大中十二年正月二日,河南县令弘农公□□□府□善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公讳牢,字松年,弘农人”。这一记载对研究《后序》写作时间极为重要,胡可先指出:
晚唐人顾陶所编的《唐诗类选》,是唐人选唐诗的一部重要典籍,但其书久佚,写作年代有所争议。因为《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录顾陶《唐诗类选序》及《后序》。《序》作于大中十年,文后有题款,自无可疑;而《后序》没有题款,故时间难定。卞孝萱以为作于大中十年,罗时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为成通二三年所作。令考《唐诗纪事》卷五三《杨牢》条:“牢,登大中二年进士第,最有诗名。大中时,顾陶作《唐诗类选》,去取甚严。其序云:删定之初,如杨牢等十数公,时犹在世;及稍稍沦谢,一篇一咏,未称所录,若续有所得,当列为卷轴,庶无遗恨。”参之杨牢墓志,牢卒于大中十二年正月,故知《唐诗类选后序》应作于大中十二年以后。
值得注意的是,《唐诗纪事》之“时犹在世;及稍稍沦谢,一篇一咏,未称所录,若续有所得,当列为卷轴,庶无遗恨”云云,确为顾陶《后序》原文的内容。可见,计有功在宋代曾读到过文字与今传本稍有不同的《唐诗类选后序》原文,其中在“已殁”诗人中列有“杨牢”之名。既然《杨公(牢)墓志》确载其卒于大中十二年,那么《后序》作于大中十二年之后当是不争的事实。
三、《闻边将刘皋无辜被戮》作于大中十二年的事实能够否定吗?
在《丁卯集》卷九有《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诗云:“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传首动金门。三千客里宁无义,五百人中必有恩。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新唐书·宦者传》对此事记载云:“宣宗时,玄价监盐州军,诬杀刺史刘皋。皋有威名者,世讼其冤。”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载:“刘皋为盐州刺史,甚有威名。监军使杨玄价诬奏皋谋反,函首以进,阖朝公卿面折廷诤。上重违百辟之言,始坐玄价专杀不辜之罪。”关于此事件的发生时间,《新唐书·宣宗纪》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大中十二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杀其刺史刘皋。”
如此重大的事件,史书有如此明确具体的记载,其可信程度当无可置疑。因此郁贤皓在《唐刺史考》中《关内道·盐州》刺史记名曰:
刘皋,大中十二年。《新书·宣宗纪》:大中十二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杀其刺史刘皋”。又见《杨复光传》,《东观奏记》卷下。《全唐诗》卷五六三收刘皋诗一首。
《新说》的作者之一吴在庆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也记载:
刘皋(?-858)籍贯不详。宣宗时仕至盐州刺史,颇负盛名。大中十二年,为盐州监军使杨玄价以谋叛罪诬杀,公卿大夫多为其诉冤。今存诗一首,见《全唐诗》卷五六三。生平事迹见《东观奏记》卷下、《新唐书》卷八《宣宗纪》、卷二〇七《杨复光传》。
显然,刘皋之死事件的“证据链”是完整而清楚的。其时间,《东观奏记》的记载次于大中十二年的事迹之后;《新唐书·宣宗纪》则清楚地载明为大中十二年三月;许浑此作的内容也完全可以证明《新唐书·宣宗纪》所谓“皋有威名者,世讼其冤”之说;而包括《新说》作者在内的学界研究者对刘皋大中十二年被杨玄价诬杀的事实,也是有充分肯定的共识的。但恰恰是《新说》作者自己在感到“刘皋死于大中十二年”之说与其“《唐诗类选后序》写于大中十年”之说明显抵牾时,就随意地修改前说,反过来认为“如果《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为许浑诗无疑,则刘皋被杀事,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诗人许浑去世之前”。
这里有两点在论证逻辑上不尽妥当,需提出特加说明。
一是没有根据就暗示《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不一定为许浑所作。要知道此诗最早在宋书棚本《丁卯集》中就载录,后来《丁卯集》各版本均载有此诗,且在《全唐诗》中也未见重出互见,作品的归属是绝无疑义的。或许《新说》作者认为许浑《乌丝栏诗真迹》未载此作,而心存怀疑,但须知《乌丝栏诗真迹》乃大中四年许浑退隐润州丁卯桥村舍时所编,刘皋被诬杀之事在大中十二年,《真迹》不录是自然的。对此诗是否伪托的怀疑,其实多少反映出《新说》的作者在否定“刘皋被诬杀于大中十二年”这一史实时信心并不充足。
二是用似是而非的方法否定《新唐书》对刘皋被诬杀事件的系年。《新说》因感到此问题对确认许浑卒年问题之重要,故花费较多笔墨,来论证这一问题。正由于此,这里我有
必要将这一问题特别说明清楚。以下是《新说》所论:
可疑的是《新唐书》对杨玄价杀刘皋的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系年。我们知道,唐武宗以后的实录等史料多亡缺,正如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引引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条下所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吏杜让能。”……欧阳修在撰《新唐书》时多据《东观奏记》“补充了许多不见于《旧唐书》的史料。”……可见,《新唐书》关于杨玄价杀刘皋的记载乃取自于《东观奏记》。《东观奏记》关于此事的记载并未记年月。应该说,《东观奏记》的记载是较为严谨可靠的,因此在其明了所记事件的具体时间时,作者在许多奈目的记载中。多有具体的年月记载;而未知道具体确年的,则未记年月。杨玄价杀刘皋的这一条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新说》以上论证的基本逻辑是:《东观奏记》关于刘皋被杨玄价诬杀一事并未记年月,“大中十二年”是《新唐书》从《东观奏记》中“推测”出来的,所以“并不可靠”。这里存在两个需要辨析的问题:第一,《东观奏记》对刘皋被杀事件有没有可靠的依据?第二,《新唐书》的记载是否肯定取材于《东观奏记》?
众所周知,《东观奏记》专记宣宗一朝之事迹,在唐朝杂史中最称翔实,共分三卷。下卷自大中九年开始直至大中末。所记之事大体以年代先后为次,或有少数事迹在时间顺序上并非如编年史般严格,但整个下卷自九年起记,逐步展开的总体格局是显而易见的。而“刘皋被诬杀事件”正记载于“大中十二年后,藩镇继有叛乱”和“李景让为吏部尚书,抗疏”直谏之后。其后紧接着便是“上晚岁酷好仙道”之事。这样的记载顺序,已经将刘皋被诬杀事确定在大中末期,是毫无疑义的。只要是通读过《东观奏记》全文的学者,应该客观地承认,裴庭裕对刘皋大中十二年后被诬杀的时间定位是具体和可靠的。
《新说》在质疑《东观奏记》的同时。又顺势提出《新唐书》关于这一事件“时间记载只是根据上述情况(按,指《东观奏记》下卷记载)推测出来的,其实并不可靠”。这似乎有些强加于《新唐书》了。要知道,《东观奏记》下卷记载刘皋被杀事,是未记月份的,而《新唐书》却确切记载为大中十二年“三月”。难道《新唐书》的作者会先从《东观奏记》中得到一个“大中十二年”的大致时间,再编造一个“三月”的具体月份吗?如果这样想象,对欧阳修和《新唐书》都太不严肃,太不尊重了。
研究一下《新唐书》编修史应该知道,宋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主持史局后,局中编修官有宋敏求、王畴、范镇、刘义叟、吕夏卿五人(至和二年起增加梅尧臣)。其中宋敏求贡献尤为突出。敏求父宋绶,博学广闻,得其外祖杨徽之旧藏两万余卷,皆亲自校雠。敏求承传家学,藏书多达三万卷,精熟唐史,尝编《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并撰写过记述唐西京长安的《长安志》,记述唐东京洛阳的《河南志》。尤为史家称道的是,他凭借丰富的藏书和文献考订功夫,将唐朝实录空白的朝代都填补起来,撰成了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六朝实录共一百四十八卷,为《新唐书》重修做了最好的准备。实际上,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的修撰,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宋敏求的六朝实录的;也只有按照实录的体例,历史事件才会精确到年、月。因此,《新唐书·宣宗纪》明确记载大中十二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杀其刺史刘皋”,与《东观奏记》卷下将此事次于“大中十二年后,藩镇继有叛乱……上赫怒”之后完全相符,这更增加了《新唐书。宣宗纪》的可信度。看不到这样的历史事实,而去逆推《新唐书·宣宗纪》取资于《东观奏记》,再猜疑《东观奏记》事件编年的不可信,并以此来否定《新唐书·宣宗纪》的准确性,这就造成基本形式逻辑的颠倒混乱,徒生学术讨论的枝节。
四、关于“晚唐两许浑”问题
在《新说》中,作者提出了晚唐有“两个许浑”的问题,很能引起阅读的兴趣;但其中讨论的指向和方法,仍然使人不无疑窦。《新说》的作者认为,《丁卯集》的作者“诗人许浑”与《吴越备史》卷一中提到的“侍御史许浑”并非同一人。是否确实如此,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吴越备史》卷一出现“许浑”的两段史料。我在《许浑年谱稿》中引用的一段材料是:
成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浑、中使许计,赍璧来瘗秦望山之腹,以厌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
《新说》作者提出用以比照的一段材料是: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发长安。三月,敕遣卫尉卿许浑来宣谕,仍赐国信。是月,王子元臻与所聘杨氏至自淮南。夏四月,帝至洛阳,大赦。改元天桔,敕遣给事中郑祈、刑部员外郎杨永休(亦作永承)进封王为昊王。新说》的作者认为:“侍御史许浑从咸通中的六品下阶
官历约三十七八年而任从三品的卫尉卿,可信。因此《吴越备史》所记的卫尉卿许浑即侍御史许浑。那么,此许浑是否就是诗人许浑呢?如果按《年谱稿》许浑的生年为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算至甲子四年,即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则诗人许浑已经一百一十七岁了。”有此前提,《新说》作者进一步说:“诗人许浑果有如此高寿,且尚居官,其中之情理真伪,是不待多说即可明了的。”仅看这一段论证,《新说》所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令人赞同。因为谁都能够看出,《丁卯集》的作者“许浑”与卫尉卿“许浑”绝非一人,而且风马牛不相及!
很有意思的是,单从史料上看。一共有3个许浑:一是《丁卯集》的作者许浑,一是咸通年间的许浑,一是天复年间的许浑。这种情况,在逻辑推理上实际存在三种可能:唐代或有三个许浑,或有两个许浑,或只有一个许浑。我和《新说》的作者都采取了“两许浑”说;差别在于我认为大中年间曾任侍御之职的诗人许浑和咸通年间的侍御史许浑当为一人,而《新说》的作者则认为咸通年间的许浑应与三十七八年后在天复至天桔间方出现的卫尉卿许浑为同一人。说实话。《新说》的作者如果确实要在这个问题上论出“情理真伪”的话,应该做更深入的文献考索、挖掘,在咸通与天复两个许浑之间找到确切的证明,说明他们是同一人才行;仅用“侍御史许浑从咸通中的六品下阶官历约三十七八年而任从三品的卫尉卿”,来证明彼此同一,自谓“可信”,其实还缺少过硬的说服力,难以让人“遽可立断”。
《新说》的作者证明了成通中“侍御史许浑”前往秦望山厌胜所针对的事件,并非大中十三年的浙东裘甫起义“改元罗平”,而是钱缪吴越称王。这一点并非无见,笔者甚至也能给予首肯;但其证明“咸通中”前往浙东的“侍御史许浑”不可能是“诗人许浑”的几点申论却殊难成立。试看《新说》作者颇为自信的两点理由:其一是“以咸通元年而论,根据《年谱稿》所定的许浑生年(788),是年许浑已年七十三。唐朝一般官吏在七十岁即要悬车致仕,许浑年已七十三,怎能特殊而任侍御史出差呢?”其二是“许浑出差时为侍御史,据《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侍御史六人,从六品下。
而诗人许浑大中七八年已任虞部员外郎、郢州刺史。据《旧唐书。职官·二》,虞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又据《旧唐书,职官‘三》,……其刺史为四品下阶官员。诗人许浑的历官已如此,他在大中八年任四品下的郢州刺史后又无贬官的记录,则为何至咸通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呢?”
《新说》作者所提出的这两点理由实属似是而非。让我们先来看年七十三能否“特殊而任”某官问题。唐代有没有七十多岁而任官的特例呢?这里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盛唐的贺知章。开元二十六年(738)李亨立为皇太子,贺知章迁为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孙逖有《授贺知章等太子宾客制》,此年贺知章七十九岁。天宝二年(743)年老辞官,年八十四岁。另外昭宗天复元年“五老”之一的王希羽“特敕授官”为秘书省正字,其时王希羽恰恰正是七十三岁。唐代此类特例当复不少,为什么许浑七十三岁就不可能在某种重大事件发生时被“特命”授予某官呢?
至于《新说》认为许浑已历官至郢州刺史,“后又无贬官的记录,则为何至咸通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呢”?我认为,这涉及到唐代重视京官而产生的官场文化现象。许浑在大中末郢州刺史任满后,并不能排除特授侍御史的可能性。正如晚唐崔嘏《授裴谂司封郎中依前充职制》所说:“台郎望美,词苑地高。”一般来说,唐代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诰决定,但御史、拾遗、补阙、郎中、员外郎等台省官员,虽然只有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但都须上报,由皇帝亲自任命。且此类台省官员往往正是由州蒯史迁授。俯拾即是的例子如:韦应物由滁州刺史召人为左司郎中,杜兼自濠州刺史人为刑部郎中,杜牧历任黄州、池州、睦洲刺史后,擢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许浑任睦州刺史后擢虞部员外郎。他们的京职品秩皆低于地方郡守,但京官“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而且只有循吏方获此荣。如果认为这样的现象是“降职”而不是擢升的话,是有违唐代官制常识的。
当然,我更倾向于许浑此次被派遣浙东,其“侍御史”并非实授,只是因为许浑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一台省职位,便借以称呼,这正是唐人尊称京职的习惯。方干曾有《许员外新阳别业》诗赠许浑,其有“多谢郢中贤太守,常时谈笑许追陪”云云。既称“郢中贤太守”,则许浑正在郢州刺史任上,虽然这个职务品秩高于员外郎许多,但称其为“许员外”正是表达一种敬仰。杜牧会昌二年有诗赠时任湖州刺史的张文规,诗题为《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大中二年杜牧有诗赠时任苏州刺史的卢简求,诗题为《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都是尊称他们过去的台省官职,称许浑为“侍御史”或许也是出于这样的习惯。
最后,关于这个问题要特别提出一条材料,即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关于许浑赴南海幕府与诗人房千里交往的记载:
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
需要说明的是,许浑南海之行在开成元年(836),其时尚未任监察御史,也就是说,“侍御”并非许浑赴南海时所带京职。正因为如此,《南海非》中的“许浑侍御”之谓就特具参考价值了。范摅乃咸通、乾符间人,撰写《云溪友议》时离许浑去世时间较近,其事迹他相当熟知。这里范摅对许浑以“侍御”称之,无论是尊称,或者是对其最后特授官职的记录。都说明成通年间出现“侍御史许浑”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活动的客观反映。至于“两个许浑”的问题,若云唐代有“两个许浑人物”乃不误,但若云唐代有“两个许浑侍御”,则并非事实。成通后三四十年的那个掌邦国器械、总武库的“卫尉卿许浑”和诗人许浑实在是遥不相干的,在进行晚唐诗坛人物研究时,这个同姓同名现象其实进人不了话题。
综上所证,许浑之去世应已人咸通年间了。这一看法不仅仅关合了《吴越备史》的记载,同时还有大中十二年许浑《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的写作事实以及顾陶人咸通年间所写的《唐诗类选后序》为支撑,也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十六之许浑“大中末为郢州刺史”的记载完全相符。我在《许浑年谱稿》将其卒年订于“咸通二年或稍后”,说得略微宽泛些,是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许浑的卒年问题到底应如何考订?本文当然不会是结论,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心这一话题。由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覆盖面对晚唐一批作家都有一定的涉及,因此继续做更为深入的考证,对晚唐文学研究确是很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