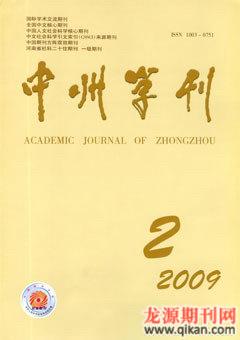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
林小云
摘要:《吴越春秋》作者运用史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审美形象的过程。其方法有四种:1、传闻异辞,择善而从;2、博采史料,重新组合;3、曲意改铸,移花接木;4、点染生发,踵事增华。作者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对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审美把握,用审美理想之虚驾驭史籍材料之实,经过艺术的想象和概括去创作。这种叙事手法,已经从历史领域跨入了文学领域。
关键词:历史;文学;叙事;想象;艺术构思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94-05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演绎的是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自《隋书·经籍志》将《吴越春秋》列入“史部·杂史类”后,古代学者多将之看作历史著作。随着对古代小说观念和作品的研究,现代学者渐渐认识到《吴越春秋》的文学价值,多数倾向于把它看成小说。但遗憾的是,这些探讨多数仅从《吴越春秋》中史实的真实与虚构上来立论,认为《吴越春秋》的记载虚构多于真实,因而是小说。但我们认为,如果仅仅以书中史实与虚构之间简单的比例关系来界定它是史书还是小说,是不够科学的。众所周知,史书中也有虚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史书中虚构的性质和功能与小说是不一样的。史书中的虚构,是为了补充事件发展过程中不足的链条,是历史学家重现历史、反映历史的重要手段,它追求的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小说的虚构想象,则是作者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的创作手法,它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因此,从分析《吴越春秋》的虚实关系人手,探讨它是史书或是小说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分析它的哪些材料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而应注重探讨这些虚构与想象在整部作品中的性质和功能,也就是探讨作者如何通过想象和虚构来建构自己的审美形象体系,从而正确认识它在叙事上与史传的区别。
作者的创作意向决定了他处理史实和虚构关系的创作原则。元代徐天枯在《吴越春秋序》中指出:“其言上稽天时,下测物变,明微推远,燎若蓍蔡。至于盛衰成败之迹,则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议论,种、蠡诸大夫之谋,迭用则霸;子胥之谋,一不听则亡;皆凿凿然,可以劝戒万世,岂独为是邦二千年故实哉!”明代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也说:“呜呼!孟轲氏称‘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观二国之兴而偾,偾而兴,斯昭昭矣。骄畏之殊,兴亡所系;忠谗之判,祸福攸分。可畏哉!”二序都认为《吴越春秋》昭示了盛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具有劝惩意义。的确,赵晔对吴越争霸斗争的描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楚平王的荒淫无道,导致了楚国的几乎灭亡;阖闾的任贤使能、虚心纳谏,使吴国国力大增,破楚伐越;夫差的穷兵黩武、忠奸不分,造成了吴国的灭亡;勾践的苦身劳心、励精图治及群臣的尽忠事君、竭力报国,让越国得复宿仇,灭吴雪耻。这一切,正是作者通过此书意欲留给后世的昭示。他的创作,自始至终也都体现了这一番用心。因此,他在处理史实和虚构关系时始终遵循着这么一个原则,即服从整体艺术构思,构建以主要人物为主的审美形象体系,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当我们把史籍记载和《吴越春秋》的情节对照来看时,作者运用史料进行艺术创造的处理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充分挖掘和筛选具有典型性和富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史料,重新进行叙事意象的组合。这种组合不是简单的对史料的取舍和加工,而是将各种素材组成一个系统,围绕着形象,进行一种整合性的审美创造,从而创造出比原始史料更高的艺术境界。赵晔通过“传闻异辞,择善而从”、“博采史料,重新组合”、“曲意改铸,移花接木”这三种方法来贯彻这个原则。
第二,在极其简单的史实记载的基础上进行虚构。这种情况下,由于史料极其简单,因而作者所能发挥的想象空间很大。但是这种虚构又没有离开基本事实所辐射的范围,没有离开总体的艺术构思。这种情况在本书中具体表现为“点染生发,踵事增华”这种方法。
以上这两种原则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对史料的运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作者运用史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想象和创造建构审美形象的过程。一、传闻异辞,择善而从
当代史学研究理论认为,史传的记载都经过了作者的主观筛选和编排;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史传都有作者的主观因素在里面。作者在选择什么、强调什么的时候,头脑里都有一种价值观念在进行衡量。同样,赵晔著《吴越春秋》,当然也是有所为而作,这样他在面对众多史料的时候,当然会用他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筛选。吴越争战是春秋末期一场惊心动魄的争霸斗争。吴国在北服齐晋、国势最为强盛之时却被越国所败,且最终为越国所灭,这无疑给当时的中原诸国以极大的震骇,也给后世以极为深刻的教训;而越国,一个僻远的蛮夷小邦,却能在一段时间内称霸于江淮之上。其原因何在?这些都是统治阶级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场争战,不仅正史有载,其它众多著作如《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也都有相关的记载。但是,这些著作中对吴越之事的记载却多有不同。对于这些传闻异辞,赵晔并非毫无标准地随机选用,而是有自己的取舍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传达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是否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例如,有关越国先祖的问题,赵晔之前的典籍中记载着两种不同的传说:一种是以越国为芈姓,与楚国同为祝融之后,如《国语·郑语》、《世本》、《墨子·非攻》等;一种是以越国为大禹之后,以《史记》为代表。对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赵晔选择了《史记》带有神奇色彩的“夏少康封庶子于会稽”的说法,浓墨重彩地铺写了大禹治水的神奇故事,着重刻画了大禹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勾践作为大禹的后代,忍辱为国,卧薪尝胆,最终灭吴雪耻。也就与大禹的精神相映衬,使整个越民族那种忍辱负重、顽强不屈的精神凸显出来了。这里,作者虽然没有对史实进行任何的增饰和改造,而仅仅是对史籍中已有的素材进行筛选,但这种筛选却已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审美创造。越国先祖的问题,如果孤立来看,无论是祝融之后,还是大禹之后,都只是“出身”问题,无改于越国为蛮夷之邦的现实。但一旦把它熔铸入整个作品的艺术系统中,这就不是简单的“出身”问题,二者的性质就有了很大的差别。越国为祝融之后,无非就是神化越国的先祖;而为大禹之后,却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整个越民族那种忍辱负重、顽强不屈的精神。也就是说,作者所选取的这段史料,已不仅仅是“死”的史料,而已经“长入”了作品的人物性格中,成为整个作品有机生命的“活”细胞,极富生命力。
同样的,赵晔在处理伍子胥对已死的楚平王的报复的史料上,也体现了他的审美创造。伍子胥是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因此,作者在有关伍子胥史料的选择上也是深具用心的。当伍子胥率
军攻人郢都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是如何来宣泄十几年的积怨的?秦汉时期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鞭坟说。《吕氏春秋·首时》:“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谷梁传·定公四年》:“挞平王之墓。”此外,《淮南子·泰族训》、《说苑·奉使》等书也均从此说。另一种为鞭尸说。《史记‘伍子胥列传》:“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但是,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楚世家》中却也主鞭坟说。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塑造了一个“弃小义,雪大耻”的“烈丈夫”形象,对其复仇行为加以肯定,体现了他对伍子胥这一人物的赞赏。可见,鞭尸说实是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为了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而曲意改写的。自此之后,这种说法渐渐流传开来。扬雄《法言‘重黎》云:“胥也,俾吴作乱,破楚人郢,鞭尸藉棺,皆不由德。”王充《论衡·定贤》也说:“伍子胥鞭笞平王尸。”对于这两种传闻,赵晔采用了鞭尸说,因为鞭尸说更有利于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伍子胥的性格特点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观其出亡途中对申包胥所说“必覆楚国”之言及听说楚平王死,自己不能将报仇之举加于其身而“坐泣于室”的举动,其报仇之念是何等地深入骨髓。因此,为了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吴越春秋》不仅采用了《伍子胥列传》中的鞭尸说,而且还在其基础上对伍子胥鞭尸的细节作了进一步的虚构。《阖闾内传》曰:“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掘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谄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吴师入郢,距楚平王之死已有十几年的时间,楚平王大概早就化成一堆枯骨了。践腹掘目之举,恨诮之语,虽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却十分切合伍子胥当时痛报宿仇的心理,符合伍子胥强烈反抗性格的发展逻辑,在艺术上是真实的。复仇是伍子胥一生中的大事,而其性格特征也是在复仇的过程中逐渐展示出来的。当伍子胥历尽艰难终于得报宿仇时,也可以说是其性格发展的一个顶峰。因此,对伍子胥这一复仇举动的描写,对塑造其形象无疑有着关键的作用。作者在这里的处理无疑也使得伍子胥这一形象的性格更为鲜明突出。其他又如《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佯籴”事。在《吕氏春秋》中,勾践是因为越国闹饥荒才向夫差求籴的;三年后,又乘吴国闹饥荒之际,以怨报德,借机灭吴。《说苑·权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则有所不同:“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在这里,勾践请籴是为了试探夫差虚实,其原因与《吕氏春秋·长攻》和《说苑·权谋》不一样。比较两种说法,因饥荒请籴事出偶然,佯籴则更见越国君臣的复仇用心。因而《吴越春秋》采取了《史记》“佯籴”的说法,而且运用艺术想象力,精心改造了吴国饥荒的原因,乃是夫差中了勾践之计,用越国归还的被蒸过的精粟作种造成的。这样,整个“佯籴”事件就成了越国君臣为复国而精心谋划的整套阴谋中的一个环节,这就使故事更为腾挪跌宕,越国君臣处心积虑以报强吴的行为用心也就更为鲜明突出。
二、博采史料,重新组合
《吴越春秋》的史料来源极为广泛,除正史的记载外,多数散见于各种诸子著作中。赵晔将这些零星材料连缀成篇,并且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和虚构,使之在整个作品的叙事中产生新的作用,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例如要离刺庆忌的故事,就是由散见于各书的三则小故事连缀而成的。一为壮士椒丘新人河斗水神的故事,本事散见于《韩诗外传》卷十、《论衡·龙虚》;二为要离在丧席上奚落战败过水神的东海勇士椒丘新,并于夜间开门僵卧等待他来行刺时责他“三不肖”,终使椒丘訢投剑而去。本事仅见于《韩诗外传》卷十;三为要离刺庆忌,散见于《战国策·魏策·唐雎不辱使命》、《吕氏春秋·忠廉》、《说苑·奉使》等篇,都是零章散句。这三个故事本来都与伍子胥毫无关联。《吴越春秋》则把这三个故事连缀起来,并对之进行了一番创造,使之在全书的审美形象体系中产生了新的作用。
首先,他把第一则故事作为第二则故事的铺垫,以椒丘新的匹夫之勇来衬托要离的“士之勇”,而前二则故事又均为后一个故事张本,同时也使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要离,是否真能刺杀“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尝追之于江,驷马驰不及;射之圈接,矢不可中”的庆忌呢?等到要离在江中“顺风而刺庆忌”时,读者那种将信将疑的心理才得到了释放。其次,赵晔又把要离的事迹与伍子胥联系起来——要离奚落椒丘新之事乃是通过伍子胥之口被告知吴王的,要离因伍子胥的强力推荐得以面见吴王,遂定下苦肉计,刺杀了庆忌。这样,要离刺庆忌的一幕,如同专诸刺王僚一样,成为伍子胥导演出来的有声有色的一出惊险剧了。最后。赵晔还改造了要离自杀的地点及方式。在《吕氏春秋·忠廉》篇中。要离死于归吴国后;《吴越春秋》将其自杀的地点改为江陵,让他在未面见吴王时以“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的“自责”而自杀,表明其行为并不以名利为目的。赵晔还把其自杀的情节处理得更为惊心动魄:要离先是投水自杀不成,便又自断手足。服剑而死。这样,要离的性格就得到了艺术性强化,表现出上古“侠士”强悍的个性和视死如归的风度。赵晔对要离事迹的处理,可谓别具匠心,不仅塑造了一个“轻命重气”的勇士形象,更对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较大的衬托作用。伍子胥不因要离“细小无力”而轻视于他,而是从要离辱椒丘訢之事看出他具有一种常人所不及的内在素质,因而向吴王力荐,显示了他深刻的洞察力。正因为伍子胥看问题不被表象所迷惑,才能在吴国几乎举国为越国顺从的表象所迷惑蒙蔽的情况下,见微知著,深谋远虑,看出越国的实际用心及其对吴国的潜在威胁。作者在这里对这些史料的采用,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有本即录”,为传奇而传奇,而是使之进入整个叙事结构系统中,与人物形象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富艺术感染力。作者的艺术创造力于此可见一斑。
三、曲意改铸,移花接木
《吴越春秋》的作者面对众多的史料,从创作的需要出发,大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改造,以展现人物性格,表达作者的态度,从而建构了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审美形象体系。在《吴王寿梦传》中,作者写吴王诸樊的死是因其让位于季札而不得,遂“轻慢鬼神,仰天求死”。而事实上,诸樊的死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写得很清楚:“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可见诸樊乃是战争中死于敌人箭下。杨伯峻先生注曰:“《吴越春秋》谓诸樊欲传位于季札,仰天求死云云,不足信。”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来说,《吴越春秋》的记载当然是失实的,不足为信。但赵哗为什么不从史实,而做如此处
理呢?显然。以赵晔的儒家学者身份,不可能不熟悉《左传》中有关的记载,但他当然也不是简单对史传记载一概采纳。他之所以舍弃史书中的记载而作如此的改头换面,是有其审美形象建构上的考虑的。赵哗在首章记叙吴国的由来时,对吴国的始祖太伯“三以天下让”的行为予以浓墨重彩的叙写,奠定了吴国以礼让著称的基调。此处记载诸樊让国于季札而不得。不得已即位,故欲求速死以期传位于季札,更是进一步渲染了吴国的礼让之风。但是,吴国的这种让国高风,到了公子光、夫差日中代已荡然无存:公子光弑吴王僚而自立、夫差即位前日夜谋求王位,这与太伯和诸樊、季札的行为形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但是,即位后的夫差虽残暴但尚不失仁义,败越后“封地百里于越”,又在越国闹饥荒时慷慨地借以粟万石;在与齐国争霸并败齐于艾陵后“乃使行人成好于齐”。这一切虽是出于夫差“怀小服远”以称霸诸侯的目的,但也未尝不是吴国先辈的礼让之风在夫差身上烙下的印记。显然,作者通过改造诸樊的死因,渲染了吴国的礼让之风,不仅使之与公子光、夫差的争位形成鲜明的对比,并通过这种对比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评价,而且又为下文描写夫差的复杂性格做了铺垫。
《吴越春秋》中曲意改铸,在史实素材上虚构的例证还很多。比如《阖闾内传》中伍子胥交代白喜(即太宰嚭)的家世时说:“白喜者,楚白州犁(即伯州犁)之孙。……白州犁,楚之左尹,号日卸宛。事平王,平王幸之,常与尽日而语,袭朝而食。费无忌望而妒之,因谓平王曰:‘正爱幸宛一国所知,……。平王大怒,遂诛卻宛。”此处,作者把白州犁和卻宛当做一人。但《左传》中伯州犁和卸宛却是不同的两个人。《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杀太宰伯州犁于郏。”公子围即后来的楚灵王,楚平王之兄。则伯州犁乃是死于公子围之手,与楚平王、费无忌毫无瓜葛。又《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郁宛直而和,国人说之。鄢将师为右领,与费无极比而恶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卻宛焉……(令尹)招鄢将师而告之。将师退,遂令攻卻氏,且燕之。子恶(即卻宛)闻之,遂自杀。”则卻宛于昭公二十七年死于子常、费无极与鄢将师之手,比伯州犁之死晚了二十六年,此时楚平王已死。可见卻宛之死亦与楚平王无涉。但赵晔在书中把伯州犁与卻宛二人合而为一,将他们的死都归罪于楚平王、费无忌。这样一来,虽然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复存在,但却不仅突出了楚平王的残暴昏庸和费无忌的谄佞奸诈,而且也使得白喜与伍子胥有了同仇共怨。伍子胥正是出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之心才引荐白喜,与之俱事阖间;否则,以伍子胥为人的精明、看问题的深邃,如何会犯这种错误?更何况被离还警告过他不可与白喜亲近。正因为伍子胥此时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报仇,所以将曾遭楚平王残害的人均引为同道而不顾及其他,终于给自己及吴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见,作者这样处理,不仅强化了伍子胥的复仇意识,而且为下文伍子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再如太子友谏夫差事。《夫差内传》中太子友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隐语暗示夫差:若吴国伐齐,越国就会伺机而动,有可能吃掉吴国。“螳螂捕蝉”的寓言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经常出现。《庄子·山木》、《战国策·楚策·庄辛谓楚襄王》、《韩诗外传》、《说苑·正谏》等均有记载。其中《说苑·正谏》的记载与吴越事有关:“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日:‘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吴越春秋》关于太子友谏夫差的情节显然是来自《说苑·正谏》,但又不是简单地挪用,而是更为曲折。赵晔不仅将进谏之人由舍人少孺子改为太子友,亲近了进谏之人与其进谏对象的关系,突出了夫差的刚愎自用,而且太子友的劝谏之辞更是一波三折,极具说服力。他通过层层设喻,把夫差引入自己所设的情境中,引导夫差自己说出“天下之愚,莫过于斯:但贪前利,不睹后患”的看似醒悟的话。在此基础上,太子友才进一步明确地说出“夫吴徒知逾境征伐非吾之国,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人五湖之中,屠我吴国,灭我吴宫。天下之危,莫过于斯也”这些振聋发聩之言。但是,如此具有警醒之力的劝谏,最终却还是没能阻止夫差的执意北伐齐国。这样一来,不但增强了文章的故事性,而且给读者的心理期待以极大的反差,有力地突出了夫差的性格特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在明知自己北伐齐国的行为可能给越国以可乘之机的情况下,夫差为了满足自己称霸中原的野心,依然不顾后果,执意伐齐,其后果当然是可悲可叹!
四、点染生发,踵事增华
上面分析的三种史料运用的方法,都是对史籍中具体素材的一种意象整合,以使原有的素材融入到新的作品中,在作品审美形象的建构上产生新的功能。这是在史实基础上的一种再造想象。下面要分析的另一个方法,则是一种创造想象。作者由史籍中的零星记载生发开去,对之加以大肆的铺张叙述,使其情节更加丰富多彩,跌宕错落,富有传奇性。如伍子胥逃亡吴国之事,《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只说“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吁”,极为简略。《史记·伍子胥列传》则对伍子胥的逃亡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写,写了伍子胥奔宋、奔郑、过昭关,得渔父帮助,途中生病乞食等事,表现了伍子胥逃亡的艰辛,突出了他忍辱负重的精神,但还是较为简略。《吴越春秋》又在《伍子胥列传》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铺张,敷衍出长达六百余字的一段文章,详细记叙了伍子胥智过昭关,得江上渔父和击绵女帮助之事。特别是后面两件事,情节更是曲折多彩。江上渔父,《伍子胥列传》中只记其渡子胥及不受子胥之宝剑;《吴越春秋》中则不仅详细记叙了渔父渡伍子胥过江,而且写了他为替伍子胥保守秘密而自沉于江。击绵女,《伍子胥列传》中并未出现;《吴越春秋》中则写了她帮助伍子胥后,自以为“越亏礼仪”而投水自尽。《吴越春秋》的这一番描写,不仅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敢于冒险救难、舍生取义的渔父形象和一个为援助走投无路之人而甘于牺牲自己名节和生命的击绵女形象,表现了伍子胥逃亡的艰辛及其身处险恶形势、窘困处境之际的机智和谨慎,呼应了前文中伍奢对他的评价,而且通过江上渔父和击绵女的舍身相救,突出了伍氏的无辜,更表现了人们对伍子胥的同情及对楚国统治者楚平王的不满,反映了楚国的民心向背。这种烘托不仅为后文伍子胥的复仇涂上了正义的色彩,并为下文《阖间内传》中楚军引军击郑时伍子胥因应江上渔父之子的请求而释郑回师,及过濑水时投百金以报击绵女埋下伏笔。这种写法生动地揭示了伍子胥有恩必报的精神世界,使得伍子胥的形象更为完整丰满。
《吴越春秋》对勾践夫妇和范蠡入臣于吴之事的创造性构思亦别具一格。此事在全书的叙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有了勾践的忍辱人臣,才换来了越国的休养生息及其后的灭吴雪耻,勾践的性格由此也才得以充分地展示。然而。有关此事的史料却很有限。《左传》中没有记载;《国语》中虽有,但也仅有三十几字:
卑事夫差,宦事三百人于是,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越语上》)
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昊。(《越语下》)
此外,《孟子·粱惠王下》有“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之言,《韩非子·喻老》中也有“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的记载。不过这些记载均为零星之语,谈不上情节和故事性。但正是这些极为简括的史料,给作家以极为广阔的想象与虚构的空间,使之能够依据总体艺术构思,沿着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叙事结构发展的脉络去想象。事实上,《吴越春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越国众大夫“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勾践与范蠡秘议和、勾践为夫差尝粪疗疾等离奇情节。从“临水祖道”时“仰天太息,举杯垂涕”的心灰意冷、颓唐丧气到“斫剉养马……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的深藏不露,再到为夫差尝粪疗疾时的坚忍,勾践的性格一步步地在发展变化。此时的他,已非新败于吴时尚需群臣的劝谏才能稍微有所振作的君主,而是一个忍辱负重的阴谋家。有了在吴国的这一番磨难,勾践归国后才能又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灭吴雪耻。从情节的设置上来说,有了勾践在吴国时取悦于吴王夫差的一系列言行,夫差才为其蒙蔽,终于放其归国,才有了勾践归国后的一系列阴谋。并且,围绕着勾践入臣之事,吴越两国众多人物的性格面貌也得以展现出来。范蠡忠于勾践,足智多谋,使勾践赢得了夫差的信任;夫差欲以仁德怀人,终于被勾践的表面顺从所迷惑,放虎归山;太宰瓠收受越国贿赂,欲为勾践开脱,因而迎合夫差好大喜功、欲以仁德为名的心理,力劝夫差赦免勾践;伍子胥则看出勾践“内怀虎狼之心,外执美词之说”,将为吴国大患,而力谏夫差除掉勾践。也就是说,作者把不同的人物置于同一矛盾中,通过人物的不同态度来展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清人李慈铭曾指责赵晔“东海鄙儒,其撰《吴越春秋》,皆以乡曲猥俗之言影撰故事,增成秽说”。如果我们也拘泥于传统的虚实观念,以史料是否真实去简单地比照衡量,当然会认可他的这种看法;但如果我们能够突破传统虚实观念的束缚,从全书的艺术构思出发来看待这种虚构,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难以证实的事件,正是赵哗艺术能力的体现。这些在史书点滴记载的基础上以想象为手段虚构创造出来的情节,不仅在全书的叙事逻辑上起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而且建构了以主要人物为主体的相互衬托、相互作用的性格群体。也就是说,《吴越春秋》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被李慈铭斥为“秽说”的情节,才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黑格尔曾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句话强调了想象与创造在审美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作为依傍史书的著作,《吴越春秋》是通过对史料的灵活运用来完成这一重要步骤的。作者对典籍上的某些材料搞了张冠李戴的移植,有所取舍,有所夸张。这是运用史料的艺术需要,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和人物性格发展脉络的完整统一。作者增加的一些细节描写和情节渲染,也许并非事实之真,但也没有违背情理之真,没有违背特定历史情况下人物可能的表现。经过作者的取舍加工、生发点染,原本简洁干巴、孤立的史实记载被演绎、整合到整个作品的情节中去,成为作品叙事结构的有机成分,不但使审美形象得以形成,而且构筑了与人物性格相协调的审美情境。尽管作者处理史料的手法多种多样,但始终都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对历史的现实进行具体的审美把握,用审美理想之虚驾驭史籍材料之实,经过艺术的想象和概括去创作。这种创作手法,已经不是历史的,而是文学的了。这正是这部作品在叙事艺术上对史传的一种超越,也是它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