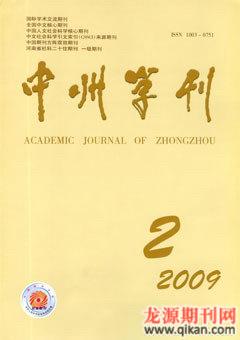丁文江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刍议
欧阳哲生
摘要: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主要代表。过去学界在论及这一论战时,一般论者只注意丁文江与张君劢的思想差异,往往忽略了他与张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研究系背景;只纠缠于对参与论战者文本字里行间的歧异解释,忽略了他们在论争背后的“策略”运用,特别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争夺话语权的意图。
关键词:丁文江;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科学派;玄学派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80-05
一
在科学与“玄学”论战的两大派中,丁文江、张君劢分别是两派挂帅的人物。丁文江与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前有许多类似经历:其一,两人同岁(1887年出生)同省,张是江苏嘉定人氏,丁是江苏泰兴人。其二,两人都出生在农村的大家庭,且排行第二。张出生在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其父生子女十四(成人者男六女五);丁出生在一个富绅家庭,其父生子7人。其三,两人早年都有过报考传统功名的经历,旧学根柢不错。张6岁开蒙读书,12岁考入上海广方言馆,1902年参加宝山县县试,考中秀才。丁亦6岁入塾读书,13岁考秀才,博得泰兴县知县龙璋的赏识。其四,两人都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官费补助,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而在留学期间,又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与立宪派人或革命党人发生关系。张于1906年被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预科学习,1910年夏毕业。留日期间,张加入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创办《宪政新志》。丁1902年赴日留学,在留日期间曾参与《江苏》一刊的编辑;1904年负笈英伦,留英期间,与吴稚晖来往密切,并随其在伦敦拜访过孙中山先生,留日、留英期间均受到官费补助。区别之处:张学政治学,丁学动物学、地质学。其五,两人均为1911年学成回国,随后参加了清朝学部为游学毕业生举行的考试,两人都有过在北京政府供职的经历。张君劢于1911年5月经过考试被清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初年,他参与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民主党等,周旋于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之间;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6年回国;参加了反袁斗争,成为梁启超研究系的骨干。丁文江于1911年9月经过考试登录“格致科进士”,1913年进入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工作,以后创办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相比而言,张沉迷于政治,始终没有放弃对政治的追求;丁早期基本上不涉政治,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地质学者或低阶技术官员。如果说,丁文江与张君劢早期生涯有许多的相似点,那么,两人应梁启超之邀,共赴欧洲考察,则是丁、张二人联结的一个交汇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结谊的开始。赴欧考察任务结束后,张继续留在德国,拜师著名哲学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攻读哲学达两年之久,1921年底与应邀来华讲学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一起回到中国。而丁只身前往美国,作了为期两个月的短期考察。比较而言,张君劢已有多次办报的经验,在公共舆论界获得了一定知名度,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比丁文江更为长久,与政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二
讨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文字已是汗牛充栋,但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一论战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自然有些问题(如对张、丁之争的评价),论者可以各持己见,但有些涉及基本史实的描述则需要共识。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作一个讨论。
1、论争(或论战)的名称
关于论战的名称,究竟是定为“科学与人生观”论争,还是命名“科学与玄学论战”?前者是以主题命名,后者是以派别命名,我以为以主题命名为宜。作为论战文字结集的两部书——《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人生观之论战》(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其书名实际上已表达当时人们对这场论战名称的处理,即以论战主题命名。只是偏向于科学派的亚东图书馆冠以“科学与人生观”,强调论战是以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为主题;偏向于张君劢的泰东图书局以“人生观之论战”命名,直截了当地强调论战的主题是“人生观”。两书书名虽在名称上各有所偏,但并无不可,以之概括所收文章和作为论战名称均可成立。而以“科学与玄学”论战冠名,则明显有偏于扬丁贬张之嫌。因为“玄学”一词首先出自丁文江的回应文章标题——《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文章以“玄学鬼”指称张君劢,实在有贬损张氏之意。以后,作为对立一方的梁启超、孙伏园、林宰平、范寿康等在文章中受到丁文江的牵引,不自觉地沿用此说,“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说法遂传播开来。问题是,在中文的语义中,“科学”是褒义词,“玄学”就其与“哲学”对应这一面来说,可以说是中性词,19世纪二、三十年代哲学界许多人亦主张此说;而就其寓含玄思、玄妙、玄理,则又略带贬义,故从语义上来判断这两派,科学派具有天然的优势。因而我们以丁氏的文章命名这场论战,无疑已预设了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尚未研究,即预设立场讨论问题的方式,在确立“学术价值中立”原则的当今,理应为我们所摒弃。一些论者迄今仍对“玄学派”表示“同情的理解”,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主义”倾向表示质疑,这表明这一问题仍有不确定的空间。实际上,“五四”以来的许多思想论争,如此前的“东西文化问题”之争、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多以主题命名,这种处理相对为宜。
2、论战的主要代表
张君劢作为一方的代表,似无争议。另一方的四位代表:胡适、陈独秀、吴稚晖与丁文江,胡、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地位,而丁文江作为“科学派”的主要代表,却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矮化甚至忽略。这里夹杂一个因素,即亚东图书馆在为此次论战结集出版时,请陈独秀、胡适作序,以为该书造势。陈独秀在论战过程中没有写过一篇文字,他的序文不过是借题发挥。胡适在论争中也只写过一篇简短的调侃性文字——《孙行者与张君劢》,以示声援;丁文江写作的第一篇文字《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与他通报过,他是丁文江背后的最有力支持者;他写作序文,可以说是从后台走到前台,宣告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其“胡适的新十诫”。在文字上,陈独秀逐个点评,酣畅淋漓,脾睨一切,颇有横扫千军万马之势,表现了初兴的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气势。胡适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语意幽默,给“科学派”增添新的证词,强化了科学主义的思维定式。可以说,陈、胡的序文喧宾夺主,使前此颇有大将风度的丁文江反而略显逊色。有趣的是,论战结束后,张君劢无论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还是在10年后发表的《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中,都只字不提自己的论敌丁文江的名字,而只言胡适、陈独秀、吴稚晖三人,丁文江反而被有意地淡化甚或遮蔽了。但从丁文江给论战带来的“科学”特质看,从其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主题看,他都是其
他人无法替代的一个要角。
3、丁文江与张君劢的思想渊源
罗家伦曾将丁文江与张君劢之间的分歧概括为:洛克的经验论对抗康德二元论、马赫、皮尔逊知识论对抗德里施生机论、赫胥黎存疑论对抗倭铿精神论。点出丁、张思想的西方来源的国别分别是英美与德国,这一点并不为错。但将丁文江的思想来源仅归结于洛克、马赫、皮尔逊、赫胥黎这几个人,则似有简略之嫌,至少从丁文江所列“平日自己爱读的书”可以看出他喜读的书目还有达尔文、罗素、杜威等人的著述。丁文江特别指出“要知道君劢所信的正统哲学在德国政治上发生的恶果,同对于欧战应负的责任,不可不读”杜威著《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可见他对德国文化的反感与杜威的意见有密切关系。丁文江喜欢的另一位哲学家罗素在哲学上既排斥法国的浪漫主义哲学(如卢梭)和生命哲学(如柏格森)等,也不喜欢德国古典哲学(如黑格尔),他有着英国人那种特有的自信和自由主义情结,在哲学上将数学与哲学相结合,自成一派,他的思想风格、他不信仰基督教的态度都极大地影响了丁文江。
有关倭铿(Rudolf Eueken)与张君劢的密切关系已为众多论者论及,张君劢本人亦有明白交待。而张氏与当时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关系,则鲜见人提及。实际上,卫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热衷,对张君劢以及民国初年的孔教论者(如康有为、陈焕章)亦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他是民国初年孔教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卫氏1899年来华,很快醉心于学习中国语言和儒学。卫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以神学家和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他对梁启超推崇备至,曾向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推荐梁启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对随新文化运动而进入中国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思想和实验主义,他抱有极大的抵触情绪。1924年他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关于老子、孔子和康德的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卫理贤当众宣布:“我想借此机会向听众介绍一点真正深刻的哲学,因为这些年从美国引进来的怀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哲学实在令人可怕。”明显表现出对胡适引介的美国哲学的不满。张君劢因在德国留学的关系,加上与梁启超的师生关系,与这位德国的“中国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卫氏的做法对梁、张自然是莫大的鼓励。
张、丁之别除了思想理论渊源的区别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即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沦为战败国,其国内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即是对西方现行的文明制度的怀疑。张君劢对西方文明弊病的反省,实际上与德国思想界寻找自身出路的倾向有关。而英、美两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战后享受了胜利的果实,其自信心自然大增,故从英国归来的丁文江和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着与张君劢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战后世界形势的观察也有其不同的视角,他俩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信心,是与英美在战后的强势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4、对论战的几点认识
其一,一般论者习惯于根据《科学与人生观》或《人生观之论战》这两部文集来研究这场论战,将这场论战看成是一场混战,很少回到历史的现场。其实,丁文江、张君劢及其助战者都在各自的阵地上拉开了阵势。丁的三篇文字相继发表在北京发刊的《努力周报》,站在他这一边的论者遂以《努力周报》为主要阵地,如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第53号)、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第53号)等,而赞助张君劢的论者则多在具有研究系背景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文章,如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1923年5月13日)、孙伏园《玄学科学论战杂话》(5月30日)等。当我们还原历史时,从两方的阵营来看,科学派一边的作者均用真名真姓,显得理直气壮,特别是章鸿钊、任鸿隽等科学家的加盟,改变了此前科学家基本上不参与思想论争的格局。玄学派一方的作者虽有梁启超、林宰平、张东荪的助战,但基本上是人文学者或哲学家,知识背景相对单一,有几篇文章还以笔名、化名发表,明显表现出底气不足。
其二,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论争,以及《努力周报》与《时事新报·学灯》的对阵,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在文化思想上的分化。丁文江的另树一帜,表现了他力图摆脱梁启超文化的影响,以确立自己在北京知识界的一席之地。与胡适等北大派共同组织“努力社”,创刊《努力周报》,实际代表丁、胡重组力量的尝试。此前,丁文江几乎完全在梁启超所控制的系统内活动,胡适对梁氏也执礼甚恭。在此次论战中,梁启超仍然以长者的姿态、以暂时中立人的身份宣布《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别要效尤。”但从论战的发展来看,丁文江明显摆脱了梁氏的思想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取向。
其三,人们喜以科学派的胜利来说明这场论争的结束,从当时科学派所占上风的声势上,从介入讨论的人数偏向科学的人生观阐释上,这样看并不无道理。但是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笼统,科学派只是一个临时的统一战线,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且不要说在论战中,丁文江和赞助他的其他科学派人士观点并不一致,就是陈独秀、胡适为论战总结的序文也是各说各话、别有所为,这是一场没有结束的论争,当时陈独秀即抱这样的看法。张君劢也并没有折服于自己的论敌,他在《人生观之论战》一书序中(1925年)和以后发表的《人生观论战之回顾》(1934年)、《我之哲学思想》(1952年)等文字中继续申述自己的思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邓中夏与陈独秀相呼应,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人生观的问题。胡适以后多次以人生观发表演讲,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又不同于倾向文化保守主义的怀疑、求实、求真的人生观。也就是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实际加剧了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三
论及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论争,一般论者只注意到张、丁之异,往往忽略了他俩的相通之处;只纠缠于对参与者文本字里行间歧义的解释,忽略了他们在论争背后的“策略”运用,特别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对话语权争夺的意图。其实丁文江与张君劢展开“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其真正目的除了表达他们各自的观点外,是否还另有所图?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在政治上,丁、张同属梁启超的研究系,均认梁氏为师。在人际关系上,他们亦构成一个圈子。陈伯庄称他认识丁文江、张东荪、蒋百里、徐新六、林长民诸人,都是通过张君劢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小圈子。梁氏在五四运动以后,其影响
力日益下降,在舆论界已不占主流。因而争夺话语权,成为他及其追随者迫不及待的目标,时人对此已有警觉。据曾在1920年为罗素来华讲学担任翻译的赵元任回忆:“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讲,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作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作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做译员看待。”即是一例。研究系从文化迂回到政治,以图再振,这是其新的策略,时人对此已明察秋毫:“五四运动以后。研究系三字大为一般人士所注目,盖彼暂舍目前政权之直接争夺,而努力文化运动,谋植将来竞争之稳固地盘者也。虽其文化运动之主张,系出一种取巧之政略,而非诚心觉悟忏悔,作基本工夫,以图根本上之改造。然视同时国中各政党,固步自封,仍守因袭传统之党纲,不知顺应世界新潮为进止者,似稍差强人意耳。三年以来,多方进行,颇具成绩,青年学生彼罗致者亦不乏其人,其潜势力之继长增高,未有艾也。”炒作“科学与人生观”的话题,显然另有一番用心,即是将舆论重心转移到他们这边来。从丁文江在《努力周报》第48、49号上发表回应文章《玄学与科学》后,《努力周报》继而在第50、51号破例安排张君劢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再由胡适、梁启超分别领头撰文出面助战,《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两报组织辩论,最后由深具研究系背景的《晨报副镌》转载发表在《努力周报》和《时事新报·学灯》两刊的文字,这里似乎蕴含着某种“策略的安排”。当张、丁拉开论战的序幕时,梁启超第一个站出来极力鼓动大家参与这场论战:“我的挚友丁在君、张君劢因对于人生观的观察点不同,惹起科学玄学问题的论战,现在已开始交锋。听说还有好几位学者都要陆续加入战团。这些人都是我最敬爱的朋友。我自己现在是暂时取‘局外中立的态度,但不久也许‘参战,最少亦想自告奋勇充当‘公断人。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庆幸的现象。两军主将都是我们耳鬓厮磨的老友,我们尤感觉莫大光荣。我很盼望这回论战能为彻底的讨论,把两造意见发挥尽致。而且希望参战人愈多愈好。”梁启超如此高调,并“拟出两条‘战时国际公法先行露布”,为论战制订基本的规则。论战进入高潮,张、丁已尽显各自基本意见,梁启超又发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明确论战的主题,对张、丁的意见加以评点、修订,划分壁垒,居中调和,貌似公允,明显表现出推导、操控论战的企图。有意思的是,当科学派的声势渐渐压倒玄学派时,7月19、20日《时事新报·学灯》最后刊出王平陵的《“科哲之战”的尾声》一文,发出鸣金收兵的信号。只是因为范寿康在《学艺》发表《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一文,波澜再起,引发了《努力周报》(第72号)刊出唐钺的最后一篇回应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这场论战似乎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收场。
《努力周报》与《时事新报·学灯》分别在北京、上海发刊,它们的对阵,自然对南北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有的论者喜以在论战中丁仍请张吃饭,或张在文字中仍称丁为“吾友”来说明张、丁二人互相容忍的雅量,其实我们倒不如看看丁文江私下给章鸿钊的信:“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弟与君劢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战,纯粹为真理起见,初无丝毫意见,亦深望同人加入讨论。”将自己与张“交情甚深”的内情向章鸿钊交底。当然,把丁文江出来挑战张君劢,解释为双方一种预谋的类似新文化运动初期刘半农、钱玄同导演的“双簧戏”,这也过于牵强。但丁、张双方不因辩论而交恶,反而相互“唱和”,“亦深望同加入讨论”,或如梁启超所示:“我两位老友(指张君劢、丁文江——作者注)以及其他参战人观战把我的批评给我一个心折的反驳,我是最欢迎的。”则表示了他们对一场“恶战”的期待。此前,丁文江曾就“裁兵计划”,与蒋百里互相抬杠、辩论,但并没有引起舆论界足够的注意。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们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国民党人(如吴稚晖)、无党派人士(如胡适)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加入这场论争,虽然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大体不离为丁、张二人助战的姿态。丁、张二人之主将地位赫然彰显,一时占住了舆论中心的地位,他们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时代的重心毕竟发生了转移,文化问题正退居其次,政治问题已推到台前。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国、共携手合作,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管是曾进入北洋政府核心决策圈的梁启超也罢,还是未能在北洋政府获得高位的丁文江、张君劢也好,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这次努力终究无助于挽回他们在政治上边缘化的颓势。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持续了约一年多时间,它使丁文江本人的名声,远远超出了地质学界,成为海内外知识界人人知晓的公共性人物。傅斯年说:“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论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钱缪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罗家伦亦说:“民国十一二年问国内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我在美国才看到好几篇他的文章,虽然他的论点大体是根据德国的马赫(Ernest Mach)和英国的皮尔生(Karl Person)的学说,可是他思想的清晰,笔锋的犀利,字句的谨严,颇有所向无敌之概。”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正酣之时,傅斯年尚在英国,罗家伦身在美国,他俩的回忆证明,丁文江当时的论战文字,已经不为国界所限,远播海外,引起了远在大西洋两岸的欧美留学生的注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丁文江实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者。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