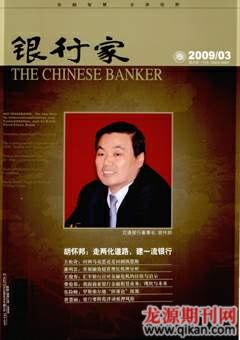美国之行散记
王青石
今年寒假,我跟随“STS”(STUDENT TRAVEL SCHOOL FOUNDATION)组织的游学团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美国。身已至此,写一篇加长版游记。
附:行前小小记
行前那一段时间我像是梦游过去的。我爸一时食欲大开啃了个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猪蹄,不知怎的就闹了个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我无辜的母亲只好陪在那里,于是一女名曰多兰受我爸诏令来照看我那几天的生活,每天日程犹如电脑程序:做托福的阅读理解题、上薛老师的数学课然后上床睡觉,犹如行尸走肉。现在,我连那个叫多兰的人长啥模样都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唯一比较清晰的一段记忆是农历小年的那一天晚上多兰带我去了我爸病房,大家一起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年饭,出发前最后一天多兰先跑掉了,我妈从医院回来陪我收拾行李,然后送我到机场,时间是2009年1月20日,之后便又不省人事了。
来到美国
说不清是一天还是两天,反正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终于折腾到了美国,全程本来计划要疯狂地赶写寒假作业,但是由于光线过暗等等原因,便没了坚定的意志,只好闷头睡去。
时差是一种很烦人的东西,我们的飞机貌似在逆着时间飞行,一会儿天亮一会儿天黑,让我的大脑很是受刺激,便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熬过了漫长的一夜,或者是漫长的一天,不管他了。



其实整个飞行过程中我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却也不觉得困,大概是飞机上一如既往美味的饭菜带来的某种生理上的力量吧。我们的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飞机不是直达的,需要在纽约机场转机。纽约机场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黑色白色黄色交织着,染得这个机场别具风味。
经过一道又一道看似没有意义的安检,我们一行人全身而保登上了飞往奥兰多的航班,班机上几乎没有人,机舱里安安静静的,只有众队友打游戏发出的按键声组成了一首没人欣赏的曲子。
突然想起来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个梦,整个梦都围绕着“飞越纽约”排演着一套伧俗的故事。如今真要飞越纽约了,心里杂乱如麻,不知该想啥。飞机起飞了,大概是由于人少,腾空而起的那一下冲劲格外地足,没用几秒就升到云端,我开始不自觉地认真俯视这座传说中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夜色中的纽约灯火通明,从高空看去,地面上犹如散落着一枚打碎了的巨大夜明珠,大片大片小巧玲珑的建筑群恰似发着辉光的碎屑,铺撒了大地,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天际还星星点点闪烁着光芒;这时一片云海飘入视线,在黑暗的作用下,就像一大片香醇的咖啡浸没了四野,把夜明珠的光都盖了过去,又像一片绝望的荒漠,叙述着致命的诱惑与沧桑的白骨;伴随消逝着的夜明珠的翠绿翠黄的光影,一股睡意扑面袭来,渐渐便没了意识。
再次醒来,脑壳里的内容已灰烟散尽,昏昏沉沉稀里糊涂地走进了美国的接待家庭,这是栋二层楼的“HOUSE”(在北京我们通常称“别墅”), 当时时针已指向当地时间的凌晨两点,所以也没来得及仔细观察,直接就上床睡去。
艾伦
第二天,我们认识了这位负责我们全部课程、行程的半老太太(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艾伦,艾伦很友善,对所有人都非常好,而且也懂得怎样与我们相处,没用几天时间就与大家打成了一团。 从艾伦的举止看,她似乎不属于那种气质高雅型的什么什么夫人,尤其是大笑起来“哇嘿嘿嘿”的动静甚是夸张,几乎可以用“狂笑”一词来形容,但接触过后发现在她的粗犷里其实透着智慧与宽容博爱,当有人犯了错误,她会怒目而视却口出平和之言,捋清道理头头是道极具说服力,还口口不失“我爱你”以及“将来不要忘记我哦”之类肉麻的言语。或许有一天我会忘了她,不过我不希望如此。
对于艾伦,我真的想说很多,然而下笔却又不知该怎么说;我很欣赏她,但却想不出来任何伟大的实例,只觉得她关爱所有人于无影无形,她将光芒散发于无时无刻,近似神却就在我们身边。疑惑之时,我突然想起艾伦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不自觉地朝天上看了一眼,上帝在哪里?没人看得见,不过我们所知道的是:上帝的眼睛无处不在,随时准备帮助善良的人,随时准备感化愚鲁的人,随时准备惩罚邪恶的人,如何实现?上帝将这一切行为寄托在每一个人身上,用芸芸众生之手解决芸芸众生之忧,你不信吗?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亲眼看见一切。
餐饮文化
众所周知,很多年轻的中国人都喜西餐,于是便有了不少“将来到国外去一定会吃得很香”这种念头。然而,大错特错。此行前我一直也持这种观点,虽然曾经出去过很多回,但要么是随旅行团吃国外的中餐,要么是吃自己用国外材料煮制的中餐。这次到奥兰多,三周时间都吃住在地地道道的美利坚接待家庭,那一日三餐的平常饭菜让我头一次真正彻透地了解了所谓的西餐:真正的西餐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美味佳肴。
以家喻户晓的汉堡举例,中国人习惯用火腿片以及炸鸡来填充汉堡面包,渐渐地,汉堡一词语在中国的概念便成了“面包夹各种味道的鸡柳”或者“面包夹火腿”。然而,在汉堡的发源地——美利坚,这种面包夹肉制品实际上只选用加过香料的、多汁的大块牛肉馅作为中间的核心部分,经常会加一片奶酪以增加香醇程度,听起来你或许已经馋涎欲滴了,但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吃不惯,主要是因为那牛肉层虽厚,但食之无味,所谓汁多,实为水也。然如此之大肉,弃之可惜,难下咽也得下咽。再想起那些我吃饭时坐在餐桌对面的金发男女对此“佳肴”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吃得很香的样子,我捧着当下手中的肉夹馍,也胡啃一番开来。
那些在中国名声响亮的西餐快餐企业,像必胜客、棒约翰、赛百味,包括很早就登陆的肯德基与麦当劳在美国国内都是质量与味道一流的优质企业,这也是它们能成功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们的产品并不代表着西餐快餐的平均质量或味道,它们是西餐、快餐中的精品,所以才会导致中国那么多人尤其是儿童和年轻人对西餐、快餐产生认识上的误区。
宠物
我之所以写上貌似无关紧要的宠物这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家庭发生的一件事。
我还记得那是个周末的早上,我们刚吃完简单的早饭,正准备回屋歇息,突然听见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大声惊呼的声音,都以为出什么大事了,我刚准备返身去一看究竟,只听得第二通大喊:“天哪!鱼死了!”家庭成员们火速赶往现场。我心想:我在中国的家里养那么多鱼,早就习惯死鱼了,但也不能摆出典型外人的样子置之不理吧,便顺着刚才准备返身的力道假装焦急地快走了过去。
眼前是一家人在鱼缸前哀悼的场景,口中念念有词,那鱼溃烂的身体还在冒着气泡,与我们家水族箱的鱼的死相同样惨。这时,云戏剧性地遮住太阳,屋中霎时黯淡下来,为哀悼巧妙地制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这一时刻,我突然再度想起我们家的鱼。
我们家水族箱的鱼死得很频繁,每次死后家人顶多说几句类似“这鱼不好养”或者“下次不买这种了”的话,哪里来什么哀悼!就有一次稍微特殊点的,那次养的青蛙饿死了,尸体被群鱼贪婪地瓜分了,只剩一副血淋淋的皮拖着半透明的黑色肠子漂在水面上,我母亲来了一句:“你看那尸体跟个人尸一样,骇死人了,以后再也不要养青蛙了。”想到这里,我愈发惭愧。
同样是生命,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却是明显的不尊重。有人会说,人命多值钱呀,那他能指出鱼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有何区别吗?同样被大自然抚养,死了迟早要去同一个地方,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人类或许聪明,是最高级的动物,但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凭此凌驾在其他生命上头?我们或许可以主宰这个各种生灵肉体共存的星球,但我们永远主宰不了所有灵魂同在的世界。因为生存在地球上的我们有大脑,有思维,而在另一极的空间里我们所有灵魂都无非是一抹虚幻的气体,或是一把松散的土灰。在美国,名义上的宠物大多都是实质上的朋友、亲人,而在中国,则大不同;以狗这种生灵来说,大多数美国人是绝对当狗作最亲近的朋友,视他们为家庭成员之一,有时甚至是生死之交;而在中国,大家口头上也到处说狗是人类的朋友,但真实的情形是表面当朋友,心里作玩物,骨子里从来不曾有平等对待的态度,他们说狗不理解人的很多东西,它们自然永远是比人下贱的,难道人就真正懂得狗的需要吗?爱心是个啥?爱心不是整天东拉西扯一些貌似高深的虚幻口号,爱心是真正的尊重,对大自然和生灵的尊重。
迪士尼与海洋世界
曾经有一次辞了学校的课程去了趟香港,为的就是在人少的时候去一趟迪士尼乐园与海洋馆公园,转完了这两个大公园后我明确表了态:“迪士尼很小很无聊很拥挤,海洋公园很大很好玩很让人流连忘返。”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遥远的美国有一个大得难以想象的迪士尼,那里有太多太多美妙的的事情可以做,数不胜数的娱乐项目、使人受益匪浅的迪士尼历史纪录片以及数以百计的动画。从那时起,我对这又一个迪士尼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兴趣慢慢消退。
今天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个曾经无比憧憬的地方——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总部,也叫华特迪斯尼世界。梦与希望之旅再度启程。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也有一个海洋世界,并且在我们的行程中两个大型乐园都安排了游览的时间,这次又有的写了。
先去了迪士尼,到达了那里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个迪士尼与香港迪士尼的结构完全一样,各种游乐区的分布完全吻合,只不过占地面积是香港那个巴掌大的迪士尼的N倍,游乐项目的数量也远远要超出香港迪斯尼的那个可怜的数字。另一个相当有趣的事实是:这里排队同样要用上很长时间,不过与香港迪斯尼的区别却非常明显:奥兰多迪斯尼的各个项目的等候牌上一般不会出现大于六十分钟的数目,并且实际等待时间通常比牌子上标明时间少去二十分钟左右,而在香港则通常是要等数个小时才能玩一个不到五分钟的项目。这便是差距。
在迪士尼游玩的那一天我其实并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老师出于职业责任心强调我们分成小组集体行动,而在这次来的人群中我又找不到什么志同道合的知心人士,便随便跟了一组开始进行伟大的“集体行动”。与我一个小组的人还都心智不算成熟,当然我知道我也没必要以此说明我有多成熟,不过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此类经验。要知道,偶尔排个长队都不愿意的一群人在这里是玩不到任何好东西的,我尊敬的队友们以“耗时最少为佳,质量不管高低”的理念在这个地方慢慢在众多值得一试的项目中“精挑细选”磨蹭过了一天。不过晚上全体观看的迪士尼卡通巡演还不错,霓虹铺满大地,烟火纵横天际,震山响的音乐不断地把气氛推向最高潮,所有怀着一颗童心的人在迪士尼人物的笑声中欢聚一堂,正如我珍贵的迪士尼门票上所印刷的:“这是一个夜晚如白天一样明亮的天堂。”
至于海洋世界,与香港的那个地儿倒是截然不同,香港的海洋乐园认为海洋公园的意义就在于看鱼,开眼界,而奥兰多海洋世界则认为教育第一,让游客了解他们所看到的各种神奇的生物,因而自然也就没有设立那么多分门别类的观赏馆,多的是教育性的设施。当然,此二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谁好谁坏之分,各有千秋而已。
如果让我拿这次的海洋世界比迪士尼,我想还是海洋世界胜出了。
迪士尼败局已定?
迪士尼的压轴戏终于出场,最后两天里,我们又去了另一个属于迪士尼的大型乐园,这次我才真开了眼界:谁说迪士尼没戏?这个地方按照国家进行分区,每个国家的区域主要介绍该国的文化,同时销售该国的代表产品,所有的知识传授全部是在娱乐当中进行的。令我印象最深刻是他们用独具匠心的手法将中国文化活灵活现地体现了出来,一个装扮成李白的人身为导游带领众外国人行走在亭台楼阁之间,生动地讲述关于中国的传说,从长城的建筑史到现代化的北京、上海、香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时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中国。真是不自觉地想要叫好。
然后,在我评判中,迪士尼由此战胜了海洋世界。
黑人
受到很多电影以及朋友家人的口述的影响,在我眼中的美国黑人形象一直要么是一群戴各种象征着死亡的首饰、刺青全身、长着痞子气浓厚的长发或胡子、成天吸毒成瘾、拉帮结派到处斗殴的街头无赖,要么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人,整天可怜巴巴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但是这一次亲临美利坚,发现那其实是好莱坞反映给世界的假象,真正的黑人就在身边,无处不在,然而他们似乎又存在于无有之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黑、白、黄在这个国度不再是令人诧异的肤色,似乎没有那个美国人还在刻意地以肤色来区分身边的人们,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不存在任何种族问题,蓝眼睛望着绿眼睛,绿眼睛望着黑眼睛,黑眼睛望着蓝眼睛,目光在街道上的每一个角落里交汇,人人平等的国度充满欢笑
在迪士尼购物街上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很难忘的黑人,当时我正坐在街旁的长椅上吃冰淇凌,旁边便是那个黑人和他的白人同事在孩童密布的大街上发贴画,他的身上没有任何首饰、纹身,也没有着奇装异服,平平的板寸头在被孩童甜笑声充满的风中若隐若现,每当有孩子走来的时候,他都会露出发自心底的慈爱的笑容迎上去送一打贴画,不时地还与家长们谈笑几句;没有孩子过来的时候他便独自靠在他的小亭子旁会心、温暖地微笑着,看着男男女女来来往往,目光中透着宁静和善良,忘我的神态犹如望月独酌的诗仙陶醉于丝绸般细腻柔软的光中,不远处是米老鼠经典的快乐形象,和睦的气息钻到每一个晦暗的边缘,圣洁的美好填充了每一个瞬间。
突然,一道雷光划过大脑,我惊觉——犯了一个大错,愚蠢的我把这个黑人当成了一个异类,我把他看成了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