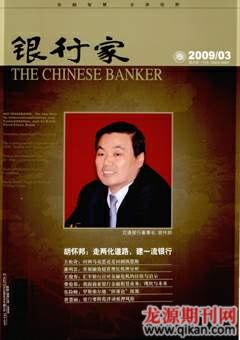给灵魂以滋养
朱 琳
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化小城焦煤镇的一间教室里,小镇的头面人物葛雷梗先生正以坚定的口吻阐明教育的原则:“除了事实,其他什么都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掉。要训练有理性的动物的头脑,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这就是我教养我自己的孩子们所根据的原则,这也就是我用来教养这些孩子的原则。要抓紧事实不放,老师!”
这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开头的一段。小说的主线是退休富商、国会议员葛雷梗的家庭和社会活动。葛雷梗是理性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虔诚信奉者,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 他衡量一切人和事物的标准是尺子、天枰与乘法表。正如他以上所言,不管是教育子女,还是在镇上办学,他的教育宗旨就是向学生灌输“事实”,要连根拔除一切不是“事实”的东西:幻想、感情、信念、娱乐、个性。他的孩子们没有童年,从小学各种学问,从没有读过童话歌谣,从不许有情感和想象力。他磨掉了孩子的天性,剥夺了他们的欢乐,扼杀了他们的情感,毁掉了他们的生活。他的一双儿女在如此教法中长大,失去了健全的人性和天然的情趣,女儿成了一场只有经济利益考量的婚姻的牺牲品,儿子堕落为极端自私的罪犯。
这部小说创作于19世纪中期,边沁功利主义和曼彻斯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正流行于英国。狄更斯对其中所包含的把人视为经济的动物、赚钱的机器的看法大为反感。他谈到自己的写作意图:“我的讽刺是针对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的,是针对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代表人物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对劳资矛盾的反映,也是从探讨作为工业制度核心的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摧残这一角度进行的,为被资本家看作没有情感和灵魂的劳力的工人们呼吁人道待遇。
方方正正、如石头般坚硬的葛雷梗是用漫画手法塑造的,令人忍俊不禁,但是这个人物只在这部小说或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吗?今天,在我们身边,难道我们没有感到不那么夸张、却深得葛雷梗神韵的人的存在吗?把人只看做经济动物的想法不正大行其道吗?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我们贯彻的不正是这样一种“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原则吗?
笔者任教于京城一所颇有声名的财经类大学,教的却是校方不疼、学生不爱的非主流的公共课——语文。放寒假前,各院系开始新一轮教学计划调整,我们也就又开始新一轮的保课努力。院系每每要削减大学语文课的课时甚至要将这棵树连根伐去,理由是这门以文学欣赏为主的课程实用性不强。而我们就得竭力证明这门课是多么多么地有用:您看,我们的身边不是充满抱怨吗?现在的学生不会写毕业论文,甚至不会写申请书、启事、求职信等日常应用文。写作中文理不通、词不达意、语言贫乏、错字连篇、胡乱标点等问题很普遍。学生基本的语文能力有欠缺,会制约他们的专业发展。于是有人首肯,认为上语文课还是必要的,但应该重点教写作技法,希望理性的、显性的、功用性的工具性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能对解决学生毕业论文、求职文书写作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写作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语文课中那些感性的、隐性的、非功用性的部分仍被认为是多余的,那丰富的文学文本带给人们的心灵颤栗、思想影响、情感熏染是多余的。它们无助于通过中外的名目繁多的各类考试,无助于拿证,无助于就业。我们承认,人首先需要解决生存问题,不能否认现实问题的直接性和迫切性;但是,教育的目的就是就业吗,学习的目的就是考试吗,“有用”就能穷尽人生的所有价值吗?我们不是总说大学教育的目标不是“制器”而是“造人”吗?人是什么?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阶段,人被高声赞美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为何?因为人不仅是生物性的生命存在,人还是万物中唯一有灵性的精神存在,有丰富无垠、复杂无比的精神生活。随着文明的进程,人类精神需求的地位逐步提高。人类精神生活关注的中心是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人生在世需要知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需要赋予生命以意义,如尼采所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托尔斯泰坐拥人们向往的一切:财富、地位、名声,但他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一生都在经受寻找生存意义的灵魂折磨,以至耄耋之年离家出走。心灵有皈依,可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对于人为何而活、如何为人等终极问题的不断追问、探询和践行本身便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若只随肉身的欲望而活,失却灵魂,人就是酒囊饭袋,如行尸走肉,世界不过是了无生趣的囚牢。拥有灵魂,拥有心灵超越精神和终极关怀情怀,人生才因此而具有神性的光芒。人的肉身需要物质的不断供给得以生存,灵魂亦需要精神食粮的滋养而丰盈、充实。正处在精神成人期的学生们内心充满人文渴求,需要人类创造的优秀精神资源的营养。其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佳作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是人类精神培育的奇葩、创造的精华,以对人生的审美反映,提供了人诗意地栖息于大地的景观。读者在文学欣赏中突破时空局限,感知、体验丰富生动的人生百态(尤其是心灵和情感方面),感受到获取理性知识时难以体味到的美感、快感。文学展现了人生的大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打破我们对生活虚妄的幻想;文学又用价值之光穿越人生的黑暗,表现出心灵对苦难的超越。文学虽不能直接地解决人们生存的现实问题,却能够作用于人的灵魂,净化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心智,滋养我们的情感,参与人格的构成。
课堂里的学生们不仅需要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的经济、法律知识的灌输、实用技能的训练,需要政治教诲和心理调节,他们还需要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等不那么务实的人文教化。我们恳切地呼吁:留一些课时给文学欣赏吧!让师生们在一起读点文学,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谈点玄,说些虚,论论剧情,品品诗美。文学不是生活指南书,在生活中亦步亦趋地按文学作品行事,只会闹出堂吉诃德式的笑话或是酿成包法利夫人式的悲剧。但是,文学作为对人生情境的审美提炼,与现实人生有距离却决不脱离。生活中马加爵这样的悲剧会让我们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不妨读一读这本书,窥见一个濒临绝境、铤而走险的大学生的精神深处,看见人如何在苦难中寻求灵魂拯救的艰难历程。当现实中一个又一个学生轻而易举地向自己的老师或同学挥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是什么让这把复仇之剑迟迟不能痛快地落下?当社会把“成功”定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时,我们可以读读司汤达的《红与黑》,看看这个沉迷于“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最后如何参悟人生的真正价值。艺术摹仿人生,也供人生摹仿。优秀的文学作品引领人们超越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获得精神的自由,又帮助人重返现实世界,以更高的精神境界去重塑现实世界,提升个人人生以及整个社会生存的质量。正如歌德所言:“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
回到《艰难时世》,在品尝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后,葛雷梗原有的信念遭到沉重的打击,在出身于充满想象和诗意的马戏团的、作为情感化身的女孩西丝的感化下,他意识到并非“光有头脑就足够了”,还应有“心的智慧”,决意要“拿他的事实和数字服务于信心、希望与仁爱”。在工业化的滚滚浪潮中,作者希冀爱和情感能够战胜冷酷的机器。
小说的结尾,已成为母亲的西丝教给孩子们故事、歌谣,“想法子用种种想象的优美和快乐来美化他们机械的现实生活;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们的心灵就会干枯,长大成人也就会同行尸走肉差不多,如果不去陶冶天真,培养性情,即使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一个国家是多么富足,但归根结底这还是大祸将临的预兆。”
让我们也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学生,把他们当作有灵性的人而不是只需懂经济的理性动物看待,少一点急功近利,留点时间和空间给那些“无用”的东西,给年轻一代灵魂以滋养。如果我们失去了灵魂,即使得到整个世界,那又有何益?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