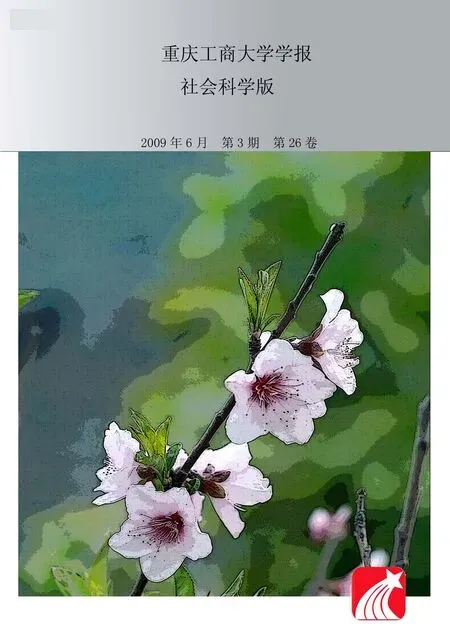现实与浪漫,肯定与否定
——论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观*
何劲虹
(四川外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重庆400031)
一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是英国著名小说作家,他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895年到1910年为第一个时期,其间的成就是,怀疑论者的康纳德刻画了被骗误入了道德深渊的孤独人物,他们既遭到毁灭,却又以为人类团结做出奉献的禁欲主义的面目出现。第二个时期始于1910年,当时在创作完《在西方的眼睛下》之后,康纳德遭受了失败的打击。除了《阴影线》(1917)外,他后期的小说缺少早期的怀疑主义与质朴无华的风格,其作品充满了感伤和浪漫的情调,其中,在女强人的感召下,胆小的主人公的故事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认为康拉德小说中这种变化是一种“衰退”,这些小说都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衰退的关键是女人——尤其是恋爱中的女人。还有人认为,康拉德写女人很难(如《姐妹》和《营救》),他不能把情感戏剧化,性爱的主题是他的禁区。他不可能写爱情,因为他的确“不相信”爱情。“对康拉德否定爱情的看法我们不必感到诧异、震惊或厌恶。从其他方面来看,康拉德认为,人精神上孤独,受到利己主义的权力和平静的折磨,蹒跚在危险的路上,他唯一的希望,是使其精神麻木,很少有自知之明。康拉德不可能使如此含糊不清的看法等同于,有人相信爱情、妻子、家庭能包治百病的观点。”[1](P127)在他最后7部作品中,有6部写到女人和爱情,他不可避免会失败,因为他“在性爱的面前”一定会陷入“创作的困惑”。
康拉德艺术构思的真正意图是把动摇不定的主人公置于女强人的魅力控制下。有人认为,康拉德后期的作品,缺乏早期作品的才能和复杂的道德情感。他们没有从艺术上去看问题。康拉德不断地写爱情主题,不仅仅表现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如迈耶指出的康拉德32篇小说中有25篇的主人公在情感上同女人纠缠不清。康拉德作品晦涩难懂又不受人欢迎,因此《机遇》和《胜利》中表现出对女性爱的情趣,是读者所期望认可的。他后期的作品销售走好,这也证明了他的创作满足了读者的愿望。学者多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康拉德为何认为女性对男性“着迷”的原因。迈耶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结合康拉德的人生经历,仔细分析了康拉德潜意识对女人的态度。根据迈耶的分析,康拉德实际上是个厌恶婚姻者,他作品中的女人毁掉了男人,而且康拉德的创作艺术衰退,是由于他1910年的精神崩溃所引起的。这种崩溃使他对厌恶婚姻全然失控,他写的一系列作品描绘了“生殖器崇拜的女性”,毁掉“被阉割的男人”。
有评论家认为,康拉德害怕女人。在他看来,她们与死亡和毁灭有关,这可解释他极度关注的男主人公在女强人面前,丧失了男子气概。再如他写女人时,陷入含糊不清、似梦似幻、感伤的状态,因为他“这时只可能把他的性恐惧隐藏起来”。[2](P163)
以上这些观点极为有趣,但是它们与康拉德的写作动机无涉,尽管他写了女强人对想象中和潜在的男主人公的影响。康拉德坚持认为:“我作品中的明确意图有坚实的基础,而且创作是理智的活动,是在对效果经过深思熟虑后指导下进行的。”[3](P284)重要的,不是根据作者的心理条件而是根据他文本所揭示的深刻内涵来解释康拉德的爱情主题。康拉德要读者认真考虑“理想主张”,即超验主义真实的可能。爱默生认为,超验主义是“人的灵魂对以终极真理形式存在的道德情操的追求,而道德情操的至高境界,应当向人的内心去求索,不假于心外的任何东西”。[4](P293)康拉德体现了定型女性人物的这种可能性;他要读者同样认真地考虑这种可能性,即这个世界没有更崇高的意义,一切的理想主张皆系幻想。而这种可能性,在他的男性人物的命运中已丧失殆尽;因而,康拉德的小说是含糊不清的,尚未揭示理想是否是幻想或是更高层面上的真理,因为“探索真理就要对它有追求和热爱,认识真理就要和它形影不离,相信真理就要为它有享受的乐趣”[5](P5);康拉德早期作品如是,其后期作品亦同。
二
《胜利》(1915)虽然受到有些人的否定,但与后期其他作品相比起,更受读者青睐,因为有评论家认为《胜利》是他的成功之作,视之为康拉德1910年之后有关女性衰退的代表。莉娜为了手无寸铁的英雄阿克塞尔·海斯特献出了自己生命,对她的描写可以看成康拉德失控的典型。这明确地表达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莉娜的能耐,通常可按她对海斯特的爱、热情的本性、女子气质来解释。她想“证明她对海斯特的爱”,从而帮助他认识“他在人性舞台上所有的积极作用”。她是生活中的一位代表,她从激情和智慧赢得了胜利,也许胜利是虚幻的,但战胜了海斯特的离去。
不过,文本赋予莉娜性格更崇高的意义。她在小说的作用是象征性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读者觉得她是定型的,似乎康拉德更加关心的是使她“具有的意义”,而不是使她“成为什么样的人”。莉娜将美、神圣的爱和不朽的生命带入了康拉德的世界。这种精神,在康拉德的早期小说中,可以说是柏拉图式的,即纯精神而无肉欲的爱情,当然也有例外。
康拉德运用大量传统的写作手法,来强调莉娜的精神性格。例如,她反复被描写成为魔鬼、幽灵、“白色鬼怪似的神奇现象”;海斯特在雄贝格饭店外碰见她时,她是“白色鬼怪似的……像魔鬼的恳求,从黑色阴影中,向他伸出她的双臂”。在整个小说中,她一直穿着白色衣服,直到小说结束,海斯特才让她穿上黑色衣服,最后同邪恶会面。因为她进入世俗的领域,颜色的改变也许是适当的。不管康拉德如何暗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是,白色仍是用来传递她的清白。如康拉德所描绘的“梦幻中的清白形象”,莉娜的精神本质,也是由她那不可思议的声音来暗示的。她的声音,“暗示对智慧和感情无限的深切”,那特殊的力量感动了海斯特,因为他生活在安静中。肯定无疑,这声音是莉娜无形的显现,像目睹者、小孩似的清白,这声音是一种传统的象征,这种象征手法起到了“把象征作为服从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意念”[6](P45),它进一步证实,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个精神上的人。
康拉德时常暗示,莉娜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同时也是一种梦幻,或一种理念。海斯特看来,她的拥抱“可能有一种梦幻般非实在的感觉,侵袭苏醒生命的现实;是他思想荒芜的贫瘠中迷人的海市蜃楼”。
康拉德的人物刻画、意象和记叙角度都有独到之处。莉娜是精神的代表,她闯入了海斯特无神、无爱、无意义的世界,且提供了超验爱情及欢乐的可能性。然而,康拉德却努力让人们不要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人物。他暗示莉娜的灵性误解了海斯特的情感。荣格说:“‘感情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未完成的思想’——这是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定义。然而,感情却是一种有名有实的东西,一种真实的东西,它是一种功能,我们有命名它的专门的词语。”[7](P11)一些场合中,好像她幼稚而笃信宗教;在另外平静的场合中,莉娜是必然出现的精神本质,康拉德决心把莉娜描绘成既体现超验理想而又有血肉之躯的女人。
《胜利》中的释义的多样性,在不相容的极端之间,达到了不稳定的平衡,这一直是小说家长期所追求的。《胜利》中的莉娜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康拉德旨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所在,毕竟,康拉德是创作了许多小说的大作家。在小说中,崇高的理想,比如,克尔兹把光明带进黑暗的心灵,吉姆爷英勇行动的愿望,或查尔斯·古尔德要把科斯塔古纳从物质利益中解脱出来的决心,既可笑,又有点危险。这个世界太专横,容不得有这样的幻想,而康拉德对待人的欲望用无情的讽刺超越它。
康拉德想要让人们在信仰与虚无之间、在奉献与超然之间、在看法与睁眼所见的现实之间去思考。潜意识的动机促使像康拉德这样天才的讽刺家去写感伤的作品。毋庸置疑,康拉德后期的小说多种多样的。他总是想写好一个女人,她似乎要给她崇拜的男人开辟一个新的精神领域。这并不是说,康拉德一遍又一遍重复地讲同一个故事,或他的人物是雷同的。比如,莉娜、弗洛拉·德巴拉尔和伊迪丝·特拉弗斯,她们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女人:莉娜经历了痛苦和爱情之后感悟了;弗洛拉缺乏生活经验,且受到自相矛盾忠诚的折磨;特拉弗斯夫人精神抑郁又娇生惯养。她们的追求、她们的痛苦,以及她们的精神几乎是不同的,但是,从象征意义上看,她们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都把精神领域的东西带进了具有远大理想的男人的生活中。
在《机遇》中,安东尼船长出于对女人的爱而搭救弗洛拉·德巴拉尔,这个故事是由一个玩世不恭反女性主义者马洛来讲述的,他时常嘲笑女性的感伤情绪,以及她们的“陈腐的幻想”,“可没有这种幻想,男人照样活下去”。弗洛拉是一个好幻想的姑娘,性格单纯、皮肤白皙、像孩子一样天真,寻求“摆脱世俗的”道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可是,在人世间,没有她清白的立足之地”。当然,她也生活在人世间。她的家庭责任感,她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她的性生活,这些有助于她对社会的认识。她被安东尼所救,而安东尼把她理想化了。像莉娜一样,弗洛拉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她帮助鲍威尔在暴风雨中点亮了照明灯;如海斯特,安东尼自己面对邪恶势力表现得很脆弱,决心按理想化和感伤的行动办事。
康拉德再一次表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模糊的,互不相融的。他通过马洛对弗洛拉和安东尼船长的观察来加以表现。《胜利》中的困境在《机遇》中也表现出来:一方面,男人通过女人所感受到的超验领域,是一种感伤的幻想,而幻想留给人们的是,在一个残酷的人世间,人们毫无抵抗能力;另一方面,精神上的种种愿望,则是鼓舞男人去行动的唯一的力量,化成残酷而英勇的行为。
与《胜利》不同,《机遇》以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对未来愉快的承诺结尾,模棱两可的意义或多或少削弱了。鲍威尔是个稳健又实事求是的人,他没有像安东尼船长那样将弗洛拉精神化,大概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弗洛拉理想的意义是安东尼唯一的幻想。当然,《机遇》所提供的,是那种可能性,可它也以那种可能性来哄骗读者而已,弗洛拉所体现的理想存在于安东尼船长烦恼的心情之外。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次表现在《营救》(1920)中。汤姆·林加德是个性格坚强有能耐的人,勇敢营救处于困难中的人,可是,他在“他自己内心朦胧冲动面前似小孩那样毫无自卫能力”。如海斯特,他的英勇品质命中注定使自己卷入生活的浪潮中;又像海斯特,他手无寸铁地面对最后的斗争。他简直就是个充满无穷幻想的人。
然而,伊迪丝·特拉弗斯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势力;她是个令人讨厌的上流社会女人,同时她又代表男人生命中精神上潜在的东西。康拉德应用大家熟悉的技巧,把她描绘成社会的牺牲品,她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聪明伶俐,而且她的声音充满魅力。从象征层面上讲,她坚持认为世界应保持平衡,且希望为理想而献身。
伊迪丝与林加德邂逅,使她的意志更坚强,决心冒死亡之危险去维护林加德的安全。她心里非常清楚,她的任务就是去拯救林加德。在林加德的眼中,她是“不可磨灭的,也许是不朽的”!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的双重作用使《营救》的背景有别于《胜利》或《机遇》,且不可能与超验和世俗的主张协调一致。
康拉德最后的作品《流浪者》(1923),也可以说,是一个爱情故事,然而,阿莱特在同里尔热恋时,康拉德将阿莱特刻画成本能上要求助于上帝的女人,而且她把他想象成“摆脱了同世俗的一切联系”。她带给他的是,“成功的生活感”,在康拉德看来,这是女人对男人习惯性的影响。也正是阿莱特鼓励老佩罗在英勇的自我牺牲中毁掉了自己。
这种种解释表明,对这种女性定型人物的描写,是康拉德作品的着力之处。除《阴影线》外,康拉德所有的后期小说,起到了表现主题的作用。这些小说确实把女人当成理想、真理及上帝的载体来加以描写,存在一定的粗陋和少有独创。实际上,后期小说的夸张,有助于理解早期微妙的作品。正是这种理念使康拉德着迷:超验真实的感觉才使生活有意义,且使男人渴望去为崇高的理想献身。这种精神上的感觉全是女性所具有的,因而女性必然对男性有这种看法,认为他们是人间戏剧的主角。极度含糊的生活是如此,因此这种看法,既能承受压力又有破坏性,既真实又具有幻想,既美又可笑。如1917年康拉德对悉尼·科尔文所说:“有人叫我海洋作家、热带作家、侦探小说家、传奇文学家,而且也叫我现实主义作家,不过,事实上,我一直关注的却是事物、事件,以及人的‘理想’价值。”[8](P35)爱德华·W·赛义德认为,正是一次世界大战使康拉德相信,比他早期作品,人世间的理想更多。战争本身使他心里想到的是,大变动的力量、可公认其自身的独立存在、开始及其结果。如今康拉德觉得宇宙的存在是充满活力并具有戏剧性。
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康拉德全部作品的重心所在。在《诺斯特若默》(1904)中,伊米莉亚·古尔德被描绘成孩子般的天真、仙女似的,她还同穿蓝长袍的马东纳有交往。她的精神本质,是她赋予事实以理想意义来加以表现的,无论这种种“事实”是银锭,还是重要的事件。她的丈夫尽管抛弃她,为的是通过物质利益而追求他对正义的信念。诺斯特若默临终时向她表白。她给男人的印象,甚至给蒙利格哈姆大夫的印象,是要鼓励他们成为勇敢的行动者。
安托尼亚·阿维拉罗斯也是在《诺斯特若默》中对马丁·德考德有类似的影响。因为有了她,“他才对幸福抱有很高的希望,到头来,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不能实现”。德考德懂得,这是“他行为感伤的基础”。但是,正是这种力量,激励着他把眼前的怀疑扔到一边,并参加了反对蒙特瑞斯特家族的斗争。
《吉姆爷》(1900)的真正意图,不是在苛刻禁欲的一个世界上,朱厄尔的爱情和吉姆的理想主义表现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超验的理想与残酷无情的环境之间的冲突,结果解决得不清楚又似尚未了结。《吉姆爷》中所潜藏的“柏拉图主义”超过了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在托尼·坦纳对甲虫和蝴蝶的意象精辟的分析中已得到确认。蝴蝶是“一种美丽的生物,一种有翅膀的生物能把自己带到高于地球的死亡平面上,而甲虫却紧贴于地球上”。无疑,甲虫是“丑陋、地球上爬的生物,没有尊严和抱负,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自己”。
这些意象暗示,康拉德其他多数小说的不可选择性,是他艺术构思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可选择性在《吉姆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性包括蝴蝶和甲虫在内,而且甲虫似的人比那特殊的个人生存得更好些,因为那个人践踏地球,还追求蝴蝶的超验美。坦纳叫做“马洛式不明确的柏拉图式的沉思”,让人们在蝴蝶和甲虫之间进行选择,在没有美的生存和短命的提升之间进行选择。小说中,理想的承诺是女人向男主人公提出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必须调整对康拉德已有的看法。批评集中到一点上,认为康拉德是忧郁的诗人,是叔本华哲学的代言人,叔本华哲学“试图对所谓形而上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作统一的说明,从而建立一个没有宗教的信仰”[9](P2)。他是对那些发现自己有背叛行为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进行讽刺的旁观者,因而,人们轻视那另一半相似的形象,可在这一形象中,康拉德竭力捕捉理想势不可挡的诱惑力。
总体上讲,“康拉德的创作兼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10](P525)。人们认为,康拉德努力使浪漫故事与现实主义协调起来,取得了他的独特效应,即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浪漫色彩的题材,从而展现现实性。厄恩斯特·本茨看清了,康拉德的浪漫主义中有一种“超验主义微妙的色彩”。可是,几乎唯有他持这一观点。其他人把浪漫故事同冒险、情节剧、青春、神秘、感伤、大自然、异国情调、魅力及悬念联系起来,而认为与“超验主义”无关。似如戴维·索伯恩评论的那样,实际上,浪漫主义要集中描绘平凡的世界,是“基本的必需品把人们互相连起来的一个去处,也是人们并未完全分开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分享类似的感情,怕死,想长期活下去,必要时会联合起来,且进行长期不断的劳动和斗争”[11](P146—147)。换言之,把康拉德坚持超验真实的可能,等同于影响他写海洋航行和遥远地方的冒险故事的浪漫主义,这是错误的。康纳德本人说过,“生活中的浪漫情感,主要存在于对过去迷人的冒险生活的回忆中,且源于不同人生历程和不同人物性格的社会关系中。”他的此种说法不存在“超验主义的色彩”。
三
对人的超验抱负,康拉德既肯定又否定。这“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是他小说的特点,也是他非小说的特点。可以察觉到,悲观的康拉德拒绝更高层面上的真实,这点,在他1898年给R.B.坎宁安一封信中能看出:“信仰是一种神话,而信念像薄雾在海岸上飘动;思想渐渐消失,话语,曾经说过,也会消失;而昨天的记忆,如同明天的希望一样,是朦胧的,唯有那一连串平常的话,好似没有终结。肯定的康拉德在1905年的一篇论文说:“不可想象的是,我需要小说艺术家道德上虚无主义的自由。从他那里,我想要多种的信仰,其中第一也许是珍惜一种永恒的希望;而且不容争辩的是,希望隐含着所有努力和克制自己的虔诚。”有人已意识到,他表达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并且已批评他尚未解决这两种观点。毫无疑问,隐藏在E.M.福斯特的看法背后的是朦胧,源于他拒绝解决“他远与近想象力之间脱节”,伊恩·瓦特的判断暗示,“康拉德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有野心,也许受到信念种种可能的异化不太深,想走出这死胡同。”这“死胡同”,事实上是一种人生观,它需要极其诚实和极大的勇气才能支撑住。敏感的人在生活中,为想象力和理智所苦恼,这种种苦恼的观点处于矛盾中,时而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中;然而,说一个人没有感觉到生活中含糊不清的负担,那么,他遂会认为并按照简单的肯定或虚无的世界观而行动,这种人的头脑并不十分清醒。
有人错误地认为:悲观的康拉德是在“早期”,而肯定的康拉德则是在“后期”。康拉德后期作品不是个“单纯而平静的”人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也不表示,“退出人性中的邪恶与善良和不可靠的理想相混杂的认识,这一认识是我们自己确立的”。假如康拉德后期的小说是低劣的艺术品的话,那么,那并非因为他对男人,或对女人,或对他们生活的看法在意义上有什么变化。不管他的艺术魅力怎样减退,可康拉德整个的人生观仍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对康拉德的批评,还不足以界定这一看法,或者证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表达它。需要的是对小说进行研究,来“认识相对立的观点的时效性”。人们可以分析,用康拉德在性欲定型人物中体现对立的观点来开始这种研究。
康拉德认为:男性的问题是存在主义哲学问题。存在主义宣称,“一切存在的出发点是个人存在,人通过自由选择来造就自己的本质,所以‘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在畏惧、焦虑、死亡状态中才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如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得不畏惧死亡,因为只有自由地死,才能赋予存在至上目标,要不就借助宗教和上帝的力量来抗拒畏惧。”[12](P315)正是男人对人性没有同情也许甚至敌视,以便找到了有意义的行动。康拉德的有些人物,如,《吉姆爷》中的布郎,《胜利》中的琼斯、理查多、佩德罗等,成了人世间的代理人,且参与了破坏过程。另一些人,则采取防卫的态度,简直是为了生存而挣扎,没有原则,没有抱负,没有计划。康拉德作品中,有几个男性人物忠实于一种准则,这种准则是在这困苦的人世间生活的一种手段,他们活得来令人感动。老辛格尔顿勇于驾船外出,麦克沃尔安然闯过了台风,他们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坚强男人的榜样。还有些人,像《特务》和《在西方的眼睛下》中荒唐的革命者,他们忽视人世间的“黑暗”,且追求异想天开乌托邦式的理想,设法苟且偷生。也有“文明的”男人在社会上混日子;当马洛摆脱了非洲的恐惧回来时,看见这些人感到很气愤。
另一方面,女人则“闷闷不乐”。她们是梦想的守护神,梦想着爱,梦想着美,梦想着信仰,梦想着希望。有人可能信这些东西,认为人世间是清白的,因为黑暗是梦想的破坏者。也有人以为,他们已看清楚了人世间更黑暗的一面,他们应该向女人撒谎,旨在让他们在梦想中活着。古德向他妻子撒谎;拉祖莫夫向纳塔丽娅·哈尔丁撒过一次谎;诺斯特若默告诉吉色尔,实际上,他来着手解决被窃的银两时,他来到大伊沙贝尔去拜访她;马洛和库尔兹都向库尔兹的未婚妻撒谎;德科德要安东尼娅告诉他,他的使命已“光荣而成功地完成了”。因为有崇高的看法,女人就可英勇地行动,似勒纳德斯一样,或她可以鼓舞男人去采取崇高的行动,如安东尼娅·阿韦拉诺斯所干的。因此,康拉德笔下的女性,皆有“支撑的幻想”、坚定的信仰,不管其真实性如何,能够使行动成为可能。这种信仰构成康拉德有些男性人物拒绝接受讽刺性的怀疑论;索菲娅·安东诺芙娜说,《在西方的眼睛下》里,“妇女、儿童,以及革命者都讨厌冷嘲热讽,这否认了一切本能、一切信仰、一切奉献、一切行动”。康纳德的着眼点,不是女人的真实或幻想,而是追求有理想的男人的那种冲动,即是艺术创作的冲动,“来自于所谓的灵感”[13](P112),也就是激情与想象。
康拉德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定型的男女人物,而这些人物并非是他非常感兴趣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使他着迷的不同人物:这个男人的性格正直,他认识到人世间可怕的真实,而且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他对超验观点的回应很热情。吉姆爷、马丁·德考德、拉祖莫夫、阿克塞尔·海斯特、安东尼船长、莫泽·乔治和汤姆·林加德,全是这种人物的变形。其中,每个人物,被描写成为世界理想化的概念,这个世界是女性的;每个人物也发现这是一个反常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希望破灭了,而且梦想也渐渐等于零。所以不是康拉德创作的“枯竭”,这使他去把他的主人公描绘成为麻木的解除武装的软弱无能的人。某些人几乎不可能行动,因为他们在人类两种矛盾冲突的观点中,感到心神不安。可以肯定,康拉德极为赞赏一位叫麦克沃尔船长对职责忠心耿耿的奉献;可是,就多数情况而论,在艺术上,他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人。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梦想,且相信唯心主义的希望是幻想时,那么,这个行动的过程是十分清楚的:他必须忠实地开船。然而,他不相信,梦想就是幻想,世俗和天上的要求既是强有力又互相抵消,那么谁也开不好船,况且失败乃至背叛的可能性就极大。
多个讲述人和不以时间为序的叙述,“小说中时间、地点错杂”[14](P576),是康拉德所使用的手法,肯定同时又否定。他把人物的描写置于矛盾冲突中,这需要极其高超的叙述技巧。莫泽认为,“康拉德的精髓是他的复杂性”。为了创作的小说获得希望的效果,即含糊不清、无结论性、涵盖面广,以及不确定性,康拉德肯定理想同时,讽刺性地将其暗中否定。罗亚尔·鲁塞尔说明,正是由于马洛叙述的复杂性,吉姆才成了康拉德要他成为那种不可思议的人物:“马洛的手法暗示,他试图把吉姆的光明与黑暗两面掺合在一起,在他成功与失败之间划出一条依稀可见的阴影线,果然,这两面看上去都含糊,要说吉姆的情况,可能全然不清楚,要说吉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那么,也许无人的境界能够确立,其中黑暗与光明可以共存。”在解读《吉姆爷》时,人们对他的判断很难弄准。但是,有人说,吉姆的梦想是让人轻视的幻想,也是非凡的理想,这也没有说准。
康拉德整个创作生涯说明,他把他的魅力同人类生存结合并做出多种解释。他曾给阿纳托尔·弗朗斯写信,说:“他知道,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是不能实现的;这是人类难以置信的灾祸,但也是其最高的特权,追求不可能的东西;人类以其人性的力量没有达到自己最高的目标,这种人性可以想象出最大的任务,而让他们在不可能挽回的小事面前解除武装。”他的早期作品,如同他的后期作品一样,像弗朗斯所说的,企图表现人类最大的不幸,这也是他最大的特权,他是一个梦想者。1910年之后,更加清楚的是,他把男人的抱负等同于女人给他带来的对爱的看法,他对人类生存的坚决主张没有减弱;比起吉姆的胜利来,我们对海斯特的“胜利”不应做太多的肯定。在康拉德一生,对其艺术上的衰退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他对男人与女人的看法有变化,而且他们在人世间的困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文学批评学就是要在这漫长的历史海洋中,披沙拣金,提要钩玄,弘微烛幽”[15](P7)。
[参考文献]
[1] Moser.Joseph Conrad: Achievement and Decline[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Press, 1957.
[2] (C) (B) Cox.The Modern Imagination[M].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4.
[3] Jocelyn Baines.Joseph Conrad: A Critical Biography[M].New York: McGraw-Hill, 1960.
[4] 刘海平,等.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 培根.培根论人生[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 胡经之,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8] Joseph Conrad.Joseph Conrad on Fiction[M].Lincoln: Uni.of Nebraska Press, 1964.
[9] 叔本华.劝诫与格言[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10] 冯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
[11] David Thorburn.Conrad’s Romanticism[M].New Haven: Yale Uni.Press, 1974.
[12] 林骧华,等.文艺新科学新方法手册[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3] 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4] 王先霈.小说大词典[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
[15] 潘凯雄,等.文学批评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