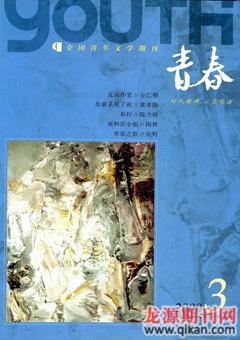我和筠小姐
陶 林
2004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居住在一个海滨小城的某一个阁楼里,写作属于我想象世界里的诗句和故事。为了养活我自己,我当时在一家小公司里上班,是一名负责内务工作的小文员——因此,更确切地说,我当时身份只是一个小职员。工作不算重,但报酬也很低,不够寻觅一个爱侣并养家糊口的。我看中的就是干这份工作留给我的自由时光,下了班之后,我可以闷在我的小阁楼里将每一天各种瞬间,在脑子里迸发出的种种乍现灵光书写出来,写成各种各样的作品。大多的时候,这些作品根本无法发表出来,也就无法为我创造除了微薄工资之外的收益,这样,我的日子过得有些窘迫。兴许是我的想法比较简单的缘故,我并没有急着恋爱或者是考虑婚姻之类的事情。因此,我的内心还是很悠闲的。
每天傍晚,我会独自一人从公司里出来,腋下夹着大学时代就使用的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我利用办公的空隙写下的只言片语。它们就如同是一些简单的发酵粉,为我日后一部部大著作而酝酿的。我时有抽烟的坏毛病,那时候,我就会一边走一边点上一支烟,避开市中心的喧闹与嘈杂,进入那些四通八达的小巷子。在巷子中行走,转头就可以看到两边被风熏得乌黑的墙体。那里,青蓝的砖早已变成了一块块黑砖。它们就像是纯粹由时间垒起的墙,坚硬地交叉,组成一个封闭的肠道,让一个诗人在它的消化里面迷失方向。
经过这些巷子的时候,我也总会经过一个小学校。每一天,当我听到这个小学校里孩子的欢声笑语时,我就知道自己这么迷失地走着该结束了。一所隐藏在深深巷陌中的小学校居然是本市的第二小学,这多少有点让我感到惊讶。所以有兴致到来的时候,我会巧妙地伪装成学生家长骗过门卫,进入这所学校,在为孩子们所设计的凳子上坐下来。这时候,感觉并不赖,在小学生面前点上一支烟,将刚满二十四岁的我伪装成一个老大人,时时瞪起眼睛看一看那些欺负小同学的胖小子——他们与其说惊怕我的块头与凭着力气来维持公道的可能性,不如说惊怕于我鼻子里缓缓喷出的烟来。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代表着一种来自父亲的权威。
城市里充斥着太多的高楼,而隐藏在深巷里的这所小学则到处覆盖着树木。葱郁、绿色的树,招引了和我一样没有去处的鸟雀。我坐在孩子们的椅子上,仰头谛听它们起起伏伏的欢叫,如那位曾与我一般大的英国诗人济慈所倾听到的夜莺之歌,如菲茨杰拉德所钟情的哀伤的歌。那时候,深怀青春期忧伤的我会凭借着糟糕的记忆力吟诵上一段诗:
我在黑暗里倾听:呵,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
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
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当你正倾泻着你的心怀
发出这般的狂喜!……
这是诗人穆旦先生所翻译的《夜莺颂》。这样的诗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般人精神上的奢侈。事实也能证明,现在的我根本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地吟诵。是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就像是一口空空荡荡的钟,风能吹响,石头能敲响,一枚硬币也能砸响。我想象自己在黑暗里倾听,在狭小的阁楼里倾听不知何去何从的日子。我越来越像一个具体生活中的瞎子了,为一点点维系自我生存的薪水而奔波。我怯于给乡村里的母亲写信,或者与任何的朋友联系,习惯在黑夜里一点点浪费掉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在,快乐的青年们在为自己青春的流逝而感到焦虑。当时的我,确切地说,很盼望自己漫长青春早点结束,等到自己衰老的那一刻。我当然也在等待别的什么,不知道究竟等待什么,异性,名声,理解或者钱。时光的流逝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啊,我肯定不止是在那所小学校里坐着那么简单,也肯定不止是吟诵着济慈引发无限伤感那么木然。死亡,肯定不是我终日纠缠不休的问题。但真的拥有衰老的我却只对这些津津乐道。那么,筠小姐呢?她与我究竟何干?我为什么要突然间记得这个很淡很淡的姑娘,犹如记起一段早已干枯的竹子,几片竹叶的零落……单纯是记忆的魔力,还是对整整一个世纪的眷恋?自基督蒙难后第二十一个百年,那些开初的年头,真是难以一语道尽啊……
在我经人介绍与筠小姐相识的时候,正在流行一首现在年轻人早已经没有能够记得起来的歌曲了。对于流行一向反应迟钝的我,当时并没有留意,现在更无从谈论再唱出来了。歌词的大意无非是一个男孩爱上了一个女孩,怯于向她表白,只是谈论风的声音等等。从一首诗的角度来讲,写歌的人是非常蹩脚的,他频繁使用“爱慕”这个词语来表达爱慕,就好像不停地在谜语里暗示谜底一样。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假使我爱上一个姑娘,我会一直看着她,用目光而不是嘴唇表达自己的心灵。可惜,姑娘们给我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她们听惯了风一样的甜言蜜语,也习惯于用那么多或者一点点精致的物品来传递爱恋——这些都是我所缺少的,所以我就一直单身。这里不得不说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年轻人非常流行单身的生活。一半人是没有学会如何去面对两人的相处,一半人是对相爱的成本估计得太高了。所以现在,我想对比我小的朋友们说一说:爱情似乎不要太倾听自己的理智,既然这是一种感情,就让感情来发话。如果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一种感情,那就什么都别想……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多的长辈会对年轻人习惯地说,恋爱要现实。可现实又能怎么样呢。
哦,好像已经说到了筠小姐吧……我是通过“相亲”的方式认识她的。现在,年轻人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方式。作为一名阁楼写作者的我,充满着一种年轻的自负,喜欢一次不经意地偶遇中所酝酿出来的惊喜。起初,我去相亲,完全是因为一种深深的好奇。在一半的时间里,我生活在自己的艺术虚构中。我需要寻找各种与我生活不相干的人和事物,将它们融入我的作品。对待每一段生活,我都只是当作一段艺术材料。筠小姐就是一份优雅的素材,她从枯燥无味的人事档案、平静如水的生活乱石丛中走出来,活生生地很从容地坐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一家叫“开心”的小餐馆里见面,为了准备那次见面,我为自己购买了一套能使自己看上去成熟一点的外套,却适得其反。
她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一切都是小小的美,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就像是我经常握笔写诗的那一只手。从她最初的一举一动中,我可以想见,几乎和我一样,对于这次“相亲”,她没有抱有任何的希望。她的身上充满了亮晶晶的小饰物。那些小玩意的光现在还令我记忆犹新,而我,却遗憾地忘记了她第一次的眼神。记忆啊,当我存留了她以后的眼神时,里面有多少的疑虑和猜测……她喝着一杯果汁饮料,用吸管搅动里面的冰块,面对脸红耳赤、语无伦次的我,显得异常地从容。我喝一杯茉莉花茶——那是和我大学时代第一位女友见面时喝的茶,味道一点没有改变。第一次见面,筠小姐向我介绍自己的工作:“我在一所小学里教书……”
“我知道,我知道。介绍人跟我提到过……是在哪一所小学呢?”
“市二小,你不知道的一个学校对吧!”
我由衷地发出了自己的惊奇,是二小吗,我几乎天天要到你们的学校去。我去干什么?也不干什么呀!几乎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那里。恐怕你们许多小学生都认识我。为什么?不为什么……他们知道有一个身怀法术的叔叔,常常占了他们互相交换小人书的位置。坐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看天看地,听听树上的鸟雀叫。并经常向他们抱怨,如果不是因为城里的鸟雀特别地少,他就会用弹弓打它们下来。这个经常在鼻子里喷出烟来的叔叔常常会自己对着自己说话,有时候是用中国话,有时候是用叽哩乌拉的语言。高年级的学生都知道,那是外语。他们有一次打赌并大胆地询问了这个喷烟叔叔,说外语和英语是一种语言,外语是“外”国的语言,英语是英国的语言。可喷烟叔叔则告诉他们,自己念的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外语,而是一种非常灵验咒语……
小孩子都相信你所说的咒语吗?筠小姐略有点惊奇,“他们都能跟你学?”
有什么不可以吗,我曾经带着他们念这样的诗句: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知道吗,这也是穆旦先生所翻译的英文诗歌,作者是雪莱——我可以背诵出英文的原句。我一句一句地教会了那些无知的小学生们,告诉他们用这样的咒语可以在冬天呼唤春天的精灵。
“你这是在欺骗学生们!”筠老师似乎觉得我这人太特别,有点怪诞。她当然不会因为我的怪诞而轻率动了凡心。作为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她不时地纠正我英文发音的错误。她又问:“如果小学生们发现你的咒语不灵验,那该怎么办?”
“噢,冬天还远呢,我告诉他们——是欺骗他们,说,只有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才能试验。”
“还真有小孩子相信了?不会有我们班的学生吧!”筠小姐看了看巨大的玻璃橱窗之外,“现在是秋天了,要到冬天来了,你骗人的把戏就会被拆穿了!”她似乎有点愤然。
“几乎肯跟我念的孩子都相信了。应该没有你们班的学生,他们都没有学习过英语,真到冬天的时候,这些孩子说不定就忘了这件事。再说呢,冬天我也不会整天到你们学校里去了。”
我和筠小姐喝茶,聊天,无聊中打发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她对我应该是处处不满意的,说话的怪诞,举止的僵硬……那时候还讲究身份什么的——作为一个在私营企业里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暗淡无光的收入和前途,等等。那时候的女孩子对公务员普遍地欣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种稳定感吧。正如筠小姐所说,有一个依靠什么的。无论什么时代,青年男女之间的相互认同总是有一定条件的——外在的,内在的,或者附属的。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的责任感来,也怯于过早地想象要对谁负责。我整天在读书写作,自得其乐,像被自己安装在一个不透明的套子里。那时,就是这样。
原本以为和筠小姐不会有第二次见面的,只是因为没有改掉到她的学校里静坐的习惯。那时,很多小学生都流传这样的话,说学校里来了一个能教人念咒语的叔叔。一段时间之内,我每天静坐的安适就变得稀罕了。每每放学后,身边就会围上一群的孩子。一位英国女作家写了本叫《哈利?波特》的童话传奇小说,孩子们几乎在一夜之间都相信,能够给他们带来奇异的人就在他们身边。而这个自称会咒语、听得懂鸟雀谈话的大叔叔几乎就成了他们对另一个世界渴望的寄托。我发现自己哪天不去那个地方,第二天孩子们都要打听我是否去了某个神奇的地方。真是一个意外,使我想辞去自己的工作到小学校里教书,继续骗这群孩子们。
某一天,跟随着孩子们的脚步,筠小姐找到了我。作为一个老师,她吓走了我所有的信徒们,并带着一种极其偶然的情绪说:“你!真的,在这里行骗?”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筠小姐,并确知她已经忘记了我。看着她那双沾满了粉笔灰的手,我仍不住自己的兴奋:“我可是从来不骗人的,我使你将来的英语课教学要轻松了很多。”
老师当然不屑一顾:“喊,你口语那么差,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反正放了学没其他事可干,筠小姐就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依然到上次那家叫“开心”的小餐馆。当时,我的生活状况很潦草,一日三餐几乎都在地摊的盒饭里享用。所以,邀请筠小姐吃饭其实也是自己的一次解馋吧。第二次,我们几乎又没有说一些实质性的话。面对我已不再腼腆,筠小姐从容并坦诚得就像是一只玻璃杯。她在我感情勃发的时候提醒我,她要寻觅一个成熟的,有一定事业基础的男士,年龄大一点也无妨。当时,她的话有点刺伤我的自尊,我从来不喜欢自己和任何人比,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任何的别人,而这位莫名其妙的筠小姐却力图改变我的趣味。她加以说明,这就是现实。这和我理解的现实截然不同,满是青涩书卷气的我一直将“现实”这东西看成是有待于我写的一首诗,或者是一篇小说。
有了第二次见面,我就忍痛向小学校里的孩子宣布,叔叔要骑着扫帚回去了——回到那个在每一个小孩子心目中充满奇异的地方,以后或许永远都不回来了。为了让那场告别充满甜蜜的气氛,我特地买了一大盒子的巧克力糖。分到糖的孩子们自然依依不舍,有大概三个孩子提出来要跟我走——为了不使自己变成一个拐卖儿童的罪犯,我当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还有一个小女孩哭了,她曾是第一个发现我与众不同的小孩,并第一个将我和魔法师相联系。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馈赠的铅笔、橡皮以及亲自绘制的图画……第二天经过小学校时,我偷偷看了看自己坐过的地方。那里,居然还有小朋友在等那位魔法无边的叔叔。一时动情,我差点走了进去。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筠小姐突然通过手机给我发了一个短消息,说:我已经好几次注意到你没有再到我们学校了。我回问:孩子们还想念我吗?她告诉我:连我教的高年级班级都开始谣传,有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师叔叔到学校里来过的。你这骗人的把戏,看来是没完了。我回复:呵呵,这居然是我这么多年来干出的唯一一件令我满意的事。筠小姐:我请你吃饭,出来聊一聊吧。这多少有点令我感到意外。我们第三次在那家名叫“开心”的小餐馆见了面。
还是简单的几样快餐。面对着蔬菜和肉类,她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啊,”我当时正感冒,声音很不干脆,“上班,下班,写东西。”
“没有谈女朋友?”筠小姐很关怀地问,却是一个我在那个年龄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习惯性的回答是:“没有,没有合适的——人家也看不上我。”有点酸楚的味道,可以博得别人的同情。事实上,我却是我惧怕进入具体的生活本身。但当时,我却油嘴滑舌了一下,很严肃地告诉筠小姐:“我一直在等你呢!”
她立即表示她几乎要被噎着。她跟我说了说自己的近况,无非是工作中的不顺心,与学生家长们之间的小摩擦等等。在叙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各自是年轻人——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们就像是一双筷子,硬邦邦地搁在桌子两边。筠小姐不厌其烦地叙述她的鸡毛蒜皮,如同在向我报一份菜单。可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或许,我是爱上了她吧,当我托着腮,盯着她那张精致的脸看的时候,的确如此。她把我称为孩子们的骗子,实事求是地指出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整天生活在不切实际之中。我一一加以肯定,并承认自己的不切实际。但我脑子里却这样转悠:她所谓的实际是哪一种实际呢,每天告诉自己的学生A是AA不是BB是BB不是A吗。我想,在一霎那爱上了这位女老师,除了她漂亮的原因之外,肯定是因为她越来越像我所面对的“生活”本身。当时,年轻气盛的我根本没有勇气去承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对生活本身却充满了耐心?——我很想知道,用自己冗长的青春去和生活无休止地打磨下去,会不会擦出一盏阿拉丁神灯什么的出来。
和筠小姐相处的第三个时段里,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给这位老师施加一点魔法,看看她会变得如何。于是第四次,我主动约请了筠小姐,她也没有拒绝。还是那家“开心”。那一次,我充分调动了自己在心理学方面似是而非的博学,跟本来没有多大兴趣的筠小姐讲述现代心理分析学派理论,也就是上个世纪弗洛伊德、荣格那群人。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说服倔强的筠小姐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着自闭性格的人——总之,那都是一套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的漫天胡扯。通过我长篇累牍的分析,我得意地诱导筠小姐成为了我的心理学病人,而想当然地扮演了一个心理医生。这是写作手艺带给我的唯一好处。然而,即使给筠小姐讲完了全部的心理学,并且让她承认自己心理有问题。我们之间还是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比起半年多之前,那时候的筠小姐已经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并拒人于千里之外了。这位小学老师已经有足够的耐心倾听我滔滔不绝的演讲了——而我只是在说心理学。当她发现我只是热衷于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全部魔法就都失效了。
一晃又接近两个月没有联系,我迎来了蜗居之中不够温暖的冬天。在一个周末,筠小姐又发来短消息告诉我:冬天到了。我感到非常奇怪,反问她:是啊,冬天到了又怎么了?你的心理问题解决了吗?筠小姐回复:我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但你的谎言被揭穿了!我想,没有孩子可以在冬天呼唤出什么春仙子之类的,就回复她:早在我离开之前,就给孩子们讲过一个故事给自己台阶下,你愿意听听这个故事吗?筠小姐没有立即回答我。沉默了很久,在我觉得她肯定不会回复我消息的时候,她拨通了我的手机,问:“什么故事,说!”
她仿佛在命令自己的学生,我不得不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说出来——
在那棵树下给孩子们讲咒语的时候,我就讲过类似的故事: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某一天有一个坏魔法师告诉他只要不停地念叨某个咒语一万遍,那个咒语就会杀死他。这个人不相信这一点,他就不停地念那个咒语,等念到九千九百遍的时候,他越来越害怕这个魔法师所说的是真的。但又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于是他等啊等啊,隔了很长时间才念一遍——等他念到最后十遍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之老了。在老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在真正临死前一刻,他终于念完了最后一遍。但念完了他发现自己平安无事,于是,他非常高兴,哈哈地嘲笑那个魔法师是个骗子。就因为笑得太过于用力,他背过气去,死了。我编出这个故事骗学生们,想告诉他们,我所传授的咒语千真万确,就看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一万遍了。
在我讲述故事的时候,筠小姐在电话中一言不发。最后,她不无愤怒地说:看来,你是我目前遇到的最会骗人的人,哼,不能再相信你了!她挂断了电话后,我发愣了很久,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位“生活”的化身相处了。我时时在问自己,我们是在恋爱吗?不是恋爱又算是什么呢?什么都不算,我们为什么一直要相识到现在。为了弥补我心中的种种遗憾,我又一次来到了那个小校园。那天下着雪,我去的时候,学生们刚刚放学。校园里很热闹,又很拥挤。我用手掌扫干净了石椅上的雪,坐在那里抽烟,斜着头张望落光了树叶的树丫。西方的圣诞节快到了,我还特地为我当初的小信徒们提前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孩子们在我身旁走来走去,为了各自的事情争吵,但没有一个再注意到我。雪慢慢地降落,我突然间感到自己真荒诞透顶了……
春天过去了,我与筠小姐联系的少而又少。那时,我开始发表了一些作品,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也没有改变我生活的现状。我一直酝酿着辞去这个城市的工作,南方有一些创业中的朋友在召唤着我。在此之前,我告诉筠小姐我恋爱了,和一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女同事恋爱了——对于她来说,或许这是一个轻松的了结吧。尽管,她从来没有准备爱上我。为了我草率的恋情祝福,筠小姐赠送给我一枚银质的项链——标牌上注明了产自于意大利——当然不是了,这一条细长的链子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佛洛伦萨、米兰、罗马和漫长的亚平宁海岸线扯上关系的。她跟我说是送给我未来的女朋友的——而事实上,我的这段恋爱刚开始就结束了。我赠送给了她一支以毕加索命名的笔——我花了三百多元钱购买了它,但我确跟她说是别人送给我的。它仅犹如一种心情而已,表达我对筠小姐或许一厢情愿的想象,也跟毕加索没有任何关系……是啊,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说,世纪初宁静又喧嚣的时光多么美好。那时候,大家各干各的事,彼此不会打扰。不断变化的流行音乐,肆无忌惮地宣称着自己的叛逆,贫乏又单调的生活里凭空产生很多的激情……
我一直在准备辞职。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我准备动身南下的时候,召唤我的那位朋友破产了。依然孑然一身的我,不得不再次留下来陪筠小姐进行这段不知所终的情感。第二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第九次见面了——却不是在“开心”。那是一个长假的前夕,我准备第二天到南方的某个城市去看望我大学时代的女友——她就快结婚了,即将成为一位商人的儿媳。而我去,主要是完成一次伤感的仪式。
和筠小姐一见面,她就很兴奋地告诉我:“你很成功!”
“什么成功?”我一时无法理解她所什么。
接下来,她就不厌其烦地用英文为我背诵了一首诗:
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岛,/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条编墙糊上泥;/我要养上一箱蜜蜂,种上九行豆角,/独住在蜂声嗡嗡的林间草地。
那儿安宁会降临我,安宁慢慢儿滴下来,/从晨的面纱滴落到蛐蛐歇唱的地方;/那儿半夜闪着微光,中午染着紫红光彩,/而黄昏织满了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起身走了,因为从早到晚从夜到朝/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总听得它在我心灵深处呼唤。
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写的《茵尼斯弗利岛》吧,怎么了?我问她。
她告诉我,她班上又很多学生会用英文背诵这首诗。我就祝贺她:那好啊,班上全是神童啊。她哑然失笑,说,那些神童都说背诵这段英文可以在天空上面将彩虹呼唤出来,很多人在下过雨过后试了,都很灵。
我立即记起了当年所播撒出去的种子,都两年了,那些中低年级的孩子已经升到了高年级。想想,也觉得挺有意思的。筠小姐又告诉我,在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作为作业,她就曾经背诵过这首诗,怎么背也背不上,却没有想到孩子们被人骗了却背得这么容易。她邀请我再回到学校去扮演那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师,我拒绝了。两年了,我早已经失去了刚刚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工作的那份闭塞中的悠然。即便是阅读诗歌的兴趣,也向着更深的方向发展。两年里,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筠小姐坐在一起吃饭。好似无始无终地坐在一起,既没有更深地了解,也没有更加陌生。
我就要动身了,去茵尼斯弗利岛。一个月以后,我又发送了一个消息给筠小姐,告诉她我就要走向一个全新的城市。跌倒了的朋友又将东山再起,我也将又有一次机会。这促成了我们第十次的见面。这次还是选择在“开心”。
她问,你要走啦?
是啊,我一直在准备走呢。我说,并习惯性地托腮盯着她看。
从此,不会再骗小学生们传授什么咒语了?
呵,一时的小把戏吧。
你虽然很会骗人,但有些话说得还是非常对的。
怎么,你也想学咒语了?
不是,我好像的确是有心理问题。
一周之后,面对朋友突然从人间蒸发的事实。我又不得不告诉筠小姐,我留下了,你当我的女朋友吧。短消息发出去,筠小姐却并没有回复,让我等了她一个夏天。
夏天结束的时候,筠小姐突然邀请我喝茶。一个暑假的休闲好像使她胖了一点点。我们见了面,变得更无话可聊了。她问我,你不是一直说要走的么?
我说,你在这里,走不了了。哈哈。
她就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告诉我,不要等啦,我跟你说过,我们没有可能的。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的,我欣赏那种……男士。
我感到很突然,问她:哪种……哦,就是非要和我比较的那种?呵呵……
时隔这么久,我发现自己学会了打哈哈,打一种对什么事似乎都漫不经心的哈哈。这是漫长的等待教会我的。就像是在演练《等待戈多》里那些无聊的对白一样——包括与筠小姐的相处,日子越发地被我过成了一个玩笑。两年多了,我为什么不迫不及待一点呢,非要和一位我一点都不了解的姑娘比拼自己无边无际的耐心?
她对我说:你是怎么看我的呢。一个总想揭穿你所编织那些故事的小学老师?一个内向、文静、善良的女孩?那么,我告诉你,没有认识你之前,我其实一直过得很愉快。我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很快乐。我们有男有女。有结了婚的,也有单身的。我们有我们的小圈子,大家就是聚在一起,挺平等,挺快乐。就算结了婚的,不会让自己的老婆或者老公知道自己的小圈子。
我听了并不是很吃惊,只是一点点地意外,不免底气不足地说了一句:哦。倒是很有小资产阶级的味道——
还没有等我说完,筠小姐就认真地反驳我:就小资产阶级,怎么了?我挺快乐的,不是挺好么,不是足够了么?你也常常发消息祝福我快乐不是吗?现在就真好,我没有发现能有什么快乐能够代替我们那个的小圈子。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方式,不谈论男人女人什么的,只是放松各自的心情。这样不是很好?
“嗯,可能我只是习惯了一个人干自己的事情,倒是没有想到别人的精彩。”我觉得在这一天,筠小姐似乎想向我亮出一张底牌。无论如何,两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竟然使我们两个本该擦肩而过的人聊了这么多。
我总觉得你很老……可能我所说的有些前后矛盾。我的确在一直寻找令我满意的男士。显然,你不是。或许,我也不是你要寻找的那个……你只不过爱去骗小学生们,让他们在一种错误的想象中长大一点。我又不是小学生,你为什么非得要纠缠我不休呢?
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我在这个海滨小城生活太无聊吗?我每天有越来越多的事要去干,所有的悠闲都在变成一种焦虑和恐慌。但我确实无法理解筠小姐所说的,那一圈无所事事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用各自来淡忘时间,真的很有意思吗?我才明白,面前的筠小姐越来越像我所面对的一个谜。这个简单又复杂的谜让我扎扎实实地猜测了近三个年头。在这个谜面前,我保持了一份并不算足够的耐心,可还是一无所知。当筠小姐用一种高度现实的口吻来向我揭开谜底的时候,我还是一无所获。
“那么。可以带着我到你们的小圈圈里看看?哪怕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问她。遭到了断然地否定。她说,或许我跟你想的不一样,但我却不相信自己有任何的不对。而你这么等,不是故意想让我内心感到愧疚的?
我说:“那又何必。”
她就不多说了。我想该到结束交谈的时候了,就在我掏出钱包,想去结这笔小小的账的时候。她又说了:“其实,你那些东西编得很好。虽然在骗小孩子们,但他们也曾围绕着你有一个小圈圈,并一样沉浸在你许诺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快乐中。”
我笑了笑,非常不爽气地说:“那,似乎有点不一样。不过,让每一个人都足够享有快乐,没有什么不妥,对吧。我们并不缺少什么快乐……”
“你又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了,如果你说起话来,能像骗小孩子那么简单,其实,你就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了。”筠小姐似乎在训她的学生。
“可能我书读的太多了一些,未必是一件好事,对吧。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我开始很稀罕地反省了自己,并解嘲,“我开始觉得必须要懂得尊重不怎么动脑子生活的人了,就像尊重一些孩子……”
“嗯,还是不知所云。其实一个人生活并不需要真读那么多书的。你读书其实也是一种娱乐,它为什么就比别人的娱乐更居高临下呢……”筠小姐停了停,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哦,越说越没意思了,我们走吧。”
我就和筠小姐分手了,我想将她往回送送,她拒绝了。这么久以来,我甚至不知道她住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方向。我爱上这位小学老师的一霎那,我觉得她那么得不真实。当她变得很真实时,我却满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奇妙的简直太过于简单了,比任何想象要直截了当得多。
那一次分手后,我几乎就再也没有跟筠小姐联系过。我爱独自一人到“开心”去坐一坐,并相信再也没有思考和写作更令我着迷的事情了。我离开海滨小城的时间又一次次地被推迟,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似乎一辈子走不了。就在那一天起,我和另一个完全不了解我的姑娘恋爱了。平静的日子蜂拥而来,恋爱、结婚、耐心地与没有了筠小姐的生活相处,终于在沉默的砂轮上磨平了自己的青春,直至终于有一天离开了那个海滨小城,到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去……
现在,我偶尔打开自己的电脑,还能在古老的歌曲存储中听到那时候曾迅速流行又忘记的那首老歌。歌词的大意无非是一个男孩爱上了一个女孩,怯于向她表白,只是谈论风的声音等等……我现在听来并没有什么感动,只是感想很多。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啊,过早地沉浸在有关爱情想象的消费中,同时,也过早地忘却了什么叫爱情。我,筠小姐,大家都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我曾经忘记了那个小城,正如今天的年轻人正在将我们遗忘一样。那个糟糕的海滨小城,日复一日的发生着变化,我们都没有能够比它更加地从容。离开了它的我时时感到还走在它黝黑、深长的道路上,默默地回那个深巷里。我想,我还要慢慢走进那个小校园,坐在那个被香樟树的阴影所笼罩着的石椅上,抽着烟,斜着头发呆。那时新雨过后,我的脑子里刚为分了手的大学女友写了一首酸楚无力的解构主义诗篇。诗歌与其说表达我的怨怼,不如说为了原谅自己的狭隘寻求解脱,衬托出我所钟爱的济慈、雪莱们的伟大。我说假使你又想念起我,我说:
当你老了,围坐在时光的褶裙中/假使你的青春不再,却又想起我/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曾衰老/在你的记忆里却格外年轻/懂得去赞美落叶和鲜花。
你该记得我什么呢,或是憎恨/我曾高贵的哀愁,变成了记忆的海峡/多少次,你只在彼岸眺望着我/我们互相看不见灯,只有金子燃烧的火/多少人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我也曾如此,并确知我们灵魂一样地孱弱。
假使你真的能够又想念起我/就请在时光的火炉边拿起这些诗/当岁月已经早燃成了冰冷的灰烬,我们/于是知晓,没有一种过错不可以被原谅/曾经卑微的两个年轻生命,仿佛啊/只是为无尽的懊恼,才共同写过/一行又一行,潮湿、柔软并虚伪的诗句。
也是在那时,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走到我的面前,她将自己的眼睛瞪得非常大,活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水汪汪的,很美。
我也瞪大了眼睛盯着她看。我们似乎相看两不厌,足有一分钟。后来,小姑娘说了:“叔叔,我知道你的秘密!”一种天真又充满期待的口吻。
“是吗,看来你注意叔叔很久啦,说说看,叔叔有什么秘密呢!”
“你天天坐在这里向天上看!”
“是啊,叔叔是天天在向天上看。”
“你想写信回家吧!”
“是啊,我最怕给妈妈写信了,我一写信就骗我妈妈。”
“可你又想回家是吧!”
“是啊。可我一定要在这里搭我的小家家,可这不能算什么秘密啊。”
“对啊,我也想家啊,我家也不在这里,可你为什么非要往天上看呢。我知道,这就是你的秘密!”
“是吗,说说看,叔叔会有什么秘密被你知道了。”
“叔叔肯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你肯定从那上面的世界来的,你是个魔法师吧,跟哈利·波特一样……”
“哈……真被你发现了,过来吧!叔叔告诉你,我就是一个从云上掉下来的魔法师呀,我变个戏法给你看看:喏,这是一个硬币,我数三声——哈利哈利变!看它不见了是吧,就是要念这个咒语了,哈利哈利变……”
责任编辑裴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