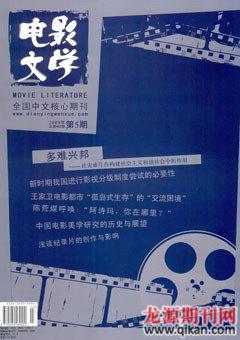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的作者观
姚 颖
摘要约翰·福尔斯面对后现代文本中的“作者”被宣称死亡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不断打破传统的写作手法。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重新构建“作者”的权威性。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中,福尔斯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干涉和介入到作品的叙述过程和阅读过程中,以重新塑造作者“一个新的神学形象”。而读者在享受阅读文本的自由的同时,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新作者权威操纵和影响
关键词作者观。《法国中尉的女人》,叙述过程,阅读过程
自巴尔特宣布“作者已死”之后,后现代主义作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之一,约翰·福尔斯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另一方面又维护着小说中作者的权威地位。本文旨在探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介入到作品的叙述过程和阅读过程中来重新塑造新时期作者的权威。
一、时代背景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作者存在的绝对权威受到了质疑。巴尔特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观点,认为“文本在今后的创作和阅读过程中,作者在它的所有层面都是缺席的”,以作者意图为出发点的批评理念也发生了转变。巴尔特把解读文本意义的焦点从作者的潜在意图转移到了读者,从而以作者死亡的代价来换取读者的诞生。
但是不少后现代派的小说家面对自己已被宣告的“死亡”,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宣判。他们一方面要打破传统写作,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己在文本中的“存在”。1969年,英国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在他发表的题为《十字路口的小说家》的论文中指出,小说家还可以做出这么一种选择,那就是“在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甚至把这种犹豫不决写进小说”。所以后现代派小说家们通过各种写作手法,变换角色,从幕后到台前,出现在文本中,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向读者申明自己的存在。
二、《法国中尉的女人》体现的约翰福尔斯的作者观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于1969年发表了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以维多利亚中期为背景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小说从创作方面对洛奇的乐观回应。这部小说在继承和吸纳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包含着现实主义、实验主义和反小说成分,而且也确实写出了创作者犹豫不决的窘境。
福尔斯在《一部未完稿小说的笔记》中这样盘问自己:“在旧传统中写作使我在多大程度上沦为懦夫?我又在多大程度上惊慌失措地跌入先锋派?”虽然福尔斯反对德里达、拉康等把文学变成完全科学从而把作者“赶跑”的做法,他却十分推崇巴尔特,对小说文本解读尺度的把握做出了深刻的思考,然而福尔斯并不赞同巴尔特“作者已死”的观点,他认为:“小说家还是一个上帝,因为他在创造。”他在多种场合认为小说是“上帝的游戏”,并且他一度还想把他的小说《大魔术师》命名为《上帝的游戏》。事实上,福尔斯既重视读者对文本解读的多样性,又不完全放弃作者的权威。福尔斯在阐发他的创作观点时说道:“小说家仍是上帝……但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全知全能的形象,而是一个新的神学形象。”
为了重新塑造作者在后现代小说的权威,福尔斯利用传统的作者介入——评论、加注、任意引用——手段,甚至直接进入情节成为小说中的角色。但是20世纪的读者不再受到“上帝”的操纵,后现代作家一方面期望创造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表现得无所不知、发号施令。“关于上帝的完美的定义只有一个:允许别人享有自由的一种自由。我必须遵循这个定义。”
遵循着这种作者观,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过程和阅读过程中重新塑造了作者的权威地位。
三、《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作者权威
1文本的叙述过程
(1)叙述方式。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在讲述一个发生在19世纪中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的同时,却又把注意力返回到叙事行为的本身,对其进行反思和探讨,采用了自觉或自反的叙述方式。理论家所说的自觉或自反的叙事指的是叙述者探讨或反复思考他们正在讲故事这样的一个事实,拿不定主意该如何讲述,或者甚至吹嘘他们能够决定故事将如何结局的一种叙事。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像“我不写她站在窗台上摇摇晃晃,也不写她向前摇晃了一下跟着哭泣着往后瘫倒在房间的旧地毯上”这样的例子。作者甚至会用大量篇幅去探讨小说的创作(第13章),结局的选择(第55章)等等。
对福尔斯这种叙事的干预,柯里评论说:“在维多利亚式的干预中,只是作为一种叙事的坦诚以提高其现实性方式的地方,福勒(福尔斯)却将它变为一种打破幻觉的自我反射性,让读者记住正在呈现的这段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创作。”
(2)作者在叙述中的多重身份。作者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是多重身份的。他时而是叙述者,时而是评论家,时而又变身为故事中的人物。作者通过自由进出文本,揭示文本创作的自主性,也显示掌握这种自主性的作者的权威。
创作主体是叙述者。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不断变换人称。在讲述故事过程中,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却又夹杂着第一人称,不时地向读者谈论写作。例如,第2章描述了蒂娜和查尔斯在莱姆湾的“科布”堤散步时的对话,这场对话向读者介绍了这两人的身份。作者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一种客观描述。作者第17章写查尔斯陪特兰特太太和欧内斯蒂娜去听一场宗教音乐会。作者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走进查尔斯的心里,描写他与萨拉意外相遇这事所引发的复杂情绪。而第13章的大半部分,作者以作家的“真实”身份,采用第一人称向读者谈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和现在的作者的不同作用。
总之,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通过变换人称,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可以进行全知全能叙事,或从有限视角叙事或客观叙事,也可对着读者发话。作者在叙述中充分享受了游戏的乐趣,也建构了作者的权威。
创作主体是评论家。
作者的评论在叙事过程反复出现,把小说的虚构性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暴露小说的“纯属虚构”,其实更是强调了作者创作的任意性。读者在阅读中,作者不断地对着他们说话,向他们作解释、介绍、评论甚至是指导。作者发出的这些声音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中。例如:“萨姆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势利鬼。他对服装样式极为敏感,几乎与20世纪60年代的‘摩登派一样敏感”;“玛丽的曾孙女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22岁,长得很像她的祖先,她的那张脸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因为她是英国著名的年轻电影演员”。
而福尔斯在评论中大量使用“计算机、电影、电视、好莱坞”等20世纪的词汇,硬把读者从历史拉回到现实,打破了对现实的幻觉。目的是强迫读者接受另一种事实:小说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作者是更高层次的真实,拥有权威。
创作主体化身为角色。
巴尔特说“作者已死”,福尔斯干脆走到台前,用文本中具体的角色证实作者的存在。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
作者不仅出现叙述声音,而且自己的形象也出现了三次。
小说一开始,一个“当地的密探”通过他的望远镜带读者观察着蒂娜和查尔斯在莱姆湾的“科布”堤散步。透过这个神秘的密探,读者偷窥了蒂娜和查尔斯。如果说作者的第一次出场还是不易察觉、含蓄内敛的话,作者的后两次出场是一次比一次张扬喧闹。
第55章在去伦敦的火车里,查尔斯遇见一位四十多岁满脸胡须的男人一直盯着他看。作者承认他就是这个大胡子陌生人(作者福尔斯在现实生活中蓄着长长的胡子)。在这一章中作者化身为角色,活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然后又现身说法,把大胡子的目光称之为。万能的神才应该有的目光”。
而作者最后一次出场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结局。这一次,他的伪装不再是19世纪的装扮,而更像一个成功的歌剧院经理。“他那族长式的浓密大胡子已经剪短了,法国化了”,“一件夏季西装背心绣得花里胡哨”,“手指上戴着三个戒指”,“琥珀烟嘴上插着一支细长雪茄”,“孔雀石头的手杖”,对拉莱格外貌的细致描写,使他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再不容忽视。“他就自己闯进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带着他的真实面目闯进来的”,“他显然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他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占用和使用”。拉莱格掏出怀表——布雷格特造——把时间做了一点小调整——拨快了一刻钟,小说又回到了萨拉和查尔斯一开始的对话,另一种结局开始了。
2文本的阅读过程
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采用了许多后现代派的写作手法,从表面看让自己的人物角色和小说叙述方式比以前传统小说拥有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他在尊重读者阅读多样性的同时,也达到了构建作者权威的目的。正如他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说,这是小说的“上帝”给予的自由,“小说家仍然是一种神”,操纵着他所赋予读者的自由。
(1)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法国中尉的女人》所具有的典型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创作和批评的对话,平等个体之间的大型对话,小说语言中永不停息的微观对话。其中创作和批评的对话主要体现为作品中使用超小说手法,对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赋予读者以前所未有的自由。
如:呃,你可能会说,我的实际情况是——我写着写着,忽然灵机一动,觉得让查尔斯停下来喝碗牛奶,让他再次跟莎拉相遇,这样的写法更聪明些。此话自然有其道理,可以解释我的那一段描写。然而,我只会报导——而且我是最可靠的目击者——我觉得,去牛奶房的那个主意明显地出自查尔斯,而不是出自我本人……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读者还被作者频频使用的“我们”、“我们的”、“你”、“我和你”等套近乎的词语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进人文本中,站在作者的立场,一起游戏、一起创作。在第45章中,当作者告诉读者“虽然我们当中写诗的人并不多,但我们都是诗人。我们同时又都是小说家,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小说来描绘自己的未来”时,读者俨然觉得自己确实是个小说家,并也试图为小说里的人物命运进行盘算和谋划。
约翰·福尔斯在小说中以大量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积极而坦诚的关系,使读者站在作者一边。产生共鸣,成为作者所希望的理想读者。读者在享受作者所给予的阅读的自由时,也成为了作者统治世界中的一部分。
(2)多重结局。福尔斯的有限自由还同样体现在他的开放性的结局中。作者一共为《法国中尉的女人》设计了四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是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设定:查尔斯与蒂娜结合,并走上了从商之路,而波尔坦尼太太死后下了地狱,但作者接下来就说这只是查尔斯的想象而已。在第55章作者曾经考虑“此时此地就结束查尔斯的生涯,考虑永远把他留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但是福尔斯又认为由于这开放式的、不确定的结尾不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惯常写法,而且也不能体现他所主张的小说中人物的自由,第二个结局被简单地一笔带过。第三个结局安排在第60章,莎拉先是以她的冷淡回绝了查尔斯,后来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的结晶——他们的女儿出现在查尔斯面前。于是查尔斯与莎拉走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最后一个结局发生在第61章中,莎拉最终拒绝了查尔斯,查尔斯离开了莎拉,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从这四个结局看来,福尔斯似乎很彻底地体现了自由的理念,让故事自由发展,让读者有充分的选择,尊重了读者阅读的多样性。为了让自己表现得不偏不倚,作者甚至采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最后两个结局的写作先后。但是,福尔斯还是为读者提供了选择项,并且对选择项做出了自己的评判,甚至自己还暗示哪一个才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我不可能同时把两种结局都写出来,然而,尽管前一章写的那么肯定武断,这第二种结局似乎才是最后的,‘真实的”。即使作者不暗示他对结果的偏好,这种开放性的结局本身就显示了作者掌控大局的权威性。读者的阅读自由,在阅读过程中的发挥想象,一早就被作者一一料到,并且在文本中展示了。
四、结语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一方面通过后现代的写作手法试图摆脱传统小说作家的绝对权威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在“作者已死”的一片呼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重新塑造新时期作者的权威性。通过对作品叙述过程和读者阅读过程中的不断介入和干涉,作者合理控制着叙事过程,适度操纵着人物角色,还以不同角色在文本中自由进出。在阅读诸如《法》等后现代小说时,读者在享受阅读文本的自由的同时,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新作者权威操纵和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