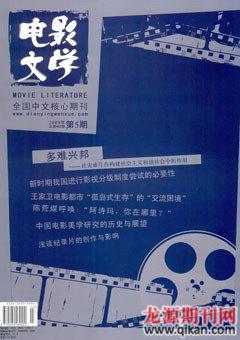一曲女性自我解放运动的悲歌
欧阳钦
摘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二颗璀璨巨星,钱钟书与张爱玲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巧合的是,二位大家在其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着力塑造了众多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笔者拟通过对其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体验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而深入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关键词自我解放运动,悲歌,女性形象,原罪意识
作为中国当代的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一生博学多才,著述颇多,尤其在散文创作中更是别具一格。但其小说创作领域,却仅有《围城》这一部长篇小说和《猫》《纪念》两个短篇小说,然而就凭这几部作品,钱先生就已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家地位。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异数”,张爱玲在小说创作的园地上硕果累累,《封锁》《金锁记》《倾城之恋》《色戒》等,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巧合的是,二位大家在其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着力塑造了众多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笔者拟通过对其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体验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而深入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一、共性分析
1都背负“围城”的重负,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走出婚姻的城堡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围城”于读者而言是一个具有很大解读空间的词语,钱先生借西方的典故所暗示的寓意,将之置换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围城”意象,益发凸显了出入其中的艰难,同时也反衬了人们冲决出“围城”的强烈欲望。
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多处于多重围城之中,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她们接受过较新式的教育,因而她们挑战男权社会,改变现状的自觉要求就更为迫切,这也就注定了她们的悲剧色彩的更加强烈。
苏文纨,这位心气颇高的才女曾一心想将方鸿渐围捕进自己构筑的“围城”,但未获成功。遂而投入了诗人曹文郎的“围城”,孙柔嘉算是成功地从“城”外挤入“城里”的女性,可最终也只能作茧自缚地将自己困入“围城”之中而不自知,《猫》中风光、美丽,长久享受着男人众星捧月般恭维的爱默,更是心甘情愿地沉溺于“围城”之中而长眠不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丈夫少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纪念》中的曼倩,在情人逝去后努力维持着她的“围城”,她与天健“两个人的秘密”是她身心的一次秘密突围后留给她赏玩不已的精神财富,凭着这一尘封心底的财富和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资本,女主人公期待着再一次突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香港的沦陷,心甘情愿、如愿以偿地挤进了范的“围城”中。
相比之下,《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则更是将这“突围”的行为推向了极致。在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始终只是英雄高亢呼啸的回音中的一个微弱颤音后,当汉军已经围攻上来后,在项羽一再要求她随同突围时,虞姬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拔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同时留下了谜一样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张爱玲借这一历史形象概况那个时代具有新思想、要求独立的女性的普遍困惑:既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又洞悉到这种依附后面的空虚。在这两难的苦苦挣扎中,艰难地探索着突“围”的道路。
2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难
女性生存的艰难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的话题,在中国这个封建旧思想蒂固根深,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度里,这个问题越发突出。知识女性们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观念的捆绑,并为改变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而竭力抗争,但却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在社会中从属、附庸的角色定位。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反复出现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虽说她小说中的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如影随形地威胁着她们,因此,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成为有钱人的太太甚至是情妇,二是一旦达到目标后,又不自觉地为维护和改善已有的地位而费尽心机。”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读书投靠了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从此以后她逐渐成为了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虽然,她也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并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而且买好了船票收拾好了东西,可临行前的一场病却使她怀疑冥冥中是否有什么东西让自己留下来,于是她还是留下了,留在了那个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于是。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堕落到幻想贬值、自信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的风尘女子,这一痛苦的蜕变经历将女性生存的艰难和盘托出。
相比之下,钱钟书先生笔下的知识女性则更多地从精神层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难。在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不必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一样为生存而出卖自己的肉体甚至是灵魂,但却始终难以改变她们在社会中从属、附庸的地位。苏文纨婚姻落败后委身于能写几句歪诗的曹元郎,最终只能通过走“单帮”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心气极高的汪太太虽做了一次大胆的突“围”行动,但在银样蜡枪头赵辛楣的退缩后又投入到三闾大学的“一潭死水”之中。
轰轰烈烈的奋斗,抗争就这样以各种方式——或悲剧,或喜剧,或闹剧——偃旗息鼓,“战场”上的硝烟尚未散尽,张爱玲与钱钟书笔下的苏文纨们已在“围城”内外领受了由男人们分配的角色,宿命难逃。
二、个性比较
1知识女性思想意识比较
与张爱玲笔下的知识女性相比,钱先生作品中的知识女性思想意识更为激进,因而在女性自我解放运动的征途上也就走得更远。在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女人所承受的所有压力中,生计问题被迫切地摆在第一位。在这一前提下,婚姻成了生活的保障,恋爱不过是得到保障的手段,她们所表现出的对金钱物质的迷恋和不能自拔使读者们感叹不已:粱太太、葛薇龙、教风、霓喜,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七巧,我们不知道她进入姜家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激斗,然而终于嫁给了姜家的痨病二少爷。这桩买卖虽然表彰了七巧的生存,却注定了她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七巧情欲受阻后,转而拥抱物欲,然后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
经济上的不能独立,导致其人格、心理上、感情上均有强烈的依附感和压抑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均是男人和自己各种欲望的奴隶,这类人尽管都有着泼辣的生命力,但她们的地位却始终无法确定,疑虑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了自私者。葛薇龙为求生存得轻松些,在一次次的诱惑中,不知不觉地堕落·《倾城之恋》中的自流苏。为了摆脱寄宿娘家遭人白眼的处境,钻头觅缝要寻找一个安全归宿,《连环套》中的霓喜,一次次与人姘居,却最终
遭到抛弃。
相形之下,钱先生笔下的知识女性则要幸运得多,她们有着较殷实的家庭背景,且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于是,在摆脱了生计问题的困囿后,在婚姻问题上她们更多地表现自我价值观的实现,而非谋生的手段。于是,淡薄了门当户对观念的她们,在爱情游戏中设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主动出击,甚至为将男人玩于股掌之中而神采奕奕,风姿潇洒。
对于《围城》中苏文纨的走“单帮”,许多人觉得是苏文纨的财迷心窍。但依笔者看来,恰恰相反,这是她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家庭妇女,她要做点什么,以验证自己的独立意识及驾驶命运的能力的一种表现。有心计,善经营的孙柔嘉,大学毕业后积极到三闾大学求职,并以自己的智慧将方鸿渐缚入“围城”成就了自己的婚姻,猫一样在家苦心经营女性王国的爱默,在沙龙里接待着社会各界的茶客,接受各界名流的膜拜。
钱先生笔下所有这些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在摆脱了生存的危机后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比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更为激进的行动,而这激进的思想和行动的背后,则是这些知识女性们不甘心在男权社会中受附庸、陪衬、边缘角色的积极抗争,虽然这样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另一个极端,但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其进步意义却难以抹杀。
2对旧时代对女性的扼杀及戕害比较
与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女性相比,张爱玲笔下的知识女性更深刻、更本真地暴露出旧时代对女性的扼杀及旧思想对女性的残酷戕害。在张爱玲23岁时(1943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为影响整个人类的一种文化哲学在中国内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张爱玲自然也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她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对人的心理,特别是变态心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娘家人卖给姜家作了二房“奶奶”,而陪伴她的却是一个“没有半点人气”“没有生命”的肉体。强烈的性欲望,使她的窥淫欲与施虐欲疯狂地增长。在泯灭自己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周遭人的希望:儿子房中“秘闻”,被她在牌桌上“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地散布,把一丫鬟给长白做小,导致其被折磨至死,姨太太吞鸦片而亡。千方百计阻止女儿恋爱,恶毒地设计圈套,断送了女儿长安的婚事……如此种种使其堕落到万劫不复之境。其手段之低下,心底之阴暗,极尽让人心惊胆战。
弗洛伊德曾打过一个比喻:本我是匹马,自我是骑手。曹七巧正是一匹失控的马,她的生活愿望被压抑后的极端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变态行动,是一种没有分寸的疯狂。弗洛伊德认为:人有死的本能,死的本能主要表现为求生的欲望,当它向外表现的时候,它是仇恨的动机,成为侵犯、破坏、征服的动力。如此可见,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即是性的本能因受到外部和内部挫折剥夺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满足。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寻找发泄,直至人格扭曲。
透过曹七巧人性背后,作品中分明展现给读者一幅苍凉可怖的人生图景。曹七巧何以由一个女人而成为女奴,由女奴而成为女畸人、女虐待狂,其中内在的原因,即这种变态心理的背后,则是中国旧式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七巧身上多的是受压抑。少抗争。因此,小说中对于由其兄长一手安排的婚事,从没写七巧的竭力反对,而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她的害人与被害,从而以曹七巧这个最彻底的承受了所有旧时代妇女的不幸,最彻底的承受了旧时代妇女的心理重负的个性形象概况了旧时代女性的共性特征。
七巧内心的“原罪意识”被作者展示得淋漓尽致。张爱玲掀开了曹七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描述了曹七巧苍凉的一生,冷静而深刻地展示她的人性泯灭的过程。
相比之下,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女性则更多地在一个平面上“咀嚼”旧传统思想重负下人性的弱点,如苏文纨高傲自负、孙柔嘉的巧于心计、爱默虚荣高贵、曼倩的精致哀怨,虽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而对于人性弱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人物形象却未能做进一步深度的开掘。
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为何如此之艰难,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三、知识女性自我解放悲剧命运的根源
首先让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在“男女平等”口号指引下,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等等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在张爱玲的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却仍在男权的社会的“围城”中无法自拔,而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女性却开始迈起了走出“围城”的第一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她们之间的差异呢?很明显,经济上的独立是后者能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一个关键原因。而伴随经济独立的是思想上的自立,思想上的自立带来的是行动上的更加激进,激进的行动带来的是经济上的更加独立。
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前驱马斯洛在人的“需要层次”论中处在最底层、也是最基础的一层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张爱玲笔下的知识女性们为着生存不惜一切代价透支着一切可以透支的资本,又焉能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而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女性们,在程度不同地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后,都在为实现自我的某种需要而苦心经营着。这里需特别强调的是《围城》中苏文纨的走“单帮”,论者对此普遍挖掘不深或嗤之以鼻,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体现出了这位在婚姻和职业上特立独行的女才子的一种抗争,一种自我实现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种抗争,其做法虽有点与其身份不符,但在思想上却迈上了与旧时代“贤妻良母”的思维定式分道扬镳的人生道路。
遗憾的是,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女性在即将迈出“围城”的脚步后便戛然而止,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而这一切却都源于自身在中国这个封建旧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里特有的、与生俱来的女性弱点——对男权的依附,一种跨越了传统的物质条件依附后一种更高层次的依附——精神依附。
透过婚后孙小姐加之于方鸿渐的种种折磨,我们不难体察得出这种精神依附背后的女性的心酸,她对方鸿渐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想逼他走,而是想镇住他。征服他。只有如此,她才觉得安全又放心,不然一旦丈夫负心,婚姻破裂,对方鸿渐是一种解脱,对孙柔嘉则是一场灾难。
由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时不难发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而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绝非一日之功,在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后清除内心深处女性的“原罪意思”将更迫在眉睫和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