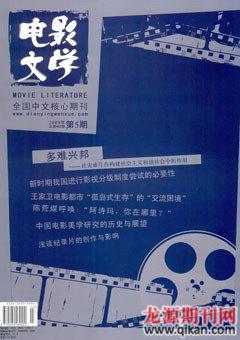当代中国电影“弑父者”人物形象构建
王玉坤
摘要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出现疏离、分歧或矛盾,象征性转喻了父辈与子辈间文化上的冲突、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弑父”大都发生在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父辈的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遭到子辈的质疑和抗拒,逐渐成长的子辈试图摆脱父辈话语权的桎梏,夺取话语表达权,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在此种背景下,影片对子辈“弑父者”的言说采取了共性化的人物建构策略,突出了家庭伦理矛盾背后激烈的新旧文化冲突。
关键词弑父;弑父者,人物形象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在经历种种社会变革、文化冲突时,影像世界中子辈的成长与挣扎总是着力表现逃离原有父权体系,挣脱现有话语权的束缚,“弑父”现象成为不同时期对于文化变革的强烈呼应。在“弑父”的文化代际过程中,影片在子辈“弑父者”人物塑造方面,对作为“弑父者”的子辈分别从其所处的压迫性环境、所属的边缘化身份进行双维度的建构,形成“弑父者”受压迫、受排挤的人物特征。还将个体主人公纳入人物组群,将个体的叛逆经验拓展为社会的群体性叛离,从个体对父亲的反抗衍生出子辈对父系权威的挑战。
一、“铁屋”中的年轻灵魂
渴望摆脱权威、自主选择生活的主人公,却往往出现在父权高高耸立的地方。象征封闭和传统的古老庭院、陈旧弄堂、偏僻山村,甚至是象征政治强权的军区大院,都成为叙事的空间。这样的叙事空间,形成了新鲜与陈旧、围困与叛逃的二元对立意象。鲁迅先生曾经将封建中国比作。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表现“弑父”母题的电影也乐此不疲地建造着一间又一间压抑的“铁屋子”,被囚禁着的年轻子一代,要么无声无息地窒息死去,要么就要打破父权的牢笼,冲出去获得新生。
这间“铁屋”可以是皇宫、军区大院,由一个亦父亦君的中央集权掌控着每条秩序、每个人的命运,强调对子辈的绝对控制。可以不问是非,为所欲为。这间铁屋也可以是庭院、老宅,代表着家长权力半是压迫半是挽留地牵绊着子辈“弑父”的脚步。这间“铁屋”还可以是偏远的乡村、小镇,象征着封闭、落后、愚昧的传统价值观对人性的制约与压抑。
影片中的子辈都是年轻的主人公,他们处在一个青春期将过而未过的时期。他们厌烦权威榜样的教诲,反感禁锢思想、情感的僵硬法则。子辈在压抑下体验着青春的萌动:梦想、爱情、痛苦、死亡,脱离父辈掌握的人生经验陌生而新奇,充满着不可名状的快感。处于狭小、压抑、封闭空间的子辈向往着一个更为宽广的天地。
《植物学家的女儿》里这间“铁屋”是一个在小岛上由父亲管理的植物园。子一代生于斯,长于斯,她们如同父亲栽种、浇灌的植物,被父亲赐予生命。父亲为她们制订严格的法则,生活上严格的作息时间,饮食上的偏好,无一不是以父亲为主体的。她们被忽略、漠视,小心翼翼地忍耐和生存。但在循规蹈矩的表象下,她们也像植物一样生长茂盛,年轻的生命同样充满青春的骚动,在黑色的牢笼中蠢蠢欲动。她们虽然处于严密的监视和管制下,但却还是忍不住偷尝自由和反叛的禁果。积蓄年轻的力量。如同顾城在《一代人》中的宣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子一代鲜活的生命注定要与陈旧的“铁屋”抗争,摆脱父权的控制。
二、游离的边缘族群
子辈往往并不是处于社会上层和中心的大人物,而是脱离家庭生活轨道、脱离正常社会秩序的边缘人物。被流放的太子、卑微的轿夫、骗子、小偷、同性恋者、妓女、吸毒者、艺术青年等。他们在生活中处于劣势,在精神上却有超越常人的思考。他们逃离家庭不再受父亲的控制,他们的生存困境是来源于社会上各种力量的控制与压迫。影片试图给这些反叛的角色以话语权,矛头则直指无所不在的一元权力中心。
《北京杂种》中茫然的艺术青年、作家以及混混,在喧嚣城市里无所事事地游荡,散落的、碎片化的个体生命经验浮现出焦虑、躁动、愤懑、抑郁、迷失。“我们都是一样的……由着性子胡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社会的异己分子”,试图用逃离、蔑视社会常规来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却不知道应该去向何方。
电影中常以音乐的边缘化来表现人物的边缘化身份。边缘化的音乐对情感的表达是非主流的,坦荡、赤裸、不加掩饰,呈现出一种情感的碎片化形态,可以触动心灵却没有终极目标的精神梦想。《黄土地》中顾青到陕北的目的是搜集民歌信天游,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新文化也要向其中寻找力量的根源。而信天游的民歌又是在那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当地人民对命运无力地呐喊,唱“酸曲”是为人所看不起的。影片开始的喜宴上,唱“酸曲”的汉子只能以类似乞讨的表演混口饭吃。所以翠巧的“酸曲”唱得越好,她就越向传统文化的边缘游走。《夜宴》中流放吴越之地的太子无鸾所带来的越人歌,舞者们苍白的衣服和面具,怪异扭动的肢体,清亮的歌声婉转幽怨,透着彻骨的寂寞,相对于代表宫廷庄严的黄钟大吕、轻歌曼舞,它只是山水间的一缕幽情。现代电影中,多以摇滚乐作为子辈边缘身份的标志化象征。摇滚乐以破裂的音节、夸张的肢体语言释放、强化着意识中最原始的渴望挣脱、获取自由的情感。《北京杂种》《昨天》《长大成人》中都出现了相同的角色,他们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声嘶力竭地向陈旧的条条框框宣战,揭露工业社会华丽外衣下的满目疮痍。他们越是离经叛道,就越被社会所排挤,现实生活的庸俗、肮脏,与理想的纯粹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极端,吸毒、暴力、滥交成为暂时逃离压力的麻醉品。
三、叛逃后的人物组合
逃离父权中心的主人公往往融合进社会中的某个性格群体中,其中存在形形色色的人。以群体式的生存模式,来加强个体的信心和力量,营造归属感。在这种群体中,人物性格一般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冲突型、对比型、映衬型。在作为精神丰碑的父亲形象失去光彩之后,子辈以脱离父辈控制管束的形式,进入了社会。这些弱小的单体,自然而然地结合成小群体,依赖群体意志来增强自信。
冲突型人物与主人公观念不同,实际行动发生碰撞和冲突,成为在社会中碰到的阻碍力量,常作为某种社会权力出现,对主人公的生活构成紧逼和压迫,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父权。《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刘忆苦是小团体中的权力中心,他可以决定这个团体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并对马小军的青春性幻想构成阻碍。《小武》《任逍遥》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形象,暴富的人用金钱和暴力压迫这些边缘青年,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不幸。《小武》中以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来描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宽宽的街道上,一面是林立的崭新楼房,另一面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部分人的富裕生活是建立在对这些底层青年的压榨和盘剥上,却以掠夺来的财富侮辱、排挤他们。
对比型人物与主人公观念不同,实际行动却不相冲突,平行发展。与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形成叛逃与回归的鲜明对比。《麻将》中的红鱼与伦伦就形成了这样的对比,红鱼抛弃良心和道德疯狂敛财,最后愤而弑父,成了杀人犯-伦伦则艰难地固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即使被社会讥笑,被小团体抛弃也在所不惜,最后他收获了爱情。对“原乡”文化的态度导致同一团体中两人的分歧,走上不同的道路,演绎不同的命运。这种强有力的对比,让红鱼结尾对于“原乡”文化的呼唤显得真实可信,富有感染力。
映衬型人物与主人公观念相同,作为群体相互映衬,通过类似人物聚合成群体性形象,将个体的“弑父”行为拓展为一代人集体的“弑父”行为。将个体生命体验置换成群体生命体验,形成一代人的社会遭遇,他们有共同的渴望、沿着逃脱家庭的路走向共同的命运。在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意味深重的符号性映衬者,《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骑着棍子的傻子,他是一个不存在自我意识的个体,他所呈现的完全是社会的父权意志留下的时代烙印,他的成长与马小军们的成长保持着一致的步调。在神化政治父权的时代,小军们与傻子的交流是革命话语的暗号:“古伦木”和“欧巴”。当精神偶像幻灭后,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共聚一堂再试图以革命话语与傻子交流时。这种交流中断了,遭到了傻子的拒绝,傻子换了一句时髦的京骂,主流意志的改变导致社会话语体系的改变,傻子和他们一样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