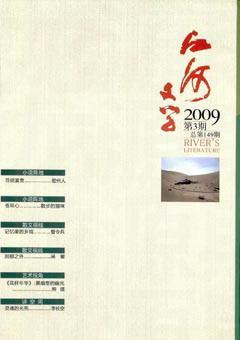《花样年华》:黑暗里的幽光
熊 瑛
同陈凯歌总试图通过电影表现其思辩性一样,王家卫通过他的影像世界向着大众不厌其烦地述说着他的末世情怀,有些絮絮叨叨、有些光怪陆离,有些锋芒毕露。当你一次又一次地被他那同一情感主题的电影牵着鼻子走时,也许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你竟然会爱着这样的电影,如同爱着自己那充满隐私和谎言的人生。
王家卫,这位五十年代出生的独行侠式的导演,是“后现代”文化氛围下孕育出的电影奇才,也是“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中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2000年,他裹挟着影片《花样年华》,一举夺得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特别技术奖和最佳男主角奖两项大奖,为起步甚晚的华语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也许王家卫极其个人色彩的艺术追求,正暗合了电影理念最为完美的法国电影界人士的审美情趣。
叙事结构——王氏破碎与断裂
片头字幕:那是一种难堪的相对,她一直低着头,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他没有勇气接近,她掉转身,走了。(一九六二年香港)
电影是时空的艺术,它通常会以空间的变化来表现时间的流逝,或以时间的变动来展现空间的起伏。传统电影中时间、空间两条线基本保持平行同步、因果互动;而在王家卫的电影中,试图对其故事的整体脉络条分缕析几乎是不可能的。破碎的、大团块的片段代替了经典模式中的线型结构。影片《花样年华》只是讲述了一个婚外恋之后的婚外恋的老套故事,但由于王氏独特的叙述方式和镜头语言,观众便常常会感到被突然剥离了周围世界而与片中主人公孤独相对。不觉传染上了一种焦躁不安和无奈的阴郁情绪。
无论是现代都市中的边缘人(1988年《旺角卡门》、1991年《阿飞正传》、1995年《堕落天使》、1997年《春光乍泄》),还是古代的大侠(1994年《东邪西毒》),亦或是六十年代旧香港的小职员(2000年《花样年华》)……虽然场景、演员的服饰不断变换。悲喜哀乐也轮了几回,可明眼人透过繁华幕布中的灯火明灭,只看到了同一幕拒绝与被拒绝、出逃和寻找的情感故事。在通过王氏叙事手法来表现的婚外恋这一事件里,能造成鲜明节奏的同样是事件本身细微可见的运动。如苏丽珍婀娜多姿的步态、欲言又止的犹疑眼神、缠绕周慕云的袅袅烟雾以及他那如同黑芝麻糊般含混不清的笑容……这些琐碎的细节抓取,将蕴藏在普通家庭里种种微小的悲剧在银幕上放大为殊死的斗争。以情感为序,探究人物心灵最隐秘的东西,这正是王氏叙事手法的惯用招式:时问的缓缓流逝与现实的短暂破碎形成奇怪的对立统一。
王家卫热爱着在深巷里弄徘徊的那些孤独的夜行人。他熟悉他们无根的漂泊、无望的等待、无法交流的茫然和自恋情结下的悲哀。他急于要替他们诉说、急于更多地表达,结果通常拍一部电影只需8万英尺的胶片。他往往需要耗费多达20万英尺。导演兼编剧的王家卫,常常会设想出同一事件的多种可能性。在《花样年华》的拍摄过程中,他按照一般言情剧惯例拍摄了大量的缠绵床上戏,可最终,这位眼光独到的电影人将全片干脆删剪得连一个吻也不剩。任意构思和巨幅删剪必然造成了王氏电影结构的零散破碎(这使得他在多部影片中不得不用旁白来连接剧情)。然而,这种人为的破碎状态,似乎也正营造出了都市人和都市生活的彷徨失所、残缺不全。
可以说,王家卫、杜可凡(摄影)和张叔平(美工)的“铁三角”组合,演绎出了王氏电影的奇美独秀;然而,从电影叙事结构上来看,这种组合又是危险的。因为,过分完美的构图和剪接节奏的和谐很可能赋予片断画面一种静水深流的美,从而也就使它们脱离开汹涌前进的动作的巨流而孤立存在。断裂便从此产生。在影片《花样年华》中也处处可见这样的尴尬:当你正沉浸在苏丽珍款款的步履及绵绵细雨中时,突然撞入耳畔的对白便显得十分刺耳:当苏丽珍多年后重返故居,舍泪凝望窗外的藤萝蔓生时,相信许多观众都会以为影片已经落幕了,可突然又跳出个毫不相干的“一九六六年柬埔寨”,虽然这段选在“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吴哥窟”拍摄出的结尾意蕴隽永。可观众似乎已经丧失了观赏的耐性。
转场中的断裂,是王氏电影的特色。但我个人以为也是一种缺憾。
拍摄构图——黑暗里的幽光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布满了虱子。
无独有偶。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在他的许多著名画作中都出现了蚂蚁成堆的形象。(如《一个女人的回顾胸像》,无数只蚂蚁赫然聚集在一个眉清目秀的古典女性的前额上)
浮华中的诡异,宁静外表下一触即发的狂躁,这也正是王家卫电影中摄影构图的特质。《花样年华》片中,王家卫在色彩灯光、摄影角度和手法上又有了新的尝试。《花样年华》影片以冷调为主,大面积的黑色调几乎占据了所有篇幅,一盏幽幽的台灯或是晕黄的路灯便可作为光源将影像凸现出来;而人物也采用了大量的侧光、侧逆光或逆光拍摄,造成强烈的明暗反差,更形成一种独特的剪影效果。片中来来往往的人物仿若深夜里不安的精灵,在黑暗的无边巨网里行走、碰壁、崩溃、萎靡,影影绰绰。在片中唯一令人惊鸿一瞥的是:周慕云客居的旅馆中垂挂的大红帷幔,那样鲜红、妖娆、逼人入眼,好似热带雨林中的食人植物。这个本该是暖调温馨的场景,在王家卫的蓄意制造下,反而在惊扰观众视觉的同时更增添了阴冷孤寂的氛围,它似乎喻示了周苏两人之间的情感也必将无疾而终。
在电影中,再没有比摄影机镜头更主观的东西了。王家卫总是会让摄影机参与表演,以它的视角去窥探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花样年华》片中,杜可凡的摄影机终于“改邪归正”。抛弃了以往王氏电影中摇晃喧哗。而以一种平静审视的态度,用大量平移的镜头运动方式来讲述一个怀旧故事。配合着拉丁舞曲的慵懒舒缓,慢镜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略带贵族颓废气息的粱朝伟和云鬓高耸极具风尘感的张曼玉,就这样错失在漫漫的时间之河。
在摄影构图中前景的设置,似乎也让王导大费周折。片中周慕云的妻子周太太从未正面出镜,每次出现她的背影时,为了避免构图的单调,王家卫会用一个椭圆形的前景来衬托,摄影机这时仿佛一只偷窥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女人的隐私。在周苏两人感情发展到最激烈的两难处境时,有一个平移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在周璇演唱的《花样年华》的乐曲声中。镜头先由收音机移到周再移到一堵墙,然后是苏,再由苏摇到墙,最后回到周身上,这个平移的速度出奇得缓慢,尤其是那堵厚厚的墙已经令画面出现了完全的黑场。这样设计绝妙的构图非王家卫而不能也!那墙,是如此令人窒息的沉重,正如同两人咫尺天涯的喟叹。在影片结束的一场戏中,周慕云在吴哥窟的一棵树身上掩埋了自己的秘密。这里又有一个平移镜头,令人玄思不已:镜头从断壁残垣摇到了一个僧侣的后脑勺,僧侣的头成为镜头前景,且久久停留。他在想什么?注视着这个凡夫俗子凝重的背影,他或者自问:佛祖真能超脱人世间一切
的大悲大痛?或心酸?或怜惜?或漠然?……王家卫把这些疑惑留给了屏幕前的万千观众。
无声独白——潜藏的诗意
片尾字幕: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花样年华》影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调动了一切默片时期的积极的表现元素;似乎在这部影片中观众并非借助语言来思想;倘若去除一切声音元素,我想绝大多数观众还是能借助画面而明白全片的内容。
在王家卫的历部影片中,人物的语言表达与内在欲望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为了深化编导者意图,常常会采取画外音独白的方式来延伸剧情。而《花样年华》影片脱离了以往模式的窠臼,取消声音文字的干扰,更着重于人物孤立的特写。通过演员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表现目光难以洞察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电影大师普多夫金在《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一文中,详尽描写了他如何利用他在演员身上刺激起来的那种不自觉的自然反应。来创造一种自觉的视觉效果的过程。王家卫便是这样一位卓越而感觉敏锐的导演,他极善于发挥演员的潜质,捕捉他们自己都未曾发觉的最本真的自我。于是有了粱朝伟的成熟内敛。张国荣的放浪不羁,张曼玉的楚楚动人,王菲的率真张扬……在《花样年华》片中,有这样一场戏:苏丽珍怀疑丈夫与周太太有染,于是借机扣开了隔壁周家的房门,接下来是一大段苏丽珍与周太太之间的对白。长长的对白时间里,画面上只出现了一个苏丽珍的面部特写,时而浅笑盈盈,时而欲言又止,时而星眸闪烁,时而沉思迷离……所有的表情都是浅浅淡淡、不易察觉的,但这张平静面容下压抑着焦虑不安、痛苦痴迷,深深地震撼着观者的心;一个怯弱、犹疑、温婉的旧式女子——苏丽珍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了。
在视觉艺术中,很少有哪一种肢体语言比走路更足以代表人物性格和更富表现力的,人物内在的情感动因往往会在这一不经意的动作中得以表白。在国内外多部优秀电影中,“走路”这一肢体动作均得到频频运用。例如美国电影片《阿甘正传》,阿甘通过他坚实有力的步伐表达着他对信念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如在默片《大马戏团》结尾时,表演大师卓别林孑然一身、摇摇摆摆走向天边,这个场景喻示着人物前途命运的艰辛坎坷、未可预卜。而在《花样年华》片中,主人公的步态更仿若一篇无声的独白,潜藏着柔肠百转的浓浓诗意。人物的尊严、决心、犹豫、谦虚或娇态在各自的步履中暴露无遗。相信看过《花样年华》影片的人,一定都会对苏丽珍提着保温桶行走在深巷中的情景记忆犹新。高耸的衣领、狐媚的腰身、窄窄的裙摆、尖细的高跟鞋,在凄绝的关感中传达出这个旧式妇女没落失意、彷徨孤苦的心境。“出去买碗面也要打扮得那么漂亮!”其实,光鲜亮丽的外表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虚弱,在百般无奈间又存了一份对爱情的朦胧期盼:在这个日日复日日的小巷里,或许又能与“那个人”擦肩而过罢……
纵然年华如花,终究是“春去也,飞红万点如海”……王家卫说:“当一份感情已不能够再拥有,唯一能做的便是令自己不要忘记。”(《东邪西毒》)一部《花样年华》,令少不更事的青年人在黑暗中困惑不已:同样一部《花样年华》,令历经风雨的过来人透过黑暗里的幽光,窥见流水落花、春梦无痕。得以会心一叹。
责任编辑:吴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