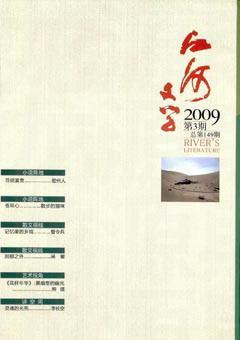悟
曹世忠
月朗星稀。
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温馨、静谧、宁静的夜色之中。
“娘呀。非气死我不中……”忽然,村东的街头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声。“半夜三更的,你也不怕邻居笑话。回去吧!”男人粗而嘶哑的嗓子里。分明裹着一种乞求哀怜的味道。
翠玲今年四十八九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男人开一辆货车,每月大把大把的钱往家流;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舒心称心。月亮再圆,也有残缺的时候。前天儿子打电话说要五千和同学到桂林旅游,她还没说钱不凑手,那边就扔过来一句生硬的话:“嫌花钱,咋不小时候把我一下子给溺死?”
翠玲睡在床上,两天不吃,不喝。见了男人,一肚子的委屈就喷薄而出:“我整天像驴马一样干活。把一颗心都扒给孩子,落了个啥?他一口气光想气死你!”
“嗨,想开点。你说,养这这不争气孩子、败家子孩子、丢人贼孩子,有啥法?”男人以为自己是贴心贴肺向着女人的,谁知她却把被子蒙得更加严实,被角的颤动里传出伤心的啜泣声……
一夜夫妻百夜亲。有一回,俩人拌了嘴,他气得不吃饭,翠玲就在一边数落孩子:“你该咋吃还咋吃,那死人就没一点好处,把他一下饿死也不亏。”说听话音,锣鼓听声。女儿就连忙给他端饭,一口一个爸,再大的火也熄了。想起这件事,男人胸中就涌起一股热浪,一直溢到喉咙。
此时,见女人如此痛苦,男人便把千仇万恨一下子集中到儿子身上,咬牙切齿地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明儿我去找他,再犟,看我剥不了他的皮!”
女人又嚎啕大哭起来了:“你怕我一口气气不死不是?把我气死了,你可再娶个年轻的,过好日子。”
猛然间,男人的火一下子燃上来了,气呼呼地说:“你死!随你的便!”
“我这就去,也好离离你的眼!”女人掀开被子,三下两下穿上鞋,就从屋里往外跑。
女人是刚烈性子,脾气上来了就不管不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咋说?男人急忙撵过去拉住她。
“你别管我!我走。也解解你的心头之恨。”僵持在屋门前的女人,头发凌乱着,泪水像泉眼一样往外涌……
男人想了一夜,弄不清女人为啥发那么大的火?解铃还须系铃人。第二天他只好找着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要是把你妈气着,叫你哭天抹泪都来不及。去,给你妈赔赔不是。”
儿子回了家,坐在床边说:“妈,我不懂事,别跟我一般见识。”
女人依然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儿子就打“持久战”。女人的心就软了,说:“这回不跟你一般见识,下次再这样,我非买包老鼠药不中!”
他问:“这次饶你,听见没有?”
儿子说:“听见了,妈,以后我不再气你了……”
过了两天,男人碰见了对门的花嫂,花嫂半开玩笑地问:“你们两口子那晚到底唱的啥戏呀?热热闹闹的。”
男人开始不肯说,后来就说了。
花嫂说:“孩子是人家身上掉下的肉。知道吗?”
“我又没说不是呀?”男人一脸诧异的神情。
“那你又是剥皮,又是抽筋,换上我也得和你拼命干。”
“我可是一心为她好呀,咋好心换个驴肝肺!”男人依然一头雾水。
“死脑壳!屎壳郎还夸他孩香,知道吗?”花嫂哈哈大笑,直笑得花枝乱颤,“你呀,得把女人这本书好好咀嚼一下,才读得出里面的味道哩。”
男人的眼前忽然一亮!
责任编辑:吴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