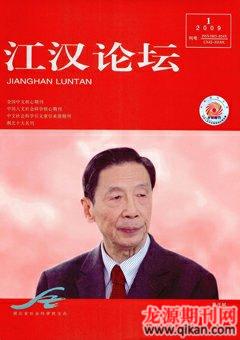从天狗到骆驼
白 浩
摘要:以郭沫若为代表,20世纪新诗以“天狗”的雄姿确立了自我主体,并开创出白话自由诗的形式,宣告新诗现代性的获得。中历“水牛”意象过渡,后来诗人转向颂扬“骆驼”精神,自我主体丧失,“我”让位于“我们”,自由体转向于古诗体、民歌体,并产生失语症与大话癖等时代症,新诗从诗魂到诗艺都从现代性向古典复归。
关键词:天狗;骆驼;诗歌精神;诗艺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1-0099-05
尽管胡适率先以白话文“尝试”为诗,但真正使新诗获得现代性起点的仍归于郭沫若,原因即在他以“天狗”的雄姿宣告了崭新现代精神的奠定。“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闻一多敏锐地指出,“郭沫若底这种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①。郭沫若诗歌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一方面是在文学本体建设意义上的(诗艺),一方面是在精神本体建设意义上的(诗魂)。这个诗魂,这个现代精神的核心,正是独立的自我主体的确立。郭沫若为20世纪大写的“我”字作出天狗式的标注,标志着20世纪新诗现代性的获得。
然而,随着革命文学“甘作党喇叭”的皈依,再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规范,“天狗”转向了歌颂“水牛”,而在建国后,则变为了“骆驼”。郭沫若确是时代精神的敏感者和引领者,从“天狗”到“骆驼”既是时代精神的变迁,同时对于20世纪新诗来说,正是其现代性诗魂、诗艺从获得到失落的标志。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开篇便谈到了超人诞生的三种形态:“我向你们说精神的三种变形:怎样精神变为一匹骆驼,骆驼变为一头狮子,最后狮子变为一个赤子。”② 如果把“天狗”视为“狮子”的类比物,那么,中国新诗精神的发展正好是一个逆序的发展过程。唐晓渡曾谈到“时间神话”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支配。在时间神话、“新纪元意识”支配下,诗人们不断地“彻底决裂”,走向革命,理直气壮而又急迫地走向“未来”,“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也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③,然而在时间神话的掩盖下,诗歌精神却正是从“天狗”走向“骆驼”的逆序行进。
一
尽管杜甫是郭沫若所不喜欢的诗人,但最早塑造了“天狗”形象的却是杜甫,在其《天狗赋》中,“天狗”乃是“猛健无与比”的西域异犬。杜之“天狗”乃是列于天子“华清兽坊”中,以“时驻君之玉辇兮,近奉君之渥欢”为志,而它所苦者在于“顾同侪之甚少兮,混非类以摧残。偶快意于校猎兮,尤见疑于矫捷”,由此,方可明白,杜甫之“天狗赋”不过是又一篇长门赋而已,而其意仍在自命异材,不过是典型封建文化秩序下骆驼文化秩序下依附人格的奴仆之志而已。而郭沫若之天狗,正是在从古典到现代文化意义上取得了爆破。通篇29句全部以“我”字开头,通篇是大写“我”的狂暴呼叫,是欲望与激情的磅礴。这个“我”,吞噬一切日月星球,是全宇宙Energy底总量,“天狗”狂放不羁,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正是尼采所谓“狮子”的精神,“这精神变为一头狮子;它这个“我”身份的获得,实在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中是没有独立个体“我”的位置的,所有的只是在各种整体性关联中的附属个体,人只有依附于各种整体关系时才有了存在的意义,诸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而人的自称也少有“我”,而多为“臣”、“妾”、“下官”、“草民”、“学生”、“奴”、“仆”等等。传统文化秩序铸造的正是种种依附人格,取消了人的自我主体性。而在此背景下,“五四”时代“我”的自我人格确认便具有了开天辟地的意义,由此具有了人的存在合理性、价值关怀、人道主义、理性精神等等现代性命题的起点和支点:“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④
为了冲破封建文化秩序的重重捆缚,“自我”以“摩罗”式的姿态展开了“个性张”、“绝义务”的破坏与建设,而郭沫若正是中国第一个为鲁迅所呼唤的“摩罗诗人”:“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其文化上的震撼意义不亚于人的第二次直立行走,从此匍伏在地的人直立为顶天立地、独立不倚、天赋人权的大写人。“我是我自己的”,娜拉、子君的意义都在于一个“我”字的确证。在传统文化中作为宾词的“我”从此成为了现代文化中的主语。“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其意义正在于“自我”的正式确立。与之相关的是它所带来的狮子文化的美学特征及语言方式。在美学特征上,“相对于骆驼的坚韧,狮子文化注重于人性的雄壮。狮子文化总是那么的理想主义,总是那么的英雄主义”;在语言特征上,狮子语言的特点在于批判,骆驼语言以注疏见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阶级与种族斗争扫荡一切的时候,这种现代性的支撑却是脆弱的。随着“五四”的落潮,大革命的失败,感伤主义代之而起,“自我”被从两个方面加以消解,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对“自我”的质疑;一方面是革命文学再度将“自我”抛弃与奴役。浪漫主义的热烈激情代之为感伤主义的低沉颓废,而现代主义的自我怀疑与否定,放逐激情,对荒诞、虚无的体悟等,如果说乃是以反面的形式对“自我”伤痛的抚慰,仍属对“自我”价值的变相肯定的话(这也正是它后来受到延安批判的原因),那么革命文学则是毫不犹豫地要将“自我”之根拔起,让文学再度成为“革命”的婢女,郭沫若便毫不犹豫地宣称要做个“党喇叭”,对个人主义痛加贬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是一个方向性转换的标志。在将文学定位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军队后,《讲话》最后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进行了误读与颠覆,并要求以此为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此,鲁迅充满人道关怀的爱与憎被颠覆为阶级论下的服从与战斗,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武器,而“自我”,也在被作为个人主义批判和打击后,重新成为阶级和集团的奴仆。“牛”随之在40年代成为郭诗中的主角,“牛”的忍耐与牺牲成为提倡的新的时代精神,“牛”也成为从天狗到骆驼间的过渡。“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坚毅、雄浑、无私,/拓大、悠闲、和蔼,/任是怎样的辛劳/你都能够忍耐”(《水牛赞》)。另一首《题水牛画册》说得更明白:“任劳兼任怨,/努力事耕耘。/谁解牺牲意,/还当问此君。”这样的牛,正是尼采所谓“骆驼”精神的典范代表。而到50年代,郭沫若称其《骆驼》“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诗,因而将诗集也名之为《骆驼集》”⑤。尽管也有人对《骆驼》一诗解作对共产党的歌颂,但从郭沫若的喜爱来看,骆驼正是他心中的寄托意象。这之间的巧合正如《骆驼祥子》一开始即声明的“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一样,祥子与骆驼间的交道仅只一夜工夫,但因为与骆驼的吃苦耐劳实在相类,所以“祥子”从此就铁定永远成了“骆驼祥子”。从牛到骆驼,实在是方便的过渡,其坚韧、驯顺、忠诚正是一脉相承。但这里有些滑稽的是,《骆驼祥子》以“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结语意在宣告骆驼精神的没落,而郭沫若的《骆驼》则又在新的文化背景下重拾骆驼精神。
骆驼意象在现代文学中并不是个罕见的意象,尽管它本身并不熟见,但它的坚韧耐劳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周作人在20年代即组织骆驼社,并先后办出《骆驼》、《骆驼草》周刊,提倡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尽管周作人意在以坚忍的苦药医轻躁的时疫,但作为骆驼精神,周作人、老舍、郭沫若都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归。艾青的《骆驼》,郭小川的《骆驼商人挽歌》,公刘《致园丁(二)》也都同样是对这种骆驼精神的表现。
在尼采看来,骆驼正是精神的第一种变形,它代表着“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它信奉的正是“你当”的信条。骆驼精神正是放弃“自我”,而服从于种种外在指令“你当”。“负重的精神负载了这些最终的重负:如同骆驼负着重载,向着沙漠奔走,精神也向着它自己的沙漠奔走。”⑥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骆驼及骆驼文化命运前景的表现,臧克家名作《老马》更为明确:“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精神的骆驼必要变为精神的狮子,方才有前路,这正是尼采超人诞生的必由之路,也正是由古典文化向现代性文化转换的关键点。然而,从精神天狗到精神骆驼,却正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及整个文学的现代性精神获得而又再度失落的逆序行进。
天狗复归于骆驼,最显著的变化便是“我”让位于“我们”。“如果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骑士们在一定的时代唱过浪漫主义的动听的歌的话,那么,到了我们的时代,个人主义者的歌声就只能是鬼哭狼嚎了”⑦,贺敬之说,“问题在于,是艾青的个人主义的‘我,还是集体主义的‘我、社会主义的‘我、忘我的‘我?……或者是个人主义的小丑,或者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⑧。与《天狗》的以“我”为主语相异,解放后诗歌中,以类似的巨幅排比方式,“我们”成为主语,成为涵盖一切的发言主体,“我们/以死难烈士的名义,/我们/以革命将士的名义,/我们/以全体共产党员的名义,/我们/以六亿人民的名义”(郭小川《保卫我们的党》)。面对这样专制整体的“我们”,如果偶尔还有“我”的位置的话,那么,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以“我”的渺小来衬托“我们”的高大,“在一个雨夜的行军的路上,/我慌张地跑到/最初接待我的将军的面前,/诉说了/我的烦恼和不安”(《向困难进军》);另一种情况则是“我”作为宾词出现,即作为改造的对象出现。这两种情况的统一在于因为作为主词“我”的渺小,所以“我”成为了改造对象的宾词,而改造的结果则是“我”融入了“我们”,即“我”转换为“我们”。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鲜明地展现了这种“我”与“我们”的关系:“呵,/‘我,/是谁?/我呵,/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里的/一颗小小的谷粒……/——我呵,/一个人/有什么/意义?”⑨即便难得保持了个人思考,并因此而被批判为“个人主义”的郭小川诗歌《望星空》中,其自我定位和力量之源也最终走向“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当“我”放弃“我”的独立主体定义,而采用依附性定义时,“我”便获得以“我们”名义的发言权,可以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身份发言,可以谈“我们的/钢铁”“我们的/五年计划”,等等。这里,自我主体的天狗成为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骆驼,而作为整体的“我们”则成为了天狗、狮子,以专横的语式扫荡一切,统治一切,摧毁一切。继承了郭沫若《天狗》语式的是以“我们”发言的贺敬之、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而这种语式发展的最极端则是文革造反派语,任何一个革命小将都可以用“我们”来蹂躏任何一个“我”。“中国人在1966年害怕‘我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是一次从‘我向‘们的大逃亡。一切具有‘我这种特征的事物都成为罪恶的同义词。都要被‘我们消灭掉。反之,只要是‘我们,就一切都可以干,一切都不用害怕。是我们而不是法律提供了人的最基本的安全感。……我们是一个时代的权力主语中最核心的主语,统治者也必须服从这个主语”⑩。
“五四”时代获得的“我”的主体性既意味着人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人的责任的担当,鲁迅“我也是吃人的人”对个体罪的反省正是中国现代文化中“人的忏悔”的开端。而在“我”的主体性丢失后,对为恶的文化担当责任感、自罪自省意识也自然流失。“许多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喜欢用‘我们来代替当事人‘我。越是在回忆所谓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时,越是用‘我们。我听过一些人讲述1966年的造反,在讲到如何迫害老师的细节时,用的都是‘我们。‘我们那时……‘我们当时……。我们成为实施一切和开脱一切的最有力的借口。任何事,只要冠以我们就名正言顺,干起来就有了正义感、道德感”{11}。正因为如此,80年代耄耋老人巴金的《随想录》重新忏悔自我的罪时,才会令人们如此震惊和羞愧。
从“我”到“我们”,从天狗、狮子到骆驼,从现代性的获得到沦丧,从对古典文化的反叛到复归,尽管是一个惊人的文化逆序流动,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却显得如此自然,大批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和捍卫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这里的关键即在于曼海姆所谓的乌托邦的诱惑变换成了意识形态的现实。当民族解放、人类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诱惑着人们时,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权利,奉献出“我”的称号,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屈从于权力而是屈从于信仰的召唤。而当乌托邦幻想转换为意识形态现实时,权力与信仰的结盟更强化和巩固着这种趋势,服从于信仰的是主动奉献,屈从于权力的则是被剥夺。政教合一的优势在于,权力以信仰的名义行使权力,而信仰则是权力基础上无可选择的信仰。信仰是权利,然而权力则排斥权利,所以这时信仰不再是权利,而成为义务、责任。无论怎样,文化的逆序而动成为现实。
二
《女神》不仅在诗魂上确立了新诗的现代性,而且在诗艺上也同样开创了白话自由体诗的新形式。它破除了古典诗体格律的严格束缚,而代之以自由灵活、奔放的形式,以感情的内在律替代了形式的外在律。对郭沫若来说,节奏成为组织诗形的关键,它既是内在感情流动的纽带,同时也是外在诗句长短形式的组织纽带。有了自我主体性的诗魂,感情流淌的内在律,加之节奏的外在律,郭沫若便形神俱备。然而,随着自我主体性诗魂的丧失,内在的激情亦趋枯竭,由是而带来外在诗形的变化也就显而易见。最显著的变化是日益从自由诗转向古体诗、民歌歌谣体诗的创作。这是从“乱写”日益转向规范,从无韵体转向新格律体,从无序的创造转向秩序的依靠和墨守。当内在律丧失后,自由诗已难以为续,郭沫若只有乞灵于格律体的外在律为拐杖来组织诗形。如果说当初以内容大于形式的创造而开辟出新的形式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依靠形式来掩盖内容的空洞,同时,郭沫若的表达功能也患上了两种典型的时代症:失语症与大词癖。失语乃是因为自我主体性被剥夺后情感枯竭下的无话可说,以及意识形态下的有话也不能说;而大词癖则是在“自我”发言权被剥夺后,虚假发言主体“我们”的狂躁与虚热,它将一切大词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但一切都不是“我”的话,而是“他们”的话,是人人可说的程式化、简单化、机械化,进入的是一整套话语自动流水线。如朱自清分析所说:“今天的诗是以朗诵为主调的”,“‘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这个‘我只是‘我们的代言人”{12}。失语症的生命萎缩只有借助于格律的外在形式来遮掩,而大词癖的外强中干则同样是失语中的呓语烧症,它们所共同掩盖的都是内在创造性的枯竭。当诗魂由天狗走向骆驼,那么诗艺也只有抛弃天狗的现代性形式,而复归于骆驼的古典化。《女神》以非理性的情感姿态和放浪形骸的诗形来获得自我价值关怀的理性精神,而复归于格律体则是以理性的外在律来遮掩自我主体沦丧的非理性境遇;大词癖则干脆是以非理性语和政治术语借用来表达话语与精神专制下的非理性臆狂。依靠这种话语生产流水线,郭沫若在建国后仍然高效率地生产出了诸如《百花齐放》式的诗歌,尽管他早就声称《女神》之后“就不再是诗人了”{13},但流水线的自我生产能力却仍能产出“诗歌大跃进”的虚假繁荣。
民歌体似乎是一个可供摆脱困境的选择。它因为其民间特性的暧昧性与多元杂生性而成为郭沫若及新诗自救的一个出口。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来自于工农大众,符合“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口号;从创作方法来说,民歌“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为主流与个体的发挥都容纳了空间;而从诗形来说,它既是白话的自由体,同时也是有韵的格律体。故而民歌体成为新诗在庙堂充满失语与大词癖时转向民间以获生机的一个暧昧承载物,它是唯一既是“我们”的,同时也以“我”的个体身份发言的地方。如在一首民歌中出现的“我”:“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周扬对此分析道,“这个‘我,自然不是‘小我,而是‘大我,是集体农民的总称,所以才有那样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14}。由此可见当时民歌中普遍的“我”与“我们”的二位一体关系,甚至在当时的一些爱情诗民歌中也是如此。郭沫若断言“在这里似乎显示着新诗歌的一个方向”{15}。郭沫若与周扬精选《红旗歌谣》三百首,“‘三百这个数字是有历史性的,《诗经三百篇》,《唐诗三百首》,都是三百”{16}。这可见其对民歌带来新诗里程碑式发展的自期。郭沫若热烈地“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新“国风”指由民间采风而得的民间创作,而新“楚辞”则是职业作家、诗人们(即当时犯忌的“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的创造。“从新‘国风中充分摄取养料,体会人民的生活,学习人民的技巧而加以发扬光大,这就为职业的作家和诗人们开辟了极广阔的天地。像《楚辞》是在《国风》的基础之上创化出来的那样,新时代将会有从新‘国风基础上创化出来的新‘楚辞”{17}。
作为现代新诗的奠基人,自己的自由诗创作生命却已走向末路,郭沫若一方面仍不时为新诗的存在合理性作些辩护,另一方面也在摸索新诗生命力的出口:“五四以来的新诗人应该很好的学习新民歌,同时把旧体诗词琢磨一番,使自己的诗更合乎中国的习惯和更适合中国语言的性质。”{18}但不管怎样,这些都只能是骆驼式的反刍,而不再是天狗式的吞吐与创造。中国新诗从天狗到骆驼,从中兴到末路的变迁史,从现代性诗魂、诗艺的获得到沦丧到复归古典,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的论断。面对复辟,中国诗与人都陷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困顿之中。
逆序的流动毕竟不能长久,当文革将这种复古倾向演至逻辑的荒唐极至时,必然走向自我否定,新诗的骆驼重向狮子精神变形。新时期美学精神中,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率先发出了重获自我主体性的呼唤”{19},而第三代诗人们则以个体我的生命体验来宣称“我们正在重建诗歌精神”{20}。他们以“自虐的、反讽的、黑色幽默式的、陌生化的”诗风、“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而被视为先锋派{21},老诗人公刘这位熟悉骆驼的边塞诗人,在50年代《运杨柳的骆驼》中对新时代充满憧憬与颂扬的诗人,在80年代初《骆驼》诗中也发出了人道与自我主体的复苏之芽:“我终于恢复了人的感觉了,而且准备反抗!”新诗的重获现代性意味着重获生机。
当我们将前述这种新诗精神从天狗到骆驼的变迁作为一个独立时间截片来看的话,很难不得出悲观和痛心的复辟、倒退结论;但是,当置于更为宏阔的时空视野来看,那么,天狗的出现本身是对古典文化的否定,而新时期诗歌精神又是对20世纪新的政治文化统属下之骆驼文化的否定,这是文化精神发展中相承续的两个周期,天狗的出现是第一个周期末的曙光,而天狗到骆驼则是第二个周期开始时的黑暗,它虽然以复辟的方式出现,但它也孕育和催生着自我否定的可能性,它很快便开始了新一个周期下狮子精神的诞生。认清这样的复辟周期是对所谓“时间神话”线性发展观狂热的清凉剂,提醒我们保持对新的乍暖还寒的警惕。当然,所谓复辟周期同时也正是新的发展周期,如果说上一个周期的否定之否定历经上千年时间,那么这新一个周期的否定之否定则缩短到几十年时间,这里正可见出历史发展的螺旋性与上升性。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复辟周期是否仍会存在和又将以怎样的形态存在。
注释:
①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黄人影编《郭沫若论》,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95-97页。
②⑥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尼采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0页。
③ 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李复威编选《世纪之交文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④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
⑤ 郭沫若:《骆驼集·前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⑦⑧ 贺敬之:《漫谈诗的浪漫主义》,《文艺报》1958年第9期。
⑨ 贺敬之:《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6-67页。
⑩{11} 于坚:《棕皮手记·1996》,《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32页。
{12} 朱自清:《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文讯(上海)》第8卷第5期。
{13} 郭沫若:《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14}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15} 郭沫若:《〈大跃进之歌〉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16} 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页。
{17} 郭沫若:《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18} 郭沫若:《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19}{20}{21}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4、105页。
作者简介:白浩,男,1973年生,四川旺苍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8;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四川成都,610064。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