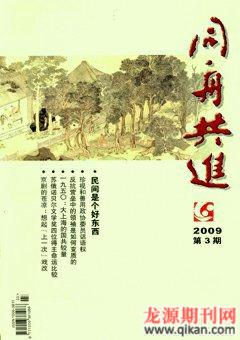文明的道路:“礼失求诸野”
余世存
作者简介 文史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有《非常道》、《重建生活》等著作。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近两百年。初期的应战,几乎且战且退,从技术、制度到文化等领域,我们的传统在人家的现代化面前一败涂地。经过惨烈的国内外战争、改良、改革、革命、动乱、乱动等社会形态,我们最终确立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只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仍处于探索之中。今天,最近一轮现代化改革也已30年——我们的现代化道路通往何方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传统社会对礼乐崩坏的应对很简单——“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这样的圣贤都明白,在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要从民众那里获得变革的基础,从民间获得创新礼乐的灵感,以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是最简单也最伟大的思想。
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性的现代化。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快地复制出一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但它的负面因素在于,后发现代化难有积累,思想相互攻伐,迟迟不能进入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呈现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更为关键的是后发现代化最容易把民众当工具。因此,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精英们与民众日益拉大距离:他们的思想是发达国家的思想,有一种近乎媚时的观念崇拜;他们对民间社会的态度情绪化,一会儿无限地仰望,一会儿无限地蔑视;他们对民间避而远之,甚至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会了如何教训民众。
起第一代启蒙思想家于地下,他们会对当代社会的戏剧性现象目瞪口呆。
在我们的民众之间、官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价值似乎已是奢侈品,甚至已被废弃,许多东西都以势利、价格来衡量了——不要只说官员腐败,官腐民败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的社会规则。
“礼失而求诸野”,这样一句古老的圣言在今天有着更新鲜的含义。
跟传统文明中民间乡野保存并发展着传统的礼乐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诸野”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一种文明的反哺。
今天的“求诸野”并非经济学意义的财政转移支付,或单纯政治学意义上的藏富于民,而是一种文明品质。从生生之为大德、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到“明德、新民、至善”,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说明还权于民、启智于民、藏富于民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至上标准。
今天的“求诸野”更非对自然的予取予夺。不是打着保护环境的名义,将草地铲去再种上整齐划一、听话如茵的小草;不是借口绿化指标,就将世代居住的家园“拆了”,把原地变成所谓的现代公园……
“礼失而求诸野”,自然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文明意义。
因为我们失掉的不仅是简单的生活生存礼仪,在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方面,我们完全被流行或凑合主导了。我们也失掉了最为基本的交往沟通规则,至今还未能产生理想的文明关系及其制度。尤其是后者,使得众多国民生活得飘忽不安,甚至不无忧惧。
我们的成就和危机同样引人注目,如何摆脱这种格局,就在于“拿来”文明并跟中国社会博弈出一种自家的礼仪制度——
“求诸野”并不限于民间,“拿来主义”也是它的固有内容。从商开始,甚至更早,华夏文明就不断学习、师法先进的有用的文明成就。胡服骑射、魏文帝南迁洛阳、宋儒援佛道入儒,都是“求诸野”的表现。这种拿来主义为孙文、黄兴、胡适、鲁迅等一代启蒙大家所明认。孙中山甚至从细节入手,希望“拿来”其他文明的规则制度以改进中国的会议效率。
他们的做法值得今人深思。在前贤的成就面前,那些全盘否定他人文明的论调同全盘肯定传统者一样,不过是在捣糨糊、拆烂污。固然,今天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发达国家经受着考验,但我们仍可以关注它们自我疗救的文明能力、制度优势。“礼失求诸野”,它们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仍是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