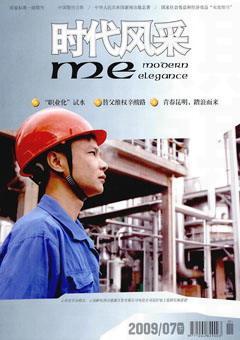不解之缘
熊 济
1960年11月,我奉命调入云南省总机关不久,受组织派遣和其他4位同志一道去白鱼口省工人疗养院农场劳动。6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全面困难的时期,社会物资匮乏,人们缺吃少穿,几乎是实行全额配给制。当时,汽油供应十分紧张,许多车辆改用煤气、天然气。昆明至白鱼口的公共汽车也被迫停运。我们一行5人步行整整一天到了白鱼口,我们的行李是由疗养农场的工人花了一天时间摇着小木船从滇池水路运送到白鱼口的。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们劳动的任务是在疗养院农场种植各种饲料、蔬菜,养奶牛、养猪、烤酒,管理苹果、板栗等果园,产品首先供应疗养员们的需要,劳动场地主要在疗养大楼前方,北至又一村,南到现今交通疗养院。这里山清水秀,疗养大楼面对浩瀚滇池水。那时的疗养院南北备有一幢配套建筑,是一座有500个床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规模疗养院。虽然是困难时期,疗养院依然住满了疗养员,医护职工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全院在一种宁静而不失生气的环境中过着紧张有序的生活。一个月的劳动经历,我对省工人疗养院有了初步的、感性的认识。
“文革”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省总生活部工作。生活部的职责之一是联系省工人疗养院和全省疗养事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每期(一般是三个月)疗养券由生活部发放到各地、市,各省级产业工会和大型厂矿企业,疗养员由各单位、组织派送,基本是公费医疗。疗养是对劳动者有效的身心关怀,让一般病患得到治疗康复,从而使他们身心愉悦、精神充沛地重返劳动工作岗位。人们常常把能到疗养院疗养当作一份光荣。
1994年2月,我奉调省工人疗养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这时的疗养院职工依然是那样朴实,自然环境依然是那样优美,但它却变得冷清多了。分析起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疗养院的房屋及设施已经显得陈旧了;二是由于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对疗养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疗养院有些萧条了,走入了它事业的低谷。在上级的指示下,我作为在任书记与院长,同院领导班子一起,主要的思考与工作着力点是:一、稳定职工思想,上下团结一致,尽力保住政策范围内的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二是调整疗养院部分功能,在保持疗养医技特色的同时适当转变,增加休闲度假、会议服务,开辟新的生产经营门路,调整了部分机构和体制,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三是积极主动争取客源,保住老客户,扩大新客源;四是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高接待中各个环节的服务质量,努力做到周到、细致,让客人满意。通过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职工思想是稳定的,各项业务工作是能够组织开展的,维持住了全院的基本经济开支,并小有建设,但整体局面还难以令人满意。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省工人疗养院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春天。1996年初,省政府决定改建省工人疗养院,它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抚慰着从事工人疗养事业的人们以及为疗养事业服务的工会干部们。在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省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省工人疗养院不断传来一个个喜讯。规模宏大的新疗养大楼建成了,又一村休养区装修了,道路平整了,院区环境更加优美了,疗养体检中心的设备更加充实和先进了,同时建盖了一批职工宿舍,可以说,疗养院焕然一新。与物质条件根本改观相适应的是,人员、机构、机制有了明显变化与提升,新的省工人疗养院有条件更好地为职工群众、为工运事业服务。
省工人疗养院改建之初,正值我在疗养院书记、院长任上,以及奉调返回省总机关在事业部任部长又继续为疗养院服务期间,我为疗养院起草了改建的规划报告,呈送省政府,并随省总几位领导跑省政府、省计委、省财政厅等部门,落实项目、资金,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省总领导为省工人疗养院的建设不遗余力,从项目立项、资金落实、基建监理、经营管理、环境建设、客源开拓等,都给予了全面的、有力的领导与帮助。
一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已和省工人疗养院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并为对它的工作有一份微薄贡献而深感喜悦和欣慰。
省工人疗养院的明天一定会蒸蒸日上,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