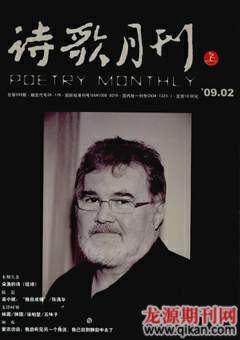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朵 渔
我突然觉得诗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就在敲下这个题目之前,我还在想为诗人的合法性辩护。也许“怀疑”的苗头早已深藏于我的内心,它随时会鬼魅般跳出来。我甚至觉得诗人的现实存在有了某种晦暗性,包括诗人的身份、手艺、精神、创造等等。读完老于长文《在喧嚣中沉默,自由派诗人的成熟》,这种感觉更甚。我必须对现代汉语诗人的身份危机做一番自我辩驳——对诗人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现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合法性问题进一步追问:你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你说你在创造,那么你到底创造了些什么?你有没有自知之明?
首先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写什么”和“如何写”的关系。于坚首先强调,“‘写什么几乎已经被历史穷尽。‘如何写才是无边无际的。”意思是天下无新事,今天的这枚月亮跟照在李白床前的那枚月亮没什么区别,端赖谁说得漂亮而已。这话并非毫无道理,从诗歌史的观念来看,真正的革命性的创造的确是从“如何写”开始的,每一次革新,即是创造一套新的语汇,一种新的个人隐喻。旧的隐喻不断死去,而变作本义(literralness),新的隐喻系统不断增生变异,诗人在此意义上被称为文化的先锋。汉语新诗的创生,就是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一种“再描述”,来对抗古典语言的雅驯与僵化。所谓“拒绝隐喻”,大概就是对“本义化”语言的拒斥。白话新诗不仅仅是“言文一致”的变革,而是两种语汇的对抗。但是,这种“对抗”的动力之源并非来自“如何写”的焦虑,而恰恰是由“写什么”所催生的。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作为革命的突破口,又试作白话诗作为新文学战略的突破口,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没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做背景,没有现代性转型的逼迫,没有“写什么”的革命性要求,大概也不会在其时提出“如何写”的变革。“胡适的宣言意味着新诗首先是一场语言革命,是如何写的革命,这正是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所在。”我认为不尽然。白话文的兴起,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雅驯”的文言已经无法满足新思想的表达与传播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核心确是“言文一致”,但首先强调的是“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然后才是“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新诗的现代性,是庞大的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征象,首先是诗歌精神、文化意识的现代性要求,没有现代意识的人,没有现代精神的传播,新诗形式的转变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新诗现代转型的第一步是去魅,去除附在汉语之上的神性之魅,巫性之魅,政治、皇权之魅。格律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自由舞步。“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我不认为汉语诗歌有一个“无用”的传统,恰恰相反,汉语诗歌一直是“用”的,“诗言志”的,古代诗人尤甚。所谓的“酬”“奉”“送”“赠”“和”“答”“题”“戏”“别”……都是“用”的方式之一种,既有日常人生之“用”,也有俯仰、干禄、敲门砖之“用”。古典诗歌也并非“如何写”的典范,其制作手艺既称不上神秘,也并非由少数天才、巨匠、大师所统治。格律的经典化其实为“如何写”设置了一个可视的门槛,“熟读唐诗三百首”大概就可轻易跨过此门槛,读过几年私塾的士子们都可以登堂入室。当然,因为“大雅久不作”,我们觉得它很难了,很神秘了。而现代汉诗取消了“格律”的门槛,看似更容易了,人人得而进之,但进去之后的空荡荡,却逼出了真诗人和假诗人的分别。新诗“门槛”的降低,自由,是穿透集体意志、重新寻找个人手艺的一个途径。手艺是诗人经验的组成部分,个人独创性的标志之一,但新诗“规范”的缺失,使手艺被弄成最莫名其妙的事。在现代诗写作中,“手艺”是“如何写”的基本保证,也是在新诗“去魅”后的个人创造。在强大的传统阴影下,个人的独创不可能把一切“曾是”皆重新创造为“我曾欲其是”(尼采语,Thus I willed it.),也许微乎其微,而正是这“微乎其微”的一点点,使新诗回到了“个人”,属于了“个人”。 传统诗文的“雅”则属于一个身份阶层,大家“雅”得很一致,很精英,而白话新诗的“俗”却唤回了个人,这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性。
“如何写导致的是写作上的个人风格印记。而写什么则往往导致集体意志。”这一结论下得轻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如何写”才是“团体”“风格”“流派”得以形成的标志,“口语”“废话”“隐逸”“修辞”“复古”等等,皆属“如何写”的范畴;而“写什么”最终导致的将是个人化(当然,“政治去魅”之前并非如此,如毛时代的集体主义写作,不仅仅是“写什么”,连“如何写”也是统一的——工农大众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个人化”的来临端赖于“什么”的确立,这里的“什么”即去蒙昧后的个人观念、信仰、行为方式以及个人视野中的现场事物。“个人”带来的往往是原创、失范、众声喧哗,并最终导致“集体意志”的破产。这些年,为新诗制定“标准”的冲动不时涌动,这是一种很腐朽的做法。越是具有原创性,越无法被归类,越不可能拥有统一的“标准”。“标准”的确立,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束缚,是经典化过程中的临界点。新诗也并非完全“失范”,诗人的“手艺”即是范式之一,也是诗歌“深度”与“难度”的基本保证,只是它确实很“个人”,很“神秘”,“标准”制定者们不得其门而入。
我觉得老于将“如何写”和“写什么”搞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循环论证。探讨两个相互对立的问题说明这是个假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将问题解释得更清晰,而是更混乱。我将“如何写”和“写什么”看做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写什么”,然后再解决“如何写”。“写什么”关乎个人的视野、眼光、判断力、道德状况,有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现场和时代状况。不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是自欺欺人的写作,游戏、巫性、复古、返魅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诗人绝非“无中生有”的通灵者,诗人本身即是一个“有”,只需考虑写作的实践经验即可得出此结论。很多“学院派”的写作信条上写满了“如何写”,而“写什么”往往被享乐主义的技术狂欢所淹没、消解。一首诗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拐了十八道漂亮的弯,而在于它最终抵达了哪里,并在此抵达之途中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心灵、境遇、精神、混沌、以及一个诗人的手艺。“手艺”是“如何写”的必要保证,没有这一层保证,写作变成现实的工具、无难度的口水、娱乐的对象、集体主义的抒情是很自然的事情。
于坚说现在“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在我看来,并非是“坚持”,而是彻底“沦为”了无用。当然,此“用”非彼“用”。也就是说,诗歌被冷落是诗人自找的,而不是他真的坚持了什么。曾有学者发问:“中国还有值得尊敬的作家吗?”(丁东)这个发问的逻辑起点是:作家应该向社会提供点什么。你说你提供了“无用”,明显的不合时宜。诗人真的提供了手艺的、审美的“无用性”了吗?其实也未必。读读当下的诗歌作品,人情冷暖、入世情怀、守雌守默、民胞物与,似乎都不缺少,诗人们普遍是“用世”的,但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诗歌读上去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力感,像这秋后收割一空的大地,没有一点清新的气象,独缺一种澡雪的精神。“写什么”的问题立不住,精神的路径不得解决,难免满脸烟火之色,在生活的世界或取或予,与时俯仰,皆有失分寸。
没有人向诗歌要答案,诗人所能提供的也许只是一堆质疑、迷惑、困难、叹息、矛盾或绝望,但诗人不应提供虚假的光荣、表面的正义、深沉的谬误、精美的垃圾。诗人不是手提斧子的人,他提着自己的头,惯于走夜路。浅唱低吟不是现代诗人的典型形象,波西米亚不是,垮掉的一代也不是,我们必须重塑汉语诗人自己的形象。在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里,诗人的身份危机已不言自明。这是一场美学危机还是一种道德危机?诗歌自身的美学理想能够挽救这一切吗?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诸多疑问指向诗人自身。简单的道德主义不可能挽救一首诗,美学的浅尝低吟则会加剧诗人身份的合法性危机。关于诗歌,有两个古老的争论:诗与宗教,诗与哲学。诗担当不起现代人的宗教,上帝已死,诗人是否也要跟着一起死去?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曾将哲学引向对诗的投降,这不是对诗歌的救赎,是在返魅意义上的利用。如今,我们面临同一问题的不同面相:道德与美。道德压倒审美,会导致集体主义的义愤感;而审美压倒道德,则会使诗人从时代的现场中消失,成为不义的一群。诗人作为独立的审美的个体,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必自诩为“比你较为神圣”的一群,诗人必须不断自问:如何表达现代性,如何从精神上把握这个时代,并在诗歌上开创一个黄金时代?除了审美之维外,还有伦理之维,诗人必须回到时代的现场中,而不是自我边缘化,才不会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诗人必须领受一项道德义务——去感受自我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团结感”,在有限之中而与无限相关联。
向来就有两类作家,在道德与美的双刃上跳不同的舞蹈。理查德·罗蒂曾援引纳博科夫和乔治·奥威尔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类作家。纳博科夫对道德主义的奥威尔充满鄙夷,而对自己那种不顾大难当前、对于芝麻小事产生惊讶好奇的能力、对生命中的儿戏般的小注脚满怀得意之情。“凡是只能在入世情怀方面而无法在风格方面提供教诲的作家,都不能获得不朽。”罗蒂基本上做了持平之论:“我要强调,在若干重要的目的上,例如引起愤怒的颤栗和激发反感与羞耻,奥威尔与狄更斯有志一同;而在其他若干目的上,例如引起肩胛骨之间的激荡和美感的喜乐,纳博科夫与狄更斯不谋而合。”“不同的作家想做不同的事情,普鲁斯特想要自律和美;尼采和海德格尔想要自律和雄伟;纳博科夫想要美和自卫自保,奥威尔想对受苦受难的人们有用。他们都成功了,每个人都获得了杰出而同等的成功。”(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
前些时间,曾和朋友谈起了“我们的精神”问题。我们的核心价值何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方向上创造自己的传统?什么才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我觉得我们的出路还是在于精神。这精神关乎我们的良知、视野、识断、创造力和行动力,而其指向首先便是这“满目滔滔”的时代现场。诸神缺失的时代,如果连诗人们都心志凋零,成为思想史上的缺席者、失踪者,谁又能来安慰这小小的灰暗的人生世界?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天地良心,承担你该承担的一切,再也没人向你下命令。但我不相信“别裁别趣”是一种承担,我也不相信“文化复古”是一种方向。看不清“现场的事物”,看不清个体的实存和语言的现实,总归是一个问题。诗人们忙于接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我们时代的现实却远未与世界接轨。在这个技术统治的同质化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可谓“天降大任”,平庸即是一种罪。朱夫子当年论“人才之坏”,曾感慨“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总之我们现在也是闲说话有余,出世或闲适有余,复古或后退有余,先锋或愤怒有余,与时俯仰以就功名有余,而清洁不足,自省不足,格局不足,廉耻不足。
鲁迅先生曾言:“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我们现在大抵是一种什么状况?青灯黄卷或摩顶接踵均左右不适,美学的幌子上写满了山寨的名字,呈现出十足的“江湖骗术”的特征,完全依靠语言自身的“永动机”装置来遮掩一切。在知与行上,既无明确的核心价值、精神结构和心灵深度,又无天骨开张的胸襟、气度、信仰。这个时代的诗人看上去个性分明,隐隐然领时代风潮:大师、名流、精英、流氓、隐士、壮士、烈士……事实上多空言喋喋,笔底风云,舌下英雄,空有济时及物之心,于事无补。一种厚颜无耻的信念也正淹没一切,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在。这不再是一个天才当道的世界,一切均在权力话语之下心悦诚服。专制和势利也渗透进诗人的肌肤,一个时代的诗人群体变得浇薄、谬戾,甚至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温情与好意都不复存在。想当年李杜“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何其温情;想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那份厚意;想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份情怀……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
尼采对“当今时代”是这么说的:现代的喧嚣令一切无从生长,一切都滑落在浅水里,没有什么可以沉入时代的深井;一切都是飞短流长,一切都是流言蜚语。我们还能从自我身上唤回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吗?我们还会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随诗神的脚步吗?现代生活的崩乱与分裂,逼迫我们一次次重返最初的开端,返回自我的实存。人只有认清他自己所处的真实境况,他的状况才是一种真正的“精神状况”。辨清自我的实存与时代的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的世界才会逐渐清晰起来。前面的路大概有两条:超越与沉入。超越之路是难的,那意味着你将独自与一个整体对抗;而沉入,则需要在自我中唤醒一切属人的东西,才不会被物的世界包围,才不至于产生幻灭感。“前者要求的是自我修炼,后者是爱。”(雅斯贝尔斯)出世与入世迫切的诗人,若无精神的自省,若非堂庑特大者,心志凋零、虚无幻灭是题中应有之义。
200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