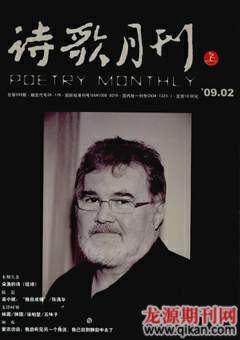津渡随笔(四篇)
津 渡
水边的鸟
秋冬是观察水鸟的好时机。从入海口到秦山,绵延数十里,些许滩涂和湿地一息尚存,到这儿来过冬的鸟儿不少。丽日当空,便有大群的白鹭、池鹭、苍鹭,以及行鸟 、鹬类的鸟儿到滩涂上和湿地中觅食。
池鹭偏爱僻静的地方,它们往往站在荒寂的埠头和水面突出的礁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流水,乍一看,还以为是个身披蓑衣的老人在那里静静悟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要是你猫身走近了,正面看到它,就会大吃一惊。它们面颊青绿、豹眼环睛,天生一副尖嘴钳一般的巨嘴。那颈饰也很特别,青色和麻色的细羽一绺一绺地绞结,很容易让人想起是堆带电的胶线缠绕在一起,隐隐的电流要一直麻到你的心里去。这副尊容,铁疙瘩一样的身子,再配上紧贴大腿的白短绒“裤头”、黄色的“长筒雨靴”,哪里是个淡然的老人,简直称得上是凶神恶煞。你这时才会明白,它可是独守滩头,一夫当关,在那里“剪径”过往的鱼儿。它们的个性也真的猛恶刚强,我幼年时,水埠头的围网边曾经缠住过一只,我抓住它,它也不肯屈服,把我的手背啄得鲜血淋漓。傍晚,我用麻绳系住它的脚,另一端绑着凳腿上,它就拼命地扑腾,一刻也不肯停歇,到了上半夜就饮恨而死。
灰鸥要好看得多,它们浑圆的身子披着灰色的短绒,在海面上一边翩飞,一边温文尔雅 “晏晏
——”地鸣叫,看起来颇似位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其实看看它们的嘴就知道了,也是位凶狠的主儿。它们在水面上滑翔,忽然俯冲下来,一啄,就会钩起了一条鱼儿。有时候,它逮到较大的鱼儿,放在围堰的石板上啄食,一嘴下去,就会撕起一条鱼肉,耸动脖子,几下几下就吞咽了进去。
湿地中间的苇林是鹬的天堂,它们在此悠游地生活。黑尾塍鹬是招人喜爱的鸟儿,我每见它把长长的绿喙伸进泥汤中筛糠似地抖动,引得屁股上那点黑羽不停地颤动,这就要使我止不住发笑。更可笑的是锥尾沙鹬,它们觅食时,屁股始终会一闪一闪地点击个不停,可惜它太狡猾,不等我近身,便会远远地飞起,留给我一个黑色的小点。三趾滨鹬是清闲的,它们总是在苇丛中停停走走,一边细心地端详芦根,一边挥动针刺一样的尖喙,漫不经心地东啄上一口、西啄上一口,天知道它在啄食什么呢。蛎鹬也是难以亲近的家伙,它们异常地惊觉,我只在海潮来临时看到它们在礁石畔奋力啄食,那举动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举着鹤嘴锄在岩面上敲击。我曾经想仔细观察它进食的过程,不意它在专心工作时还有余暇来注意周围的动静,海浪声那样大,它居然察觉到了我,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把脖子伸得直直的,在飞溅的浪花涛屑中飞走。
滩涂和湿地上不时也有行鸟的光临,它们的脖颈上无一例外都围着一条“围脖”,白色或黑色的,甚至棕色,我想这大概就是俗称它们“环颈”的原因吧。金眶行鸟的身段娇巧,长腿玉立,三趾纤纤,它们潇洒又清俊,除非觅食果腹,它们总是从容有度,意态佻然,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它们。至于鹭,无论林间、滩头、湿地,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我原来工作的办公楼,三面环水,一面向山,上万只鹭在我窗子对面的秦山上繁衍生息,数年来与之比邻而居,我潜意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置身其中,就连我自己几乎也要变成一只鹭了,它们带给我的欣喜,三言两语又岂能尽述。
公历二OO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农人和鸟
黄昏时经过落塘村,我特地停了一停。临海的那片湿地,如今大部分地方都填了土,种了绿草和植株,意在新建出一片海滨的生态公园。落塘村这一带启动得稍晚,沿着海堤还留着几个水塘,养着些鱼儿。因而我才能看到落暮时分一片拍打堤岸的海潮,一个倾斜的天空,一个歪戴了斗笠、在塘坡间逡巡的农人。七、八只大白鹭似乎并不太怕人,像几只保龄球立在水塘黑黑的另一角,那意思再明显不过,无非巴望着他早点儿离开,再到水边啄上一两嘴,借机叼走几条小鱼。他扶了扶斗笠,把一声咳嗽压低,然后走了,它们才挪了挪颈子上那个接着长嘴的头颅,而后松开,伸直,慢慢提起枝脚往塘坡下去……
前些天我收到一期杂志,封二与封底有两幅有关农人生活的图画:一幅是夫妻俩从田间回来,男人扛着把镢头,一手倒提着只黑水鸡;另一张是男人把一条狗儿放倒在石台上剥皮。虽然画面充满动感,也不乏某种力量,但我看了这两张图,心里却有说不出来的难过……我楼上的人家养了一群小狗,有一次,一只叫“亮亮”的小狗不慎落水,我把手递给它,让它搭着,把它从小河里拉上来后,它从此也就跟我结了缘。有时候,我还没看到它,它就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了,在我腿上、手上、脸上蹭着,舔着。雨天,我开着车,我从后视镜里竟然看到它浑身湿漉漉的,起劲地撵着我的车。这毛团似大小、可爱的小生灵,不知不觉,竟和我的生活有了某种联系,时不时要来感动我的心灵。我幼年时和母亲在水田里扯稗草,有时惊起些苦恶鸟、董鸡,我母亲往往就会停下来,念叨着吓坏了它们,好生地一番叹惜。鸟儿和我们同一片蓝天,同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离我们越近就越是福泽,农人们大抵都有这样的认识。
当喜鹊在村头的老树上垒了窝,每天清早站在枝梢,一边翘动花尾巴,一边“嫁嫁——”或者“客客——”地鸣叫,心中清澈的喜悦也就被它像泉流一样的叫出来了。在这叫声里,迎着早晨的太阳去田边地头,就是捏在虎口里的锄头柄、铁锹把,也会觉得格外地有力。后来,它们又产了卵,孵出一窝雏儿,忙忙碌碌地飞进飞去,抚养幼鸟长大,这完全是大地上的一幅生计图,与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同呢?至于麻雀,它们在门墙洞里、檐下的瓦缝间、仓房隔板下衔来布片与鸡毛,伶俐地建成一个家,一大群整天“叽叽喳喳”的邻居这样叫着、飞着,甚至在我们洒下谷子喂鸡时,它们混进鸡群里去啄食,这又是多么安谧与恬静的一幅田园图画。与它们不同,燕子是候鸟,它们在春天里回家,每每斜穿柳丝与雨帘,飞到田野上空,捉了虫子,再飞回来,栖在堂屋神龛上面的泥窝边,张开了嘴叫唤,它们不辞劳苦,如此这般地热爱生活,歌颂生活,不禁使我心生敬意。
在乡下,只有不知事的少年郎或是“二流子”一样的闲汉才会去抓鸟、打鸟,我未曾见过农人们不务正业地放下手头的活计去侵害鸟儿。他们顶多会在地头上伸直发酸的腰身,去水边摘一片菖蒲叶子,抿在嘴边摹仿鸟儿吹出哨音。要么,他们嘴角咬着根草茎,装模作样地学鸟儿的叫唤:“阿公阿婆——割麦插禾,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是善意的,这些农人都是爱着鸟儿的吧。
公历二OO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与鸟为邻
院子里的鸟儿越来越多。昨天傍晚,我从围墙边散步过去,竟意外地听到了小珠粒儿弹拨一样的吱叫声,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双音节鸣音,音调虽然低了些,但音节却是非常地肯定和清晰。我凝下神来寻找,果真就在几株绣球花树中间发现了那“鬼鸟儿”。这是一只斑文鸟。叫它鬼鸟儿倒不是因为这种鸟儿不吉利,而是因为它长得太过瘦小,连头连尾十厘米长短,大拇指一般粗细的身体,况且一副黑头黑脸,十分地清癯消瘦,叫人格外地怜惜。
眼见我走近了,这聪明的鸟儿立即报起警来,像是从舌苔下支起一根小弓弦,迅速地绷紧,“谁的,谁的”地乱叫;不出我所料,相距不远,另一只就从一蓬黄杨下机灵地飞起,扑腾到了高处的枫树枝条上。其实这对小夫妻的担心是多余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明白,眼前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实在是位再和善不过的亲邻。我想,这个看法,院子里那两只伯劳肯定早就有了的。它们刚进这院子时,一旦遇到我走近,就要可着劲大叫“碴儿——碴儿——”的,仿佛我天生就是个找碴的主儿一样。现在可好,我只要不是走得实在太近,它们是不会太在意的。若是吃到了草地上的虫子,它们还会对着我欢叫,“靓——,靓——”,这声曲显然就是愉快的,甚至称得上是种赞美。
院子里还有两只白点儿,我猜想它们是从海滩边过来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移民”来的,我是不清楚了。去年冬天,我就经常看到它们的踪迹。从它们平常飞行的线路,我猜想它们的巢就筑在图书馆屋顶的坡角上,可是我始终下不了决心去瞧个端倪,生怕自己多情,反倒唐突到“佳人”。图书馆和食堂对望,中间是座假山,一个小水池,一条绕行的过道,捏着土豆丝饼去图书馆的女孩子经常会在路上掉下几块蛋皮、土豆丝条来,我想这大概是它们喜欢上这个地方的一个缘由。下大雪的那阵子,这两只白点儿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雪茫茫一片,它们找不到吃的,傻傻地站在小餐厅前,屁股不停地点来点去。后来,好心的胖厨娘夹了一筷子煮熟的胡萝卜丝洒到雪上,才帮它们度过了难关。
白头公是这院子里数量最多的鸟儿。它们不怕人,把巢筑在房舍边的林子里。我至少已经发现了六处它们栖息的地方。它们建房是不挑树种的,随意就在银杏树、橘子树、石楠、榉树上筑巢,它们甚至还学着麻雀,在空调的室外机背后筑巢。这是种再平常不过的鸟儿,可是对它们我始终充满复杂的情感。另外的篇章中我已对它们的体貌、习性和鸣声多次提及,我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提到它们的鸣声,尽管那鸣声荒腔板调,显得极为潦乱草率,毫无规律可循,但不管发出的是何种具体的声音,每种声音中间都要无一例外地混杂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怆。这是春天的早上,太阳温暖地悬挂在屋顶,一大片黑麦草青幽幽的,就像从魔术师的大眼膏袋里挤出了大团大团的绿云,一切都显得生机盎然;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在草地上方,高大的银杏树顶端,最高的枝梢,那里有一只白头公,仰起白头,对着天异常响亮地叫着:“可苦——哩,可苦——哩噫!”不由得让人万分沮丧……
院子里活动的柳莺也很多,可是它们都不太愿意住在院子里。除了在网球场围栅外的红珊瑚篱内找到一个鸟巢,我再也未能在院子里找到它们另外的住处。它们的“主力部队”住在院墙外的柳林里,一大族,三、四十只几乎全部都在那里。虽然它们与我不是紧邻,隔河而居,但我还是把它们当作了我的芳邻与嘉宾。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们的身段、眉眼,和那小笛儿一般的曲调。
按理说,麻雀应该是院子里最多的鸟儿。不知怎地,我院子里的麻雀倒是很少,我认真数过,总共也才五六只,就住在招待所的外墙上。那里以前拆掉了一具旧空调,留下了几个孔洞。好几次维修队说是影响外观,要把那孔洞糊上,可是我不同意。我的理由是为这几个小洞搭次脚手架不合算,也不安全。维修队队长居然很当回事,还把我这“旨意”传达到了每个工人,说是我交待了的,再也不要去碰那里。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暗藏的“小九九”:这几只麻雀,好不容易才住进了我们的“招待所”,怎么好轻易地就撵它们走? 我心下可是希望更多这样的邻居住进院子里来。
公历二OO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清早鸟音
昨晚上心情不好,我睡得很早,凌晨四点多钟,又听到它们在我窗外吟唱,心里面就格外地复杂。我本来想蜷在床上,不再去看它们,但有一只白眉巫鸟在我窗下不住地叫唤,非常地耐心,那“嘤噫”声虽然较为尖细,但穿透力很强,收尾的颤音就像是音叉振动后的余音,一时之下,令我却是十分迷醉。我在自己粗浊的呼吸声中分辩它的节奏,它一声接着一声,绕着我的呼吸鸣叫,就像是绕着一根柳条,在那上面一粒一粒地数着嫩芽;稍歇息了一会,大概是去啄食了,它又降低了音调和旋律,“噫吲——,噫吲——”地叫,像是细致地给新绽放出来的柳粒儿滴上露水……我于是爬起床来,穿好鞋子走了出去。
有些时日没去长山了,但昨天我去的那一趟,只是看到了新布的鸟网,和鸟网上新增的几只园林莺的冤魂。这样子已经让我很难受了,从山上转回来时,看林的老头又特意在我经过的路口吊上了一只刺猬——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镇子边上还有几个卖林号鸟的人,它们究竟有什么吃头呢,除了胸前那团肉,全身上下几乎再无一块剔下来可以成形的肉块……我想起一个朋友和我的争执:“既然你也吃荤,就不要反对我们吃鸟,我们的底限与你不同,我们的底限是不吃人!”我宁愿相信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要我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花纸,满足一点小小的欲望……我在想,一些不开心的事不提也罢,新的一天开始,早晨的空气美好而洁净。
这是四月,居民楼和大海之间的那片空地,树木已经大片地发青,跃进眼帘的是一片葱笼。白玉兰和东京樱花谢了,开始茂盛地生长叶子,构树和变色木芙蓉虽然枝干裸露,但枝头也已梳出了像样的塔形发髻。我甚至听得到河道两边的芦苇,它们用力拔节时从心眼里发出来的喟叹声,那声音很低,在叶柄底部积存的露水里轻轻摇荡,“吁,吁依——”。琼花初开,一簇簇一团团地绽放,在那枝上做出了一副富贵满堂的光景,而黄山紫荆只剩下几点残红,垂头对着晚景。红花酢浆草的花朵是在正当开的时日,但她们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这段时间里总是羞怯地闭合眼睑,要等到太阳高照,才会重新撑开一把鲜红的小洋伞。就是在这样的景象之中,有时候,天地之间忽然一起沉静,一刹那间变得寂然无声,已而日本晚樱的花头悄悄地凋落,落在我的肩头,露珠从竹叶尖上滴溅下来,噼啪地打在我的旅游鞋鞋面上,整个世界就从细柔而忧伤的情绪中回转,这时候清晨真正的主人是鸟儿,它们珠喉呖呖,那鸣声如滴如溅,如温泉的泉眼汩动,如涓涓细流引动,从石畔岩隙间流出,继而活泛地穿引集合,汤汤洄洄,终于汇聚在一起,沸腾不息……
在东面的河坡上,雉鸡是何等地自在愉快,它们粗哑的嗓门经过露水的滋润,显然清脆了许多。这是早上发出最大鸣声的鸟儿,雄鸟有节奏地发出“阔阔,阔阔,阔阔”的声音,召呼紧跟着的雌鸟。它昂首挺胸,骄傲地对着一株苦苣头顶上的黄花,煞有介事地大叫。我实在是不忍心惊动它们,老实说,我厌恶它们惊起时从肺里发出的一连串浑浊的嘶叫声。我愿意我们永远不会惊动鸟儿,就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歌唱。比它的声音小一些,是白胸苦恶鸟的叫声。在河水的岔口处,那里有着连片的蒿白林和依水生长的野芹菜。它们有次序地下水,屁股拖曳着,从折倒的蒿根上滑下,像是从滚木上往清水里放下一艘又一艘乌篷船的小模型。一俟全部入水,它们就开心地亮开嗓子,争先恐后,像一锅沸水那样炸开,在水面上争抢虫子,“苦——苦——哇呜,苦——苦——哇呜”地起哄;而它们分散开来,就会安静下来,偶有一只大惊小怪地“苦——哇——呃哏,苦——哇——呃哏”地聒噪,心情愉快地一溜小跑,在浅水滨的水芹顶上踩出闪亮的水花。而此时,布谷鸟就在它们头顶的构树枝上,这也是鸣声响亮的一种鸟儿,有必要申明的是,它们并不只是割麦插禾时才会叫两句“阿公阿婆——,割麦插禾——”,鬼鬼祟祟地,它们中间的一只站在枝上装作若无其事,“喀——咕,喀——咕,咕咕——,咕咕——”不紧不慢地叫着,另一只却暗暗地潜往低处,悄无声息地盯着苇莺新缝制的“香巢”
——她是想伺机将她的卵产在苇莺的巢里吧。这只穿灰斗篷的鸟儿发现了我的存在,猛地吓了一跳,赶紧从树枝上方甩下来一泡屎,像个巫婆一样跳起脚,“扑”地一下飞走。它强健有力,掠过苇林时,竟然在苇叶上卷过一阵细小的波浪。
白头鹎是我一提再提的鸟儿,它们的鸣声不仅粗大,而且是太放肆了,简直把我不当回事。它们恣意地改变曲调,篡改自己刚刚唱过的那首曲子的歌词,像是无意中偷窥到了我猫在树桩后的“不光彩行为”,一定要“检举揭发”我一样,它在那里大声武气地显示它的成绩,不免自鸣得意。我拿它们没办法,就把望远镜扭过来对准它们,一大群鹎于是向我显现出它们另外的智慧,有两只故意做出很丑陋也很蠢笨的飞行姿势,打开翅膀,接着又合拢,像飞行在空中的小炸弹一样,飞到远一点的树上去了——不过是想要引诱我离开罢了;另外两只却只是做做样子,它们好像作势逃走,其实却是沉下身子,跳到隐蔽的枝叶下罢了;还有一只高高地端坐树巅,根本就不愿多理睬我,它偏过头去,起劲地一阵鼓噪,且带有警示音,“喳儿——喳儿——”地挑衅,意思仿佛是说:谁怕你了,怎么样,你有本事倒是爬上树来呀!我只好苦笑,我想它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又何曾讨厌过它们呢?
有一些鸟儿的叫声不算清晰,但很明显,比如家麻雀,叽叽喳喳的,这乡间歌唱家,想冒充过境的土八路,可是它一开口就露了馅,每每被我盯牢,这位老邻居似乎很不好意思打扰到我,和我打完招呼后就赶紧收拾陈旧的乐器,一道烟似地跑得远远的。而一只小云雀站在朴树的枝巅,头上的小发冠梳得齐齐整整,它冲向草丛时,炫耀地发出了清丽的鸣声。如果不认真谛听和仔细地观察,你是很难看到棕头鸦雀或者文鸟的。这是两种很小的鸟儿,大约都只有十厘米左右的身长。白腰文鸟和斑文鸟往往都是一对儿出来,它们个子很小,显得很谨慎,但并不胆小,有可能它就在你的头顶,它只是不吭声,在你没有发觉它,或者它认为没有危险时,还会在密集的树杈和树叶间上上下下地跳动,而且还会互相逗弄,做出一番小儿小女相依相恋的情态来。根据我观察得来的经验,鸟儿最怕的并不是人,鸟儿最怕的是人的眼睛,人眼与鸟眼一旦视线交接,鸟儿就会十分恐慌。说起来,鸟眼远比人眼敏锐有力,但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鸟儿往往却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快地逃走。果然,这一对小夫妻,向我做了两个“鬼脸儿”,就像纺车架上的棉花锭子一样振动似地飞起来,飞到了离我二三十米远的另一棵树上。棕头鸦雀是善于在枝上弹跳的鸟儿,这些鸟儿有着异常出色的迁移能力,它们在竹枝间毫不费力地避开我,一边发出了几不可辩的“唧噫”声来。
有些鸟儿会发出很好听的鸣声,比如园林莺,黄腰柳莺,甚至强爪树莺也是此中的高手,不管是否在劳作或是休闲,它们都很乐意一展歌喉。有些鸟儿却是很难得开一次“金口”,也许它们要吃饱了才愿意歌唱。我在海棠树的枝杈间看到一只红肋蓝尾鸲,我知道它也天生一副轻柔的好嗓子,可是它似乎没有养成自觉表演艺术的习惯和癖好,或者是它一时心血来潮,想要耍耍“大牌”,总之我等了老长的时间,它愣是没有给我演唱。今天早上,我还在高大的合欢树顶上,发现了一只十分罕见的白眉巫鸟,这小东西异常地惊觉,像片榆钱叶子一样在高高的树梢间扑动,起先它一声不吭,待到注意到我,这才发出细小涟漪漾动一样的轻声鸣叫,急忙地逃逸。要观察到它们的一举一动实属不易,很多人也许并不相信,亲近鸟儿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藏在那里,你最好是一动也不动,除了在那里静心凝神,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公历二OO八年四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