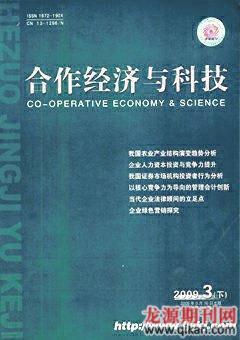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
伍 军
提要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农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农民组织化是以一定的组织方式来行动,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状态和过程。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稳定和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需要。
关键词:农民组织化;乡村治理;社会秩序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背景,必将引起乡村治理的变革,对现有的治理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些新形势和背景下,如何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即达到维护农民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构建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农民组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
农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维护农民的权益是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的前提。在新时期条件下,农村问题的解决虽然具有了更好的政策和条件,但各种利益的博弈也将更加激烈,具有不可预测性。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如何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
(一)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农民经济权益的维护。麟村位于湖北潜江市高石碑镇的东南角,耕地面积2,998亩,其中旱地1,540亩,水田1,458亩;10个村民小组,2,126人口。2005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758元。麟村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源,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城市化的推进在这里相对较缓,准确地说现在还基本上没有城市化的迹象,因而,由于城市化引起的各种问题在麟村基本不存在,而影响最大的要属全面取消农业税了。
税费改革和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因为税费过高,农业投入与农民收获基本持平,再加上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部分抛荒现象(即使抛荒也得缴税费)。税费改革后,这一现象稍有缓和,有些外出打工的人将土地出租或送给别人耕种,双方都能有所得,因而也容易达成协议,相安无事。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对土地的热情被重新激发出来。原来将土地送人或出租的农户要求归还或收回土地,有的小组则要求重新丈量和划分土地。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土地资源对该村村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农民并非真正是“一袋互不相干的马铃薯”,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了,而且也显示了组织化的力量,得到了镇政府的重视,并且最后维护了自身利益。
全面取消农业税不仅会引起土地的重新划分,还会引起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村的公共物品是由乡镇和村共同提供的。“三提五统”中的“三提”是交到村里去的,而“五统”是上缴到乡镇的,因而它们必须而且也有资金来提供农民所需要的部分公共物品。取消农业税之后,“三提五统”没有了,原本有限的乡镇财政和村财政减少,肯定会减少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公共物品的缺乏势必影响村庄的正常运行和良好村庄秩序的生成,而且也给村庄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为此,在新农村建设战略中,国家将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和“以工补农”转移支付资金来弥补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必将与村委会之间发生资源的争夺,作为处于弱势的村委会如何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资源,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除了制度、政策和监督上的不断完善之外,农民必须提高组织化的程度,增强与乡镇谈判的资本。
(二)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农民的政治权益主要表现在村民自治权、政治参与、民主诉求、上访权等方面。在麟村,村民自治虽然实行了十多年,进行了四届换届选举,但村民自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冷淡,更谈不上什么民主诉求了。
在麟村所在的潜江市也确实有极少数村庄的农民参与热情高涨,对乡镇指派村委会的做法会进行积极抵制,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较它们与麟村的差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那些村庄都有几个带头人,即“体制外精英”。在麟村,村民似乎都“安分守己”,在这样的村庄里,做带头人会有更大的风险,而且也很难有所作为,农民组织化的难度较大。
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会由于过重的剥削与压迫而自发地组建农会,但现在,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似乎更没有什么外在压力而缺乏组织的动力了。其实不然,该村村民还是有对农民组织的需求的,一方面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害怕“枪打出头鸟”,即缺乏维权的相关知识,意识也较淡薄,没有人敢带头;另一方面是没有维权成功的先例。因而,首先在加强村民维护政治权益的意识的同时,增强他们基本的法律知识和维权知识;其次,让村民能真正享受组织化维权的成功感和欣慰感。这项工作由谁来做呢?笔者认为,只能靠两种力量去做:一是非政府组织去做;二是靠乡村精英去做,包括体制内精英(即村干部)和体制外精英。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村民增加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增强村民政治参与和维护政治权益的意识。体制外精英能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带头人,在法律知识增强的同时也没有了原来的顾忌。而体制内精英处于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作为村里的“当家人”,当然希望他们能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可以作为村委会抵制乡镇政府行政干预的工具。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问题;在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中,乡镇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挤占国家下拨给村庄的资源。在这种场合下,村委会就急切需要组织化的农民组织作为谈判的筹码,为村庄争取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乡镇在农村的“代理人”,村支书和村委会干部又害怕农民组织起来,担心农民组织起来后力量过于强大而不好管理。农民维护政治权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农民组织化是乡村社会稳定的需要
农村的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都必须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一)农民组织化能为农民提供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政治是“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无法向农民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是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非制度化参与行为越多,意味着农村制度化参与渠道越不畅顺,农民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就越少,农民的合法利益就越得不到保障,以致农民进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怪圈。
农民组织化为农民提供了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了农民与政府的沟通能力,有利于调节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必将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增强了合法性机制。无论是物质资源的分配,还是把政治参与、政治要求等政治资源引导到支持政治体系的轨道上来,均可以合法的农民组织作为载体;二是具有了疏导机制。疏导机制的作用在于能使农民畅快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为政府调整利益矛盾提供充足的信息,使农民对事关自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有参与、建议和批评的正常途径,进而支持和认同政府的意志和决策,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
在麟村,村民对小组干部、村委会干部和乡镇干部还是有很多意见和不满的,比如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村公共事务的不当干预、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操纵和控制、村委会和小组干部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等等。面对这些问题,麟村村民只能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或忍气吞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村民特有的包容性和顺从性保证了麟村的稳定,但这种“弱质性稳定”其实是隐藏着不稳定的根源。
总之,从农民角度看,农民拥有合法组织后,农民可通过这种组织工具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能进一步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还可以弱化农民的反体制意识,提高农民对基层政府的合法性认同。
(二)农民组织是农民与政府矛盾的缓冲机制。社会缓冲机制是指能分解社会冲突、吸附社会混乱因素以减缓不稳定因素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冲击力的一种有效机制,它是联结社会和国家的中介体,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认为,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体之间的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的对话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节。
在麟村,村民对村干部和乡镇领导的不满没有表达的机制,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会发发牢骚,以示不满。如果有农民组织作为中介的话,农民的不满和意见都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反映到乡镇一级政府;乡镇一级政府也能通过与农民组织进行沟通,了解村民的实际心理和情况,便于做出正确的决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分散的农民有时候可能会成为流言蜚语的传播者,继而成为受害者。往往一些小事情会由于村民之间相互传递的失真或者走样而将事态扩大,从而引发不必要的不安甚至人心动荡。如果能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程度,大小事情都能在组织内部解决,用组织的章程和制度来规范成员的言语和行为,就会避免无中生有和事态的扩大化。村委会干部和乡镇领导也能迅速从组织那里了解实情,而不至于信息封闭或信息不对称,这样既能节约沟通交流的时间和成本,也便于采取正确的解决措施。
三、农民组织化是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需要
乡村治理的目标除了维护农民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外,还必须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农民组织化的过程,也就是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过程,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是乡村治理的目的和结果。
全面取消农业税,解决了国家对农村过度提取利益的问题,遏制了基层政府和干部搭车收费,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基层政权来控制农村的能力减弱,也就是所谓的“官退”(国家行政力量从农村中退出)。“官退”之后,农村必须增强自我整合的能力,“官退”的空间必须由“民进”(农民组织)来填充。在国家控制力减弱时,农民组织化能增强农村的自我整合能力,而且它也是农村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
(一)农民组织化有利于农村自我整合能力的增强。国家整合和农村社会的自我整合是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两种手段。前者的动力机制来自国家,后者的动力机制来自社会;前者表现出建构的机制,后者表现出自生自发的机制。在“赶超型现代化战略”的支配下,国家整合一直占据着主导,表现出强烈的国家建构色彩。
国家建构以强大的国家能力做后盾。国家能力主要指国家的控制力,其构成因素有行政权力、法律制度、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等。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镇进一步弱化了对村庄的控制。行政控制的软化,加之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权威受损,国家在农村的影响力势必会受影响,只能通过意识形态来体现和达到国家的控制。毫无疑问,依靠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达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控制是不可能的,为确保乡村社会秩序就必须增强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能力。
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途径很多,如“促进村庄精英系的成长,加强农村信用和制度规范建设、增强体制内精英的社会资本成长,缩小城乡差别、消除不平等的制度歧视等”,但对乡村社会原子化结构的农民来说,加强农民组织化则是提高乡村社会自我整合最有力、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农民组织化,将农民集合在一定的组织中,不仅可以用组织的规章、制度约束农民,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归宿感,通过对组织的认同而达到对基层政权和国家的认同,从而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
在麟村,国家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大,主要是行政干预依然严重。在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上,国家的建构理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组织力量弱小,表现在:村民委员会没有真正发挥其功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未见雏形,各种功能性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因而村庄的自我整合能力较差。麟村的村庄秩序较为平稳,除了与国家控制力强大有关外,村庄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农民组织化有利于乡村社会结构的优化。龙劲松将乡村社会结构分为“权力结构、组织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层次,三者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结构体系”。在乡村社会,权力表现为掌握和运用一定社会资源的能力,包括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资源类型。权力结构需要组织结构的支持和表述,包括显性的正式组织和隐性的非正式组织。文化是乡村社会比较独特的一种资源,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去,杜赞奇称之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权力结构需要组织结构的支持和表述,农民组织化优化了村庄的权力结构。在麟村,没有村民全体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只有村民委员会,既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执行机关。虽然村民委员会并非是由真正的村民选举产生的,但村民基本上还是认同的。村民委员会的产生保证了村庄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这是乡村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由于缺乏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有效监督,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滥用不可避免。如何避免村民委员会权力的滥用,就需要来自村民的有力监督。毫无疑问,农民组织的监督是最有力量和最有效的。
在麟村这个农民原子化、缺乏组织化基因的村庄,良好的村庄秩序一方面来自国家的建构;另一方面笔者将它称之为“历史的惯性”。一方面村民之间差距不大,农民强烈的攀比心理不会作祟,村民也就依然习惯按照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从而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实现了良好的乡村秩序;另一方面传统的有助于乡村秩序稳定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淡化,而现代的各种组织又没有建立起来,理论上似乎会造成乡村秩序的稳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该村的村民继承了中国农民特有的保守性和包容性,乡村秩序依然稳定。但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稳定和一种“弱质性乡村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互动的加快,这种消极的稳定势必很快会被打破,乡村秩序的弱质性也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因而,通过加强农民的组织化,来优化村庄的社会结构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