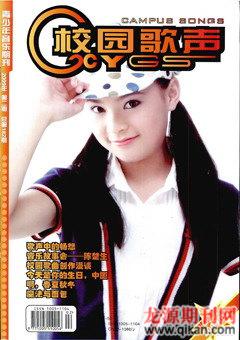春天在哪里
袁政谦
上世纪7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我从同事那里借得一套78转的老唱片,记得有4张。那位同事是从哪里弄来的忘了,只记得闲聊时他说起他有几张外国唱片,是小提琴,很好听,于是就向他借。我父亲原来也有不少国外的老唱片,但文革初期怕惹事全都“处理”掉了。那时我才读初一,自然不懂得它们的价值。我帮着父亲把那些唱片从精装书一样有硬壳的封套里一张张取出来敲碎,然后把印着外国字和外国人的硬壳和封套烧掉。做这些时父亲不住叹息,我却不知道可惜。后来在农村插队时,晚上用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打发时间,于是发现某外台每晚9点半钟播放30分钟古典音乐节目,听了几次就入迷了,此后几乎每晚都听。那应该是我听古典音乐的一种启蒙。不过,在当年中国内地的僻远山村里听这些东西,常常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白天到公社开会听林彪事件的传达,晚上听收音机时,介绍的是小提琴家雅沙·海菲兹,那位播音员把海菲兹称做“小提琴国际超级圣手”,一边听着海菲兹演奏的美妙乐曲,一边却强烈地感到这种音乐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远太远。回城工作后,便不敢听外台了(那时外台叫做“敌台”,有人就因听外台被发现而获罪),那个古典音乐节目也就没有再听。那是只有几部样板戏和几首革命歌曲可听的年代,借到那套外国唱片又使我想起在乡下听音乐的那些晚上,于是兴奋异常。拿到唱片后回家请我父亲看,他说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春天》,是50年代初期的苏联版。晚上把电唱机搬出来,接到家里那台电子管收音机上,为避免闲话,还把窗户关上。虽然那些唱片太旧,沙沙声不绝于耳,但当那些美好的旋律如溪水一般欢畅地流淌而出时,却觉得如同仙乐一样。那声音是如此的温暖清纯,足以抚慰心灵,让人感动不已。以后几天的晚上,我一遍一遍地听那些唱片,虽然夏日里关着窗户屋里很热,并且还得不停地把那些唱片换上换下,却乐此不疲,越听越觉得好听。如此这般听了一个星期,同事索要那些唱片,只好还给人家。过后却一直念念不忘。几个月后又向同事借,同事说借给朋友弄丢了,人家赔了他5块钱。于是心中怅然若失,常常想起那些不知所踪的唱片,常常想起贝多芬那首真是如同春光一般美好的奏鸣曲。
一晃十多年过去,90年代初开始买CD时,《春天》是我最早拥有的几张唱片之一。那时工资低,盗版又还未出现,正版CD比起现在来便宜不了多少,买一张很不容易。当然,关着窗户偷偷摸摸听音乐的时代早已过去。80年代听收录机,买了不少磁带,但一直没有买到《春天》。CD面市后,配了套音响,便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收集过程。我买的第一张《春天》是DG公司出品的梅纽因和肯普夫版,同一张唱片上还有贝多芬另一首著名的小提琴奏鸣曲《克莱采》。买到这张CD的那一刻真是兴高采烈。回家后立即打开音响放上唱片,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美好旋律的涌出。可是,曲子还是那个曲子,旋律还是那些旋律,而激光唱片和立体音响的音质也非当年的老唱片和电唱机可比,但从中我却听不出十多年前那种记忆犹新的味道了。这张CD我听了许多遍,可是总说不清它究竟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我自然更多的是从主观上去找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年太饥渴,如同现在吃那些精制的窝窝头时,再不会像当年吃粗糙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那样感到香甜了。真是这样吗?又觉得不全是。
一首经常听到的儿童歌曲中有这样一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这以后,虽然谈不上刻意,但我一直想找回当年第一次听《春天》时的那种感觉。我陆陆续续买了好几张《春天》,有帕尔曼和阿什克纳齐的Decca版,克莱默和阿格丽什的DG版,朱克曼和巴伦博依姆的EMI版,穆特与奥基斯的DG版等,其中有正版也有盗版。不过,听下来都没有当年的感觉。其实,这些版本都有很好的评价,各具特色。而早年听的那个苏联版,既不知是何人演奏的,也不知是什么公司出品的,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个范本。失望之余,包括第一次买的梅纽因与肯普夫的DG版,全都东一张西一张给了别人。这样,我手上便一张《春天》也没有。想想看,大约有五六年没有听《春天》了。
2004年初春里的一天,我路过一家私营书店,进去随意翻了一阵书。临走时走过音像区,迎面摆着一架子古典音乐CD,但我一眼就看出全是盗版。我已经有好些年不买盗版CD了,不过这次却鬼使神差地凑拢去。这时营业员走过来,是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她问我要买什么唱片,完了又补上一句,说都是正版片。我不由地笑起来,说正版怎么才十几元一张,这生意不是亏本了?于是那个小姑娘扭过头去不再理我了。老实说,这些盗版CD的封套都印制得不错,盗的全是大公司的产品,还像模像样地用塑料纸封装。这可能也是营业员谎称是正版片的原因。很快我就发现一张以前没有见过的《春天》,是RCA公司的谢霖与鲁宾斯坦版,1958年的录音。我早已下过决心不再买盗版片了。我的音响器材已经更换过几次,交了不少学费后耳朵也有点“功力”了,早些年买的盗版CD已经处理了不少,以前是图便宜可以多买唱片而实际上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那天,看见了一个没有听过的《春天》的版本时,我还是忍不住又买了一回盗版。不过,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新发现,只是因为手边一张《春天》也没有,好几年没有听了,想听听。
后来的事完全是意料之外的。那天回家后有事,唱片就放在一边了,过了几天听音乐时才突然想起它。但是,放上唱片后,从耳熟能详的第一个乐句开始,这张CD就让我找到那种久违的感觉。我那时真有种如梦如幻之感,那些仿佛清澈小溪一样畅然流出的旋律,似乎一直浸润到骨头里去……掐指一算,快30年了,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而这个谢霖与鲁宾斯坦1958年的立体声录音,显然不是我原来听过的那个苏联版。我担心会是一种错觉,听完一遍马上又听二遍,但同样如此。接着又查资料,有两本书没有提到这张唱片,而《企鹅唱片指南》对这张唱片的评价并不高。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自己觉得它发出的正是我想听到的那种声音。如果非要描述一下的话,可能是这样虽然小提琴的声音有点发干,但十分生动自然,并且略带一丝隐隐的惆怅:而钢琴委婉地伴随着小提琴,含蓄而不张扬
实际上,当我写出上面这行文字颇感惶恐,因为音乐带给人们的有些感受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并且人各有异,就像春天虽然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对它的感受却在不同的人心中,有很多主观的东西。音乐也同理。也因为如此,我不太喜欢看那种大段的对音乐的描述性文字。当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并非专业人士,也不懂乐理方面的东西,仅仅是喜欢沉浸于音乐中而已,而谈音乐是所有爱好者的权利。不过,我确实厌烦有些被称为“行家”的人写的关于音乐的文字,这些人掌握的形容词多,想象力也似乎比常人丰富,加上喜欢道听途说,于是就热衷写一些关于音乐的、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的文字,甚至还弄出些类似故事之类的东西来。
不过,这样的事当然不是现在才有。一百多年以前,关于上面谈到的那首贝多芬的F大调奏呜曲(作品24号),就有过一些故事,据说是跟贝多芬的某次恋爱有关,作品还被出版商附会了一个标题:《春天》,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当然,贝多芬的这个早期的奏鸣曲的确如春天一般温柔明朗,优美动听。有人说贝多芬表现的是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大自然,更有人把它跟当时被上层社会关注的贝多芬的那些恋爱事件联系在一起。罗曼·罗兰在他那本《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里也写道:“贝多芬是一个恋爱迷。从少年时起,直到接近最后的日子……”
虽然罗曼·罗兰是把“爱情”看作贝多芬的创造性动力来说的,但他同样把贝多芬那些恋爱加音乐的故事描述得绘声绘色。
不过,说来说去文字的描述相对来看总是具象的,更不要说那些五光十色的故事了。而音乐终究是音乐,它只能通过你的耳朵使你产生种种感觉,激发起你的种种情绪。你可以去想象,任由你把它想象成什么。但那是你的事,却可能不是音乐本身。我当然知道,专家们都认为跟贝多芬那些宏大、厚重、深刻的作品相比,这个被称为《春天》的奏鸣曲显得小,显得轻。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它,因为它总让我想起一个时代,还有当年聆听它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自从我得到这张谢霖和鲁宾斯坦版之后,我已经记不清我听了多少遍这个《春天》了,并且大都是只听它,而不听同一张唱片上另外两首贝多芬的奏鸣曲。有时我真有些恐惶,我不知道这样听音乐是“正道”,还是“歧途”。
现在,我又开始寻找(严格地说是等待)《春天》了。这是指谢霖和鲁宾斯坦演绎的《春天》的正版,因为我手上的这张终究是盗版。RCA公司是1994年出版这张唱片的,10年过了,要买到它显然很困难。但奇怪的是,我总觉得哪一天会跟它在某一家唱片店里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