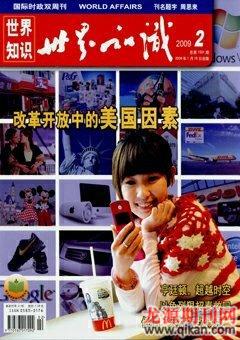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
王缉思
“文明冲突论”击中了当代世界矛盾的要害,触动了人们在宗教认同、种族意识、民族文化归属方面的敏感神经。

2008年圣诞节前夜,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与世长辞。从1957年发表第一部专著《士兵及国家》到2004年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亨廷顿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而他的政治思想影响不仅跨越了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界限,而且也将跨越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永远占有牢牢的一席之地。著名社会学家、亨廷顿的哈佛同事罗伯特•帕特南称他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知识界的巨匠之一”。另一位哈佛教授斯蒂芬•罗森则说,亨廷顿“既极为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朋友,又欣然面对同他观点截然相反的对手”。
对于思想家,是不能做到盖棺论定的。围绕亨廷顿的种种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尤其是他在1993年力排众议首次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重要的是,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冲突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证明“文明冲突论”击中了当代世界矛盾的要害,触动了人们在宗教认同、种族意识、民族文化归属方面的敏感神经。
论敌向亨廷顿认错
2008年1月,亨廷顿的论敌之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法乌阿德•阿贾米在当月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发表文章,公开向他认错。事情是这样的:在1993年发表亨廷顿文章的同一期《外交》杂志上,还刊登了一组回应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而阿贾米就是其中带头用重炮抨击亨廷顿的学者。阿贾米在当年的文章中说,国家而不是所谓“文明”,才是人们忠诚的对象;不管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口头上如何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世界各国现代化之路,就是西方化之路,别无他途。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现代化和抵制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位阿拉伯血统的教授当初还认为,主张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将在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掌权,崇尚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力争加入欧盟即为一例。但是,15年之后的阿贾米承认,亨廷顿的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我们后悔没有听取他的相对悲观、但也许更为正确的远见卓识”。阿贾米指出,正如亨廷顿所预言的,激进的穆斯林现在当选为土耳其领导人,这个国家已经不再乞求加入欧盟,而是开始觊觎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推进泛土耳其主张;伊斯兰世界在“使其现代性伊斯兰化”,反倒是西方世界开始走向自我怀疑和多样化。因此,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比我对他的批评更有说服力”。
亨廷顿谢世后,阿贾米立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题为《亨廷顿的警告》的专文,表示哀悼和反思。文章披露,亨廷顿夫人给躺在病榻上的亨廷顿读了阿贾米公开发表的自我反省,使老先生甚感欣慰,并委托夫人向阿贾米致意。
不过,阿贾米这次所说的“亨廷顿的警告”,没有更多地涉及文明冲突论,而是转述了亨廷顿在近著《我们是谁》中所表达的对于美国的深深忧虑。亨廷顿告诫美国精英:17~18世纪美国早期移民所留下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色文化是立国之本,其精髓是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格兰法治精神、掌权者的责任,以及个人权利。这些是“美国信条”的几大要素,是美国的成功之道,要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万万不可丢弃。亨廷顿提醒人们警惕的是,当代美国人被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所迷惑,有忘本的危险。尤其是从拉美等地涌入美国的新移民,还没有扎下美国的民族认同之根,连英语都说不清楚,却在人口中比例越来越高,文化影响越来越大。亨廷顿颇为伤感地描绘道:“星条旗已经下了半旗,而在美国特色的旗杆上,别的旗帜却飘扬得更高”。
亨廷顿是英格兰人的后代,对家族“寻根”极感兴趣;人越老越保守,恐怕也是难以改变的自然规律。因此,他发出这样的忠告自然不足为奇。耐人寻味的是,生为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贾米,为什么也同亨廷顿一起,唱起了美国信条的挽歌?
年过花甲的阿贾米年轻时从黎巴嫩移民到美国,从名校毕业后,成为中东问题研究的一位权威。他不但不认同伊斯兰激进思想,而且同策动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派”过从甚密,为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出谋划策。阿贾米同亨廷顿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对自己的政治见解十分执着。他甚至比亨廷顿还要高傲,在舌战群儒时从不畏缩。然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阿贾米同亨廷顿的立场恰恰相反。他时时处处为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辩护,对任何“非美”、“贬美”的言论,都要找机会反唇相讥(连我这样一个不爱争论的人,在一次会议上居然也忍不住同他激辩起来)。一位从种族到宗教文化都属于“非主流”的美国知识分子,却如此忠实于美国价值观,真实地体现了美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二律背反。
他支持奥巴马吗
另一位发表悼念亨廷顿文章的思想家,是40岁出头的《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他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时,师从亨廷顿和另一位政治学大师斯坦利•霍夫曼。扎卡里亚对亨廷顿尊崇有加,称这位诲人不倦的导师为“旷世奇才”。他回忆道,当他还在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就把那篇论及文明冲突的论文初稿拿给他征求意见,而此文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时候,他已经是该刊的执行主编了。
扎卡里亚指出,亨廷顿因发表强调宗教认同的文明冲突论而举世闻名,其实他的早期观点含有更为深刻的创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著作中早就观察到,一些试图走美国式道路的国家,在缺乏法治、成熟的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情况下,把加快经济增长和扩大政治参与作为奋斗目标,其结果是秩序丧失和政治混乱。或许是受其影响,扎卡里亚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非自由的民主”大加鞭挞,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建设没有充分个人自由的“民主”,只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弊端。
无独有偶,同阿贾米一样,扎卡里亚也是一位有穆斯林上层家庭背景的移民学者(但他同阿贾米的关系是文人相轻,相互竞争解释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他出生于印度孟买,至今对印度有某种文化归属感,操印度口音的英语,却强烈地认同美国价值观。在2008年大选中,扎卡里亚成为奥巴马在媒体中的主要吹鼓手之一。
阿贾米和扎卡里亚分属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新移民,又都忠诚于美国理想。作为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们“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立场验证了亨廷顿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归化”成为美国人,不在于他的肤色和宗教、文化、原国籍背景,而在于他是否认同美国的主流文化和政治信仰。
我曾经当面同亨廷顿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的夫人是亚美尼亚人,那你们家里有‘文明的冲突吗?”他认真地回答:“没有,我们俩的思想和习惯都是一样的。”最近我才在报章上读到,亨廷顿先生同亚美尼亚血统的妻子相濡以沫共51年,以她和岳父母都成功地同化到美国社会而感到自豪。正是通过这样一位少数族裔的妻子,亨廷顿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排斥移民的狭隘的“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
由此,我更想了解亨廷顿对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反应,可惜现在已不得而知了。根据他一贯的观点立场来推测,亨廷顿对奥巴马竞选应当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是铁杆民主党人,曾在约翰逊政府和卡特政府中担任过外交参谋的角色。奥巴马同他一样,都曾坚定地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奥巴马是信奉基督教的非洲裔,很好地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完全认同并且生动体现了“美国信条”。从这点上看,亨廷顿似乎应当支持奥巴马。另一方面,在《我们是谁》等著述中,亨廷顿对克林顿当政时期大力鼓吹的全球化,几乎说得上是深恶痛绝,而奥巴马很难同克林顿时代划清思想界线和组织界线。同时,那些亨廷顿所反感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尚未融入主流社会的新移民,多是奥巴马的强烈拥护者,而主流社会中的白人、持保守倾向的选民,仍然大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由此看来,奥巴马当选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是福还是祸,对亨廷顿式的保守思想是凶还是吉,一时还很难说。
亨廷顿学说继续受到考验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亨廷顿曾撰文批驳“美国衰落论”,但晚年亨廷顿对美国文化多元化的前景越来越忧心忡忡。新移民大批涌入美国,少数族裔的生育率高于欧洲白人后裔,是亨廷顿担心美国“变质”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美国因在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而形象受损,最近的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实力和自信心。在阵阵“唱衰”声中,美国还能恢复亨廷顿所经历过的那个辉煌时代吗?
我手头有两篇即将在《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发表的文章,其中透射出新一代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国与世界前途的一种思考,也反映了他们对亨廷顿学说的间接回应。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的优势——网络世纪的实力》,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她认为,当今世界衡量实力的标准是网络联系。拥有最大最多联系网络的国家——美国,将握有全球议程,激发创新能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在21世纪继续称雄。与亨廷顿不同的是,斯劳特不认为人口多寡是国家发展潜力的衡量标准,因为“大有大的难处”,人口越多,问题就越大。美国人口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四分之一,但其先进的教育体系和网络体系能够将中印等国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去。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人口的多样性恰恰是其优势之所在,因为创新产生于激烈的竞争。斯劳特建议,美国人应当努力学习外语,大批吸纳人才,而思想文化上的抱残守缺会导致美国衰落。
另一篇文章题为《专制复兴的迷思——为何自由民主会继续占先》,作者是国际政治学家丹尼尔•杜德尼和约翰•艾肯伯里。如果说斯特劳的文章强调的是美国的思想、文化、社会优势,这篇文章则突出地论述了俄罗斯、中国等所谓“专制国家”复兴进程中的困难和障碍。文章认为,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国家”的外交战略应建立在一个基点之上,即“通向现代性的道路最终只有一条,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自由”。所以美国不应当试图孤立、遏制中俄等国,而应以包容之势,促进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将它们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显然,如果亨廷顿还活着,是不会赞同上述两篇文章的自由化倾向的。亨廷顿要的美国,既不是阿贾米所支持的“张牙舞爪”的美国,也不是斯特劳、杜德尼、艾肯伯里所希冀的“有容乃大”的美国,而是“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美国。那么,奥巴马要建设什么样的美国呢?从奥巴马的政治宣言和诸多美国选民对奥巴马的狂热支持看,美国的政治风向标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偏转。至于偏转多少度,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消息说,斯特劳女士将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果真如此,上述文章就更有政策导向了。无论如何,亨廷顿提倡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明的“独善其身”,前景绝不是乐观的。
一代人的学风
阿贾米在悼念亨廷顿的文章中不无伤心地感叹道:“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里没有人能同他比肩。他为之贡献终生的领域——政治学,已经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夺了。他们是相信‘理性选择的人,靠模型、数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话来写作。”
的确,在美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思想家和理论家似乎不再是同一批人。没有范式、模型、图表、统计,不能发明或皈依“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框架,好像就没有理论了。因此,亨廷顿尽管有举世注目的观点和影响,却不常被归入理论家的行列。他也从来不相信“理性选择”,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亨廷顿的著作横跨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带着厚重的沧桑感,凝聚着人文素养,也渗透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包括环球旅行的观感。他的学风属于那一代人,正统、保守,却包藏着尖锐甚或偏颇的风骨。
不过,阿贾米对美国政治学界一代新人学风的概括,也许过于尖刻了。上文提到的三位新一代政治学者,还有亨廷顿的门徒扎卡里亚,都是思维敏捷、文风清新、观点鲜明,语言也绝无贫瘠之感。当今美国政治学界还是有出类拔萃之辈的,其中一些人正聚集在奥巴马麾下摩拳擦掌,准备为复兴美国而效力。
阿贾米所批评的学术倾向,前些年在中国部分学者和青年学生中颇有蔓延之势。在国际政治领域,一些人热衷于引进美国的时髦理论和自己也未必理解的生疏概念,或者把为人熟知的事实放到美国学者设定的分析框架中,不知所云。
因此,研究亨廷顿不仅有思想意义、政治意义,而且有学术导向意义。对于亨廷顿的理论和观点,永远会有不同解读和不同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渊博的学识和简洁的文风造就了这位勤于思考的学者,让他放射出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