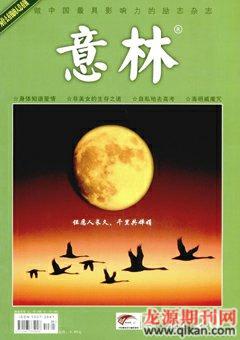福褡裢
许培龙
初春,一弯月牙儿像白色的镰刀悬在西边天际。在它那清辉泼洒下,大漠中的胡杨塆显得无比静谧。
叮当叮当,胡杨林东端一阵杂乱的驼铃声刺破夜空,其间夹杂着汪汪的狗叫。一峰骆驼在那里又蹦又跳。噗!一团东西由骆驼背上甩落到黄沙中。
腾格礼醉眼蒙眬地从30步开外的帐篷里钻出来,连跑带颠地到了骆驼跟前。这是他的坐骑———一峰骟驼。“跳什么!”他的大巴掌在喊声中啪地掴在骟驼身上。骟驼不跳了,狗也不叫了。腾格礼从树干上麻利地解开了缰绳。这时候,腾格礼的弟弟别立格带着五六个弟兄从帐篷那边走过来。“大哥,出了什么事?”“没什么,这畜生贪吃树叶,缰绳套在了树上。你们几个都回帐篷睡去吧,明天起早赶路。”腾格礼独自把骟驼牵回驼群中安顿好,回到帐篷内。他放倒身躯,拽过一件皮衣朝身上一搭,重重地喷出几口酒气,加入了呼噜大作的行列。
这是一支皮货商驼队,一行8人,12峰骆驼。领头的是人称皮货王的腾格礼。他自幼随父南来北往地跑生意,熟汉语,懂汉文;习刀舞棍、踢打擒拿样样都精通;耍霸王鞭更有绝活儿,出手快准狠。腾格礼曾凭借这条鞭勇斗过豹子,还曾一口气抽死过两只闯入羊圈的狼。
许多年来,腾格礼每到这个时节就要率皮货队南下。他们带足皮货和路上的吃用,由居延海旁出发,穿戈壁闯大漠,到大都城换取所需的物品和金银珠宝。一个来回要跋涉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到家前最后一站就是胡杨塆。这里三面环沙,中间有十多亩大的一片胡杨林,掘地三尺便可取水,是宿营扎寨的绝好去处。
清晨,12峰骆驼离开胡杨塆,不紧不慢地前行在弧线柔美的沙梁上。
背后不远处传来了牧羊犬楞虎的吠声。它6岁,身架高大,皮毛黑油油,威风凛凛,十分有灵性,是腾格礼最宠爱的牧羊犬。“楞虎咋没跟上来?”腾格礼问。“它光叫唤,不肯跟咱们走。回去叫一叫它?”别立格问道。“用不着,过一阵子,它肯定会追过来,咱们快赶路,早点儿跨过狼道。”大家都听出了腾格礼着急赶路的心情。
腾格礼所言的“狼道”,在他们前方十多里处,是宽不足二里地、横贯东西二百多里的漠中戈壁地带。每年这个季节,这个地带便成了群狼由东向西大迁徙的必经之地。昨日,腾格礼立在胡杨塆旁的沙丘上观察了这一带泛起的黄尘。经验告诉他,这一带有野驴、黄羊群在奔逃。这也足以表明,很快就会有狼群尾随追来。驼队应及早跨过戈壁带,否则就会遭遇凶险。
天已放亮,楞虎的叫声越来越近。“看看,追上来了吧。”腾格礼得意地向人们说。只见一大团黑黑的东西沿着高高的沙峰飞快地闯过来,一直闯到腾格礼骑的骟驼前面,蹲在沙脊上不停地狂吠。它拦住了去路,12峰骆驼先后停住了步子。“大哥,太奇怪了,它刚才不肯跟我们走,现在又挡路。”“就是嘛,真怪,是不是……”别立格和弟兄们纷纷说。“耽误赶路,会让我们统统死在狼道上。闪开!”腾格礼面冲楞虎,声音像闷雷。楞虎耷拉着脑袋立在一旁。驼铃声又叮叮响在沙海上。
汪!楞虎一声短促的狂叫,一反常态发疯般地跳到骟驼尾后,张开大口叼住骟驼的一只后蹄。骟驼一惊,猛地一蹶子,腾格礼被掀下驼背,四仰八叉地摔在沙丘上。这真是奇耻大辱。二十多年来,他调教过许多调皮的牲口,还是头一次从坐骑上跌下来。只见他满面酱红,忽地跃起,刷地抽出霸王鞭怒骂:“畜生!”嗖,鞭梢闪电般射向楞虎的额头,着鞭处顿时绽开一寸多长的口子,现出白生生的骨头。楞虎嗷地叫了一声,甩了甩额头上的血,转过头发出悲戚的叫声向胡杨塆狂奔而去。腾格礼瞥了瞥腾起一溜儿沙尘远去的楞虎,拍打了几下身上的沙土,翻上驼背。
驼队越过狼道不久,人们回头望去,那一带尘土大起。这次不是在过黄羊,而是在过狼群。“真险哪!”人们惊叹。
天大黑时分,驼队的弟兄已分别和家人们团聚在暖烘烘的蒙古包里,大吃猛喝起来。忽然,别立格急如风火地闯入腾格礼的蒙古包。他哭丧着脸嚷道:“大哥,到处找不到福褡裢!”闻言,腾格礼立刻吃惊地把眼珠子瞪得如红皮鸡蛋,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问:“最后见到福褡裢是什么时候?”“昨天中午还在骟驼背上。”“坏了,这可坏了。”他们所说的福褡裢是腾格礼祖上传下来的家什。一件用黑白棕三色绒线编织成的袋子,柔软且结实,袋的两面各绣有一个碗口大的棕色“福”字,福褡裢因此而得名。几代人做皮货生意都用它来盛金银等贵重物品。腾格礼的爷爷为保护福褡裢曾经差点儿搭上了老命。这一回,里面装着卖皮货后一多半所得。这些收入可供十几户人家花用一年。回去找,是不可能找到的,再说,戈壁带正在过狼群,谁敢闯。“唉———”腾格礼凄怆地长叹一声,抬起眼望了望别立格,无力地挥了挥手说:“去吧,沒指望了。”然后耷拉下双手,垂下了脑袋。
第二年,腾格礼又率队南下,这次同行16峰骆驼、10个人。
要到胡杨塆了。翻上沙梁,远远望去,胡杨林东端有堆黑色的东西。走近了,腾格礼让骆驼停下来,走上前去端详:是一只风干的狗,额头的皮开裂着。“哎呀,这不是楞虎吗?”腾格礼忙跳下驼背弓着腰细瞧:它伏着,头部冲着驼队来的方向,两只前爪环抱在脯下。“这条不知死活的狗,不跟上回家,死在这里干什么?”腾格礼愤然抬脚踢过去。噗地一声,狗皮被撩在一边,狗毛四处飞扬,散架的骨头白森森的。突然,腾格礼目射异彩,颤声惊叫:“好一个狗娘养的!”双手应声刷地向那堆白骨下面抢过去:“啊,福褡裢!”众人失声惊呼起来。
(久久摘自《青年博览》 2009年第5期图/贾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