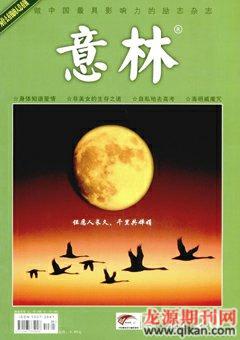萧红和萧军
陈家萍
二萧关系中,萧红一开始便处于劣势。
萧军去世,其妻撰文,总结萧军爱她的三大理由,之一便是她是处女。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萧红所说。萧红不是处女了,在萧军之前,她有汪恩甲,在汪恩甲之前,萧红还有个初恋表哥———这绝非萧红泛爱,而是她追求自由恋爱的决心和行动力。
萧红一直有扮嫩的倾向。在鲁迅家,萧红梳着系有蝴蝶结的辫子,蹦蹦跳跳的。潜意识里,她渴望回到烂漫的花季,但,她显然回不去了———她的身心皆有爱情和以爱情名义伤害她的男人的划痕。可她,偏以这个形象,承欢鲁迅,讨好萧军———萧红在情感方面的积极主动和迎合,思之,令人落泪。
她只是想拥有一份安全的爱啊。从祖父那儿,她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她就对这“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鲁迅夫妇,是萧红可以探手即触的温暖;萧军,是可以伸手攫取的爱。
萧军义气的拳头,曾数次痛击他所不耻者,拳头是他打出的另一种文章。拳头一旦如雨般落在共患难的妻子身上,便凸现暴力的狰狞面目。看见萧红左眼青了一块,梅志和许广平关心地询问,萧红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
这段文字,将人的心攫住。语言暴力比拳腳更为可怕。被打的弱女,扯块谎言维护自尊也不可能!
彼时,萧军恰逢桃花运。
“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作出气筒,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饱受痛苦煎熬的萧红写下一组《苦怀》诗———“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品咂这些诗句,让人深切地触摸到与萧军同居的萧红的痛苦,这种痛苦是这么真切,这么鲜明,永远不结痂。
爱情,是萧红赖以呼吸的精神氧气。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整整6天,没有看她一眼,奶水湿透了衣襟,萧红也没有喂她一口奶。萧红狠心堵住母爱决口,她更看重萧军的爱情!她抛掷了她本应负重的累赘,指望轻盈如蝶,飞向爱情啊。
萧红在香港病危时,交代后事,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女儿,萧红何曾忘却一日。
萧军绯闻不断,萧红的痛苦无处可藏。1936年7月,萧红接受了鲁迅的建议,赴日本。萧红的离开,是希望借助别离的空间,挽救濒临灭绝的感情。
四十余年后,萧军同从维熙说到萧红:“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
萧军说萧红的心太高,明褒实贬,意指她不切实际,文学大于生活。我不能赞同,从那些自日本寄回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萧红低首尘埃的手势,她的言行,堪称贤妻。
已怀有萧军骨肉的萧红,遇上生命的劫数———端木蕻良,将其视为情感出口,结束与萧军的同居关系。
提及6年爱情生活,萧军何其冷静:“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而萧红,却给萧军留下《生死场》的版权。
(纯净摘自《西安晚报》 2009年8月7日图/孙洪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