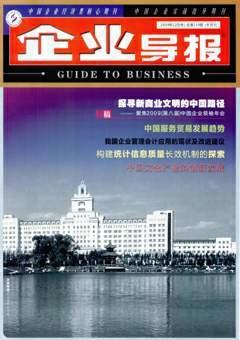荒岛思想实验诸责难与应对
李 震
【摘要】 人们相互之间如何达成正确理解是语言学转向后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戴维森从错误表达达成正确理解这一极端情况出发,从其内容与形式分析了理解所必需具备的核心环节:交流,而不是约定,直击了语言是语言共同体的约定的日常理解。这将有助于理论界进一步深入探讨语言的本质,推进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思想实验;约定;前理论;后理论
唐纳德·戴维森的思想是围绕彻底解释这一图景展开,认为交流中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通常所认为的语言,即句子与其意义的约定集合,就戴维森的该拒绝及其建构的语言交流模式疏导出他的交流理论。戴维森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来拒绝看似语言交流所必需的约定。他假设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被一起在一个荒岛上,没有共同语言这一点并不会阻碍他们的交流:当其中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另一个能够理解说出的句子的意义。这一实验显示,在不懂得对方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对于句子意义的约定,正确理解仍然可以达成。如果语言被看作句子解释的约定归属,它就不是交流所必须的。由此,戴维森拒绝了作为约定的语言。
在戴维森的荒岛思想实验中实质出现的只需要双方的交流:说话者和解释者,它有助于我们摒弃一些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中看起来必需的因素,但是,这同时也会面临问题:这个实验是否适用于日常的语言交流,如果不适用,戴维森对于约定的拒绝就是失败的,他力图把这一模型转入日常生活,“解释的难题不仅是对另外一种语言而言的,而且是对同一种语言而言的”。他通过处理语言误用来展示其对于约定拒绝的合理性,语言误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荒岛模型。
为了避免对于语言一词的使用,戴维森使用了两个新概念“前理论”和“后理论”来说明解释。前理论包括交流者带入解释的一切,当说话者说话时,解释者用他的前理论来形成后理论。后理论是按照好意原则对说话者当前所说的实际解释,在最常见的环境中,前理论和后理论或多或少是一样,这就是戴维森所理解的说话者的语言。戴维森喜欢强调词语误用,虽然它们可能构成问题,却没有一个对解释理论真的构成挑战。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语法错误,仅与前理论相关,给出意义的是后理论,并不参照判定这些现象为错误的约定。在实践上,戴维森并不拒绝约定的作用。“我们没有时间、耐心或者机会为每个说话者发展出一个的新解释理论”。但在每天的生活中,如果已经接受了彻底解释,约定就不是必要。形成后理论,实际上也就解释了人们的语言或者话语。约定虽然有着实用的价值,但并不是解释和交流的在其本质上所必需。这个设想遭遇到了各方面的责难:
首先,戴维森所描述的交流被认为只是“说话者的单边”行为,“语言误用是关于交流,交谈,是说话者和听者的互相作用”。这一责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戴维森关于交流的整体架构。从彻底解释的荒岛实验中确实没有一个相互作用的描述。戴维森一开始也以语言学家的田野调查建立翻译手册和学习一门语言作为彻底解释的例子,表面看来,这两个例子应该更显示出一种单边倾向。
戴维森阐述自己理论建构目标时曾经说过:“我们想要有这样一种理论,它满足对真理理论的形式上的限制条件,并获得人们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就我们所能告知而论,使库特(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话尽可能经常地是正确的”。 “同意”也是奎因的原始翻译中的重要术语。当语言学家记下“兔子”作为对Gavagai的尝试性翻译以后,他必需以某种方式询问土著来检验该尝试性翻译,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下一次兔子出现时说Gavagai并观察土著的反应,看看土著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一话语。这种方法显然是达到同意的一种基本方法,从戴维森的外部论(externalism)立场,没有拒绝的理由。戴维森并没有忽视说话者和解释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次,是关于前理论和后理论的区分是否正当的讨论。达米特认为“我们必需区分三个东西:语言;语言的意义理论和一个二阶理论”。达米特把语言定义为“言语交流的一种存在样式”,意义理论则是“属于它的表达的内容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以间接的说明语言行为,这里间接是说意义理论“自身不包含对说话者以及说话者语言或者非语言的信念、意向或者行为的指称,它把特定的理论术语如‘真应用于语言的表达”。必需要有理论的不同等级,必须要有一阶理论,否则在逻辑上必然引起无限倒退。
戴维森对前理论和后理论的叙述是这样的:“对于听者,前理论表达了他事先准备怎样解释说话者的话语,后理论则是他实际如何解释这一话语的。对于说话者,前理论是他所相信的解释者的前理论,后理论则是他希望解释者所使用的理论”。按照这段引文,从说话者方面看,他的前理论应该是二阶理论,它是关于解释者的前理论的理论。听者的前理论应该是一阶的,可以被描述为听者对别人如何对他说话的一般期望的集。后理论也应该是二阶理论,它们是在前理论的背景中建构起来的,是前理论的修改版。说话者将听者置入自己意向之中,说话者并不是独白,而是力图使听者解释自己。对说话者前理论的分析构成冲突的中心环节,戴维森对说话者与听者的前后理论的描述的差别是与他一再强调的意义与信念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前理论与后理论的理解不能够在彻底解释的框架之外进行,听者对于说话者的解释是遵循彻底解释的要求,在对听者的描述中之所以没有出现相信、意向于等二阶概念是因为他已经处在认为说话者句子为真的一般信念态度之中。前理论与后理论并不象达米特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是长期理论(long-range theory),一个是短期理论(short-range theory),两者都是变动的短期理论。达米特长期理论与短期理论的区分是想说明长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约定构成(具体的论证见评论)。它揭示出戴维森后来所承认的错误:“没有充分强调说话者群体内部大量的一致性所带来的实践的便利性”。
但是,达米特本人显然把约定所具有的实践的方便性与戴维森所要寻求的对理解(解释)的必要规定性的目标混淆在了一起。在我们的意识中的那类理论在它的形式结构上适合作为整个语言的理论,即使它的预期应用范围小得难以察觉。回答是当某时或者某地一个词或者短语取代了另外某一词或者短语的角色,这个角色的所有责任,以及它所蕴含的与其他的词、短语和句子的所有逻辑关系,都必须为后理论所伴随。一旦掌握到马勒普罗太太说‘墓志铭时她意谓的是‘绰号,就必须给予‘绰号‘墓志铭在其他许多人那里所具有的能力。只有一种完全递归的理论能够公平对待所有这些能力。”相应的前理论也应该是一个类似的递归理论。
戴维森通过荒岛这一思想实验对我们通常的语言观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一冲击是否能够在更多的日常的语言使用中应对回激是一个更加沉重的理论任务。相信即使细节部分仍需修改,从原则上这一冲击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