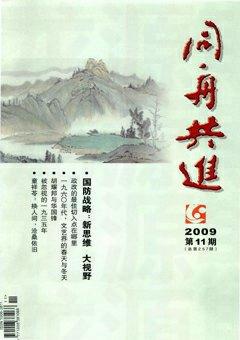伶人谏“税”
郭 梅
“苛政猛于虎”一向是万恶的旧社会的标志。其实如抛开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之类的理论,单纯从猎奇的角度看,万恶的旧社会的统治者们为了多收点税而绞尽脑汁、机关算尽,也够难为他们想的,有的税赋征得还颇具几分幽默色彩呢。
比如古罗马时代,许多城市的街角都摆放着市民拿出来的尿瓶,制革工和漂洗工会定时买走尿液,拿回去帮助制革和织布。当时的维斯帕辛皇帝出了名的爱财如命,居然把征税的脑子动到了尿瓶上。他颁布法令,规定买卖尿液的双方必须缴纳交易税。这种荒唐又蛮横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弹,连他的亲生儿子泰塔斯都向父亲提出了异议。维斯帕辛皇帝不露声色地听完了儿子的陈述,然后把一枚银币放到这位年轻人的鼻子下面,问:“有异味没有?”泰塔斯迷惑地摇摇头。维斯帕辛接着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话:“没有异味是不是?儿子,我告诉你,这银币就是从尿液中挣出来的!”
比起外国人,中国人征税的本事绝不落下风。比如五代时期南唐辖区内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张崇,以索钱无厌出名,庐州百姓敢怒不敢言。一日,张崇接朝廷命令去江都(今江苏扬州)向上级主管述职,庐州百姓以为他会调任,纷纷庆幸地议论:“渠伊想不复来矣!”(“渠伊”是当时对人的鄙称,意为“这家伙”——编者注)可惜天不遂人愿,张崇很快就回来了。他听说了百姓的议论,恼怒之余灵机一动,挨家挨户按人头征收“渠伊钱”。第二年,张崇被御史弹劾,匆匆赶往都城建康面圣对质。庐州百姓欣喜若狂,但被去年的“渠伊钱”弄怕了,不敢私下议论,只是在路边对视一眼,捋一把胡子以示庆祝。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张崇在半路接到新的诏令,仍做庐州“州长”。他立马新征“捋须钱”。瞧瞧,“渠伊钱”和“捋须钱”,多有创意又富有深意!比维斯帕辛的尿液交易税高明多了,也文雅多了。
不过,夜路走多了,总是要碰到鬼的。张崇在庐州的种种劣迹多少传进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不大满意。后来张崇到建康觐见,闲暇时去看戏放松,却被几个优伶狠狠地戏弄了一番。那天的戏是优伶们即兴编的,演一个新死的鬼魂被带到阎罗殿接受审判。判官翻着生死簿说:“作孽太多,罚焦湖百里,一任做獭。”“做獭”明显是一种讽刺,其一取声,即“作践”、“糟蹋”之意;其二取意,水獭捕食鱼类极其贪婪,正如张崇盘剥百姓一般凶猛,且至死难改本性。在座一同看戏的都听出了优伶的言外之意,不觉莞尔,齐刷刷把目光投向张崇,张崇脸上却无丝毫羞愧之色。张崇好歹也是朝廷命官,优伶有胆子在太岁头上动土,当面戏弄他,估计有后台撑腰,说不定这后台就是对张崇不太满意又想在朝堂上给他留点脸面的皇帝陛下。可惜了,张崇似乎对这种旁敲侧击毫无表示,真是辜负了皇帝的良苦用心。
张崇的同僚、魏王李知训担任宣州太守的时候和张崇半斤八两,盘剥百姓无度,苛捐杂税比牛毛还多。尽管是同族的叔伯兄弟,南唐皇帝对他也不满意。这个李知训的处境比张崇还倒霉一点,他是在御宴上被优伶指桑骂槐的。话说李知训蒙皇帝接见,不但没对他的糟糕政绩有些许微词,还给了他参加御宴的殊荣。御宴中,两个经过皇帝授意的优伶走上戏台,一个穿着绿色官服,涂成个大红脸,还粘了把红胡子,明显是扮演鬼神一类的角色。另一个伶人便问道:“你是谁?”绿衣人回答:“我乃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顿时全场大笑——笑声持续了好几百年,直到明朝时,狂人李贽还边笑边评点:“恐天下土地忙忙迁移者多矣。”
从以上两例看,南唐的伶人们嘲弄重税的本事不赖,不过那是因为南唐的税特别重(其实横向比较的话,南唐的税收状况也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五代兵荒马乱,打仗比吃饭还频繁,军费的开销当然比太平时期大多了),他们经常借登台的机会发发牢骚罢了。伶人们不但在皇帝的授意下讽刺那些爱课重税的官员,连皇帝自个儿征税征得过分了,他们也要秉承大无畏的精神,说上几句呢——
南唐升元年间,李昪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拿商人开刀,征收极重的商业税。建康是商铺云集的交易集散中心,又在天子脚下,被当作了征税的示范典型,商人受到的打击尤其惨重。这年盛夏苦旱,建康城里一连几十天都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李昪在纳凉晚会上苦恼地询问手下:“郊外都下过大雨了,唯独都城几乎粒雨未下,何也?莫非是朕做了什么缺德事,违背了天意吗?”这问题显然是个烫手的山芋,不好回答。就在大家苦思答辞时,优伶申渐高讲笑话似地答道:“大家(对皇帝的称谓)何怪?此乃雨惧抽税,故不敢入京尔。”李昪听后,开怀大笑,当即下诏免除了京城的大部分商业税。也巧,当晚后半夜,建康城中就下起了大雨。
后来,南唐的大好河山由后主李煜接手掌管,这时国家财政状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除了每年用大把金银向日益强大的后周买平安,还得维持惊人的国防开支。另外,李煜自己花在“情调”上的开销也是个无底洞,别的不说,光是那朵供窅娘起舞的纯金大莲花就制造了多少财政赤字?在没有国债和国际金融贷款的古代,填补国库亏空的唯一办法就是加税。李后主下诏,规定民间凡是碰到鹅下双黄蛋或柳絮结成大团的“祥瑞”之兆,都要交纳一笔税金——李后主不愧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想出来的税名也带着股不切实际的浪漫色彩,世上哪来这么多祥瑞为南唐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作贡献啊。于是,许多伶人以调侃的口吻念道:“唯愿普天多瑞庆,柳条结絮鹅双生。”
说了这么多收取重税的陈年旧事,我的感觉是,古代的百姓也忒老实了些,只知道流着眼泪砸锅卖铁拆房鬻儿地凑齐税金,所谓的反抗不过是借少数优伶的嘴巴发发牢骚,只有到了沦为纯粹的“无产阶级”的地步,才会以农民起义的方式,表达心中郁积的不满。怎么就没人认真打过偷税漏税的主意?唐宋时期,为了少交点人头税并节约养育子女的成本,贫苦人家往往只养育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多生的孩子不是送人、丢掉、卖掉就是直接溺死。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里这样描写:“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赋税之外,还有徭役,这位老人忍痛自断手臂,还不敢让人知道,为的就是逃兵役。新丰折臂翁们要是看到了今日的富人、明星偷税漏税甚至骗税的花招之多之高明,恐怕是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笔者不禁假想,不知伶人申渐高们如果生活在当下,会有怎样的表演?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