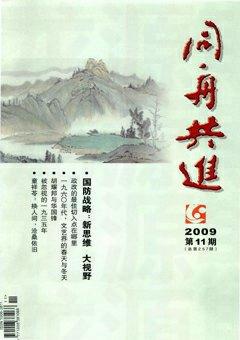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当今学界的两难问题
萧功秦
作者按: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荣休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一直很深。他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虽然知识分子自己也可能会觉得无权无势,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于话语权。“文人的笔有时比国王的刀更有力量”,而话语权又与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将会是我们交谈的内容。
美国的自由主义已变了味
墨子刻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极端自由化运动(即笔者下文所称的“世俗自由主义”)持相当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现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已变了味,社会舆论越来越受到学院主流思想的影响,这种主流思想把平等与个人自由绝对化,比如同性恋结婚,以及在小学一年级教科书中加入传授男女性知识的内容等,他认为实在荒唐之极。在他看来,要绝对自由而放弃文明教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趋势,这个趋势愈演愈烈,他对此深感忧虑。
对于美国这股正向世界各地蔓延的性泛滥思潮,我第一次感受到是在新加坡。在那里的网上我居然看到了西方人与马杂交的图片,这使我太震惊了。人不是万物之灵吗,怎么一旦获得无限自由,不是向高层次发展,完善自己的人格,而是向低层次走,越来越回归动物化?
当时,我与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学者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洁,“自由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不能善用,没有了分寸,就会变成与自由主义相反的东西”。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人性是有弱点的,人需要某种东西来约束自己,文明修养就是约束人们、使人们获得自由权利的同时,又不至于走向动物化的重要平衡因素。
我认为,相对于欧洲,美国的世俗自由主义表现得特别强烈,并很可能逐渐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实际上,美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和“美国式的民粹主义”一直是美国世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文化具有排斥或蔑视精致文化的价值倾向与态度,而美国的普选民主使人数众多的草根阶层对于谁上台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又使政治家把自己装扮成世俗化浓厚的平民主义者。几年前我在美国访问了一位众议员,他说,“只有我们看上去像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时,我们才能当上议员”。这里表现的正是这种反精英化的世俗主义。
从“一夜情合法论”看中国现代文化的程序漏洞
墨子刻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洞察,对当代中国也有启示,因为中国一直深受美国文化而非欧洲文化的影响。从麦当劳到迪斯尼,连宾馆总机小姐的第一句话,不管你听不听得懂,就是一大套英语:“May I help you……”然后才讲汉语(即使在台湾也并非如此)。我戏称当下中国是“美国文化圈”而非“欧洲文化圈”,流风所及,中国人的自由主义话语也深深感染上“去文明化”的世俗格调。在我看来,欧洲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多少保留着贵族传统或古典传统的流风余韵,而美国则更多地表现为牛仔的自由放任。
为了说明中国流行的自由观缺乏文明因素的平衡,我告诉墨子刻,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性学女学者,在公众讲演时,公开支持青年人中的“一夜情”。她对青年男女“一夜情”的唯一忠告是不要怀孕,要注意个人卫生而已。我说,令人担忧的不是这番话本身,在一个多元化的正常社会,发出各种奇谈怪论不足为奇。但我特别忧虑的是,中国自“五四”以后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发展到现在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即本土文化已完全丧失了抵制这种不负责任言论的文化资源,这就出现了文化的程序“漏洞”,反道德伦常的文化“病毒”就特别容易感染到中国来。把极端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价值,与把某种“左”的理想教义作为普世价值一样,都会产生可怕的文化后果。
其实,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不久前我的一个亲戚把自己读初一的孩子批评了一顿,让他在房间里反思自己的过错。不到半小时,民警就上了门,原因是孩子已经打电话报了警,说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侵犯,弄得我这位亲威莫名其妙。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
为什么当下中国青年人容易接受美国式“去文明化”的世俗自由主义?一方面,自近代以来,旧的文明价值被人为地铲除,中国人的自由启蒙价值中,本来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新的主要从美国过来的外来思想中,又缺少了对文明德性的关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把文明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限定条件与平衡因素来认识。
墨子刻的提醒非常及时:应该回归德性与文明。当然,中国没必要把西方的贵族文化作为自己的文明资源,但却可以从传统儒家文化中获得。正如墨子刻所说,为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儒家本身也需要发展与变化,新儒家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中国进步的源泉在哪里?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儒家传统。墨子刻用了一个很重的字眼批评鲁迅。他说,鲁迅“糊涂”了。“他怎么能这样看待传统,把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看得一团漆黑?《狂人日记》中,狂人看到的历史,只剩下‘吃人两个字,这种对历史的理解怎么不糊涂?”墨子刻认为,这种“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儒家中有“乡愿”,也有腐儒,但谁能否认儒家文化在塑造中国人的美德与文明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能用一个“礼教吃人”把两千年的文明结晶全部否定掉?墨子刻强调,他所批评的并不是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质疑中国那么多知识分子居然会如此崇拜鲁迅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价值判断。
我说,最近我在看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他写到,“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己”。在戴震看来,礼并不是用来无条件地“尊君重上”的,而是作为一种约束、节制、平衡情欲的文化功能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礼,就不会走到偏执的极端。从戴震思想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在近代以前,内部其实还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戴震就是中国士绅阶级对自身文化具有反思批判能力的代表人物。
墨子刻很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认为早在戴震以前,儒家内部就有自我更新的努力。荀子就曾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很早就对宋学走向僵硬化、教条化进行过批判的反思。墨子刻多次提到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他说,儒家文化相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化而言,是一种更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文化,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一样。中国主张“打孔家店”的“五四”知识分子却忽视了这一重要区别。
我说,可惜的是,中国现实生活中儒家的资源已丧失殆尽。共和国成立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从小已不再接触儒家经典,人们并不了解孔子的思想。虽然近年来,在官方、民间,知识分子与百姓大众都有一种回归自身传统的价值走向,然而在理性层面上,谁也说不清传统文化是什么,儒家有什么精华的东西值得我们一代代保持下来,这是当下中国精神世界的困惑所在。
墨子刻并不完全认同我的看法。他说,儒家的文化早已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由于“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式的文化大扫荡而清除殆尽。他认为,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重视家庭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文化中十分美好的东西。墨子刻的夫人就是华人,他说他就是台湾人的女婿,很为台湾人的家庭文化着迷。
这让我想到在电视里看过的情景:四川一个女孩被拐到内蒙农村达17年,当女孩的兄长与姐姐终于赶到内蒙见到已不会说话的妹妹,并看到妹妹住的非人居住的窑洞环境,其中一个哥哥当场昏了过去。看到这个场景,我自己眼泪也快出来了。这是一个多好的哥哥!而这,不正是中国人家庭观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吗?在城市里,家庭观念已淡化了,但在农村,仍保持着最深厚的家庭文化观念。
墨子刻特别强调的还有中国人的“克己复礼”观的正面价值。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忍辱负重,为了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普通中国人身上对家庭的责任感,为家庭幸福而吃苦耐劳、自强不息,都与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有关。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媲美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精神。中国有着如此强的动力,与世界上一些麻木的民族不同,其实这就是中国进步的源泉。
此外,中国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国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君”的政治观,中国人“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与道德遗产。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是批判
我们又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是思想史研究中绕不过的老问题。我问墨子刻,在不同的文明中,都有类似于西方语境中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人士,此类人有什么共性?如何找到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来概括他们?
墨子刻用了一个精彩而简洁的定义,那就是:受过教育,从而能运用知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能力传播自己的意见,在社会上具有威望,这种威望使之具有话语权与影响力的人们。在墨子刻看来,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不同,他们掌握的不是政权,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话语权,以及由于话语权而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墨子刻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道德主义相当强的民族。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宣言。然而,墨子刻也认为中国文化中弥漫着强烈的泛道德主义气氛。“以道德为己任”也有消极面,那就是忽视古人所说的“事功”精神:凡是主张功效实务的,在儒家文化中都不具主流地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变成了持续不断对政府与在朝者进行道德批判。任何肯定政府业绩的做法,都会被视为丧失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为批判而批判成为知识分子的为人之道。这并不正常。
我说,其实我的一些自由主义朋友,就是明确主张“知识分子只批判,不建设”的。这种观念可能有两个来源:首先应该承认,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独立于朝廷的以道统为己任的社会舆论气氛,当然也有其积极意义——这种以道德标准臧否人物、激浊扬清的士大夫清流舆论,连帝王也要让三分。东汉的党锢之祸,明代的清议,都体现了这一批判传统;其次,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传统,还与受到西方道德主义知识分子观念的影响有关。西方有一个权威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把世间的一切不合理问题均视为道德问题的人们”。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
普世价值:当今学术界的两难问题
我说,中国学术界正在关注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有些官方学者否认人类有普世价值,激起了轩然大波。在这里,我想超越当下中国讨论这个问题的具体的政治背景,从认识论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的各种价值都是人类面临困境后有感而发的产物,并不存在超越一切文化的普世价值。然而,另一方面,我又深知,中国非常需要从外部文明的价值中,尤其是从西方文明的平等、博爱、自由、人权的价值中,获得好的启示与借鉴。否认价值的普世性,无疑会给那些拒绝中国融入世界、拒绝西方世界美好事物及新价值的人们以有力的借口来搞闭关锁国。
面对这一两难问题,应该怎么办?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如同推导数学公式一样,推导出构成全人类美好社会的普世价值。对此我始终保持着警惕。在我看来,一方面,普世价值一旦被理性确立起来,固然可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容易把自己扭曲的、不真实的浪漫想象的移情物,如人民公社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或否定市场竞争的共产风,或西方特殊历史文化中演化出来的具体政治模式,披上“理性与科学”的外衣,提升为“普世价值”。这种乌托邦无疑会造成人类的大灾难,有过“文革”经历的我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右”的或“左”的“普世价值”或“普世公理”,都不能不予以警惕。我们宁愿从自己的实践中,而不是从理性的推演中,去寻找自己民族的理想道路。从现实看,“普世价值”的问题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主张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的人们,会以此获得推进民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却也让极左派得以宣称自己追求的那一套就是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在两种普世价值观的强大压力下,务实的改革者会左右为难。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淡化这场讨论,我很同意一位上海学者的观点,那就是提“共享人类文明的好的价值”。
墨子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有没有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构成世界不同民族与文化普世性的东西只有两件,一是认识事物时必须具有的“开明态度,一是对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的尊重。
墨子刻认为,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想建立起一种理性的政治哲学,仅仅偏重“试错”的方法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对自身信仰的意义和根源有更深刻的认识。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讨论什么应该保留,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应该修正。
在他看来,只有有了这种清明的理性辨析力,加上对不同意见表达自由的尊重,才能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接近真知。有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避免乌托邦与浪漫主义。任何文化中的人类都是如此。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