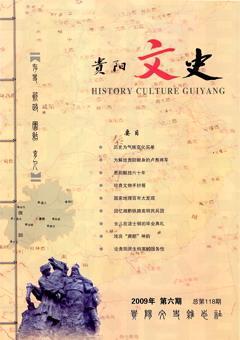细数黔军抗战
梁茂林
今年9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贵州草鞋兵》引起熊源先生的注意,打来电话,希望笔者介绍一下齐赤军研究抗战史的情况。遗憾的是,齐赤军没有等到新书面世,今年7月4日,因车祸,在睡梦中悄悄地走了。作为本书合作撰写者的笔者应该向读者说明。
这部纪实作品以黔军从1937年参战起到抗战1945年胜利的艰辛历程为主线,以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图文史料为依据,回归实事“现场”,重评历史事实,用真实的细节说明黔军的参战史,既便于读者享受阅读信史的乐趣,又希望能引起读者多方面的求索。回顾齐赤军参与撰写本书的过程,可以这样说,这部书稿用尽了他近40年大部分业余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当一段时期误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基调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变成单方面宣传共产党敌后抗战和党内路线斗争史。这样,齐赤军小时候能看到的抗战史变成了“半边”抗战,正面战场没有了,国共合作没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了只有斗争、没有联合的空洞口号,军事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多描写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磨擦”作战,而不是对日军的作战。
这种认识误区一直沿续到1985年9月3日,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上讲话,对国共合作抗日作了明确的表述,首次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并再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这才为事实上存在的国共合作抗日定了调子。从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因为改革开放,社会不断进步,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档案资料大规模面向社会公布,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期。1995年,江泽民在莫斯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上,把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地位为主线,发表了讲话。这以后,学术界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总体上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对日抗战,基本上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略防线,保住了西北、西南等半壁江山,学术研究回到了客观存在的事实。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这些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战后数十年间,由于在“左”倾教条主义主导下,对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没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此,学界基本结束了称对方为“匪”的历史。
齐赤军不是专家,他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这么上心呢?是什么原因引起他对抗战的关注呢?这是人类的理性、社会的良知、民族的大义、山东汉子和贵州人的血性,驱使他念念不忘所见所闻的这些撼人魂魄的史实。
他1956年生于贵州省遵义市,在贵阳长大。父亲齐呈祥,山东省临清市人,是1943年参加八路军的抗日老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军委授予他自由解放勋章。母亲是贵州省习水县人。从小听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故事长大的齐赤军,1972年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就在滇缅抗击日军的战场一滇西。服役期间,曾在驻地附近接触过不少亲历滇西抗日的军民,也认识不少战后滞留滇西,在此娶妻生子、安身立命的黔籍老兵。当时就在他的心灵深处立下誓言,决心要为这些无名的抗日老兵立传,真实地介绍他们的战功,以告慰这些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奉献生命和热血的“草鞋兵”。
1976年退役后,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去世前任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但他一直不改初衷,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多方寻找黔籍军人的抗战史料,攻读多部黔军史、黔币史专著,并多次回访滇西老兵。2005年,齐赤军撰写了关于滇西抗战的论文:《碧血洒松山抗战垂青史——松山攻坚大战中的贵州部队》(发表于该刊2005年第4期),在去《贵州文史丛刊》投稿的路上,和中学老师即笔者相遇。我们讲着讲着,不谋而合的责任感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于是我们分工合作,经过近5年的努力,在完成《贵州草鞋兵》的撰写任务的同时,先后在《贵州文史丛刊》、《贵阳文史》等报刊发表多篇关于黔军血战滇缅的专题论文。尽管他现在已经悄悄地走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凝聚的几代军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感悟,他的生命,却在本书中得以延续和永生。他分清了是非,认真反思这段不幸的历史,去爱那些需要爱的抗日军人,理性分析那些摧残这种爱的行为。他尽了一名士兵的责任。
齐赤军最大的遗愿是希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纪念塔”能在原址重建。他说,“纪念塔”体现了贵州精神。
责任编辑:熊源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