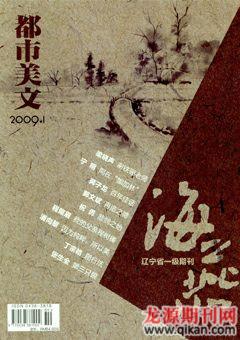我的爸爸程树榛
程黧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黑龙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供职至今。在海内外发表散文作品数十万字。
父亲曾经为我的一本书作序,以父亲的名义。那个序写得非常好,我喜欢。就想:等有机会,我一定还他一个序,当然,谨以女儿的名义。
终于,爸爸说,这套文集的序,就由你来写吧!
可是一提笔,我却不知如何说起了。我的德国姐夫Stefan说:“爸爸这一辈子,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也是非常丰富的,一般人不会有的,是不是?”
是啊!我们的爸爸,一生宁静淡泊,远离名利,但却积极、上进。这是我们三个女儿和女婿对他一致的评价。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总是爸爸桌前伏案的背影。我甚至还记得家里养的小猫都是喜欢爸爸的写字台的,爸爸在桌上写,小猫就和他面对面坐着,见到爸爸手中的钢笔在飞快地移动,还以为是在逗它玩,就不停地去抢爸爸手上的笔,有几次还把爸爸的稿纸抓坏了——那个年代生活艰苦,爸爸的稿纸都是各式各样的,但是爸爸伏案的背影在漫天大雪的东北却充满了温暖和安宁。我是多么怀念我的那些少年时光啊!
那时偶然看到姐姐的笔记本上有爸爸的题字:“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切记!”我羡慕得要死,但是笨拙的我竟然不知道向爸爸要求给我也写一个,而是绞尽脑汁用一张比较透明的纸把爸爸的字描下来,然后,铺在自己的日记本扉页,用铅笔重重地涂印一遍,最后再用钢笔把扉页上的痕迹描写下来,就成了爸爸的笔迹。
还记得当年姐姐不负众望,以齐齐哈尔市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时,爸爸即兴赋诗一首:
送长女赴北大兼示二女小女
送女上北大,负笈入京城,临行眷眷意,嘱咐又叮咛:
一要品行端,磨砺思想红,立身要正直,立心应为公;
二要身体好,锻炼永不停,身心得康健,破浪能乘风;
三要学有成,苦练基本功,孜孜勿倦怠,努力攀高峰;
对师多尊重,对友应谦恭,团结而互助,共赴新长征。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于富拉尔基
我至今还保存着这首诗的原稿,而这首诗的每一句,早已印在我的心里,从十几岁到现在,不曾忘却。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我少女时代的人生准则。还有一句话:“勤可补拙,俭可养廉”,也是从小爸爸告诫我们的。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爸爸就是这样一直用正派的、正直的、充满理想的精神来引导我们的。这种精神过于纯粹了,以至于我们经常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我没有丝毫的遗憾。也正是我们姐妹身上的这种带有古典主义的浪漫气质,才使得我们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和爱护,在事业上和生活上不断收获着幸福和财富。
爸爸不到三岁就失去了父亲,是祖母含辛茹苦将他带大。为了让爸爸读书,祖母一直守寡,将最好的土地变卖,因为她的儿子是那么喜欢读书。爸爸也没有辜负祖母,他自幼聪慧,小学只是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就考上了家乡最好的中学——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爸爸酷爱文学,十七岁就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作品,本来他的愿望是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且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当时正是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年轻的知识分子。爸爸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想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当中,他毅然选择了工科院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前身是北洋大学的天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
在大学期间,爸爸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而且他在大学毕业紧张的实习中,竟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他的长篇处女作《大学时代》。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五十年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爱情,他们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纯洁灵魂。
大学毕业,爸爸因为右派言论被发配到北大荒,但是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泯灭他的创作热情。相反,他的创作灵感如火山爆发,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最艰难的时期发表的。
我上大学之前,爸爸就已经很有名气了,尤其是在我们那个重工业城市——富拉尔基,我们的那个工厂——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那是全国第一大厂,仅职工就有一万多人。在那里,我们爸爸的名字妇孺皆知。因为爸爸在大学刚刚毕业不久就写出了大型话剧《草原上的钢铁巨人》,那时他才二十四岁,不仅厂话剧团演出,而且还由佳木斯市话剧团参加全省调演。后来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在全国引起反响。最引起轰动的是这部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当时剧组浩浩荡荡开进工厂、江畔,大家奔走相告、万人空巷。人们见到了《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刘世龙)、著名的李向阳(郭振清)、美丽的张圆等人,这些人都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大明星啊!当时我们家真是门庭若市,这些明星经常从招待所走到我家,他们和爸爸聊剧本,和我们开玩笑,还讲一些有意思的幕后花絮……
那时候刚刚有电视,齐齐哈尔电视台还播出了我爸爸写作、以及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片段。后来成为了我丈夫的洪涛还记得当年邻居们都聚在他们家看(那时有电视的人家很少),以至于他认识我时还开玩笑说他先认识的是我爸和我妈。
那些时候经常有全国各地大出版社的编辑来我们家,向爸爸组稿,我印象中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范政浩叔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景峰先生,以及工人出版社、包括我现在供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等。许多文学界的前辈都去过我们在富拉尔基和哈尔滨的家,像唐因、纪叶、蒋子龙、谌容以及电影界的严恭、朱文顺等。因为大多数人先认识的爸爸,以至于后来更年轻的何志云先生、高洪波先生等人见到我时经常开玩笑让我叫他们“叔叔”。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白楼招待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市六铺炕工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地址,这些都是爸爸出差改稿住的地方,那时只能写信,上面的地址,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了。现在这些地址都是我背着写下来的,一字不差。它们已经嵌入我童年少年的血肉里,因为我是那么盼着爸爸回家。他每次去改稿,都要走两三个月,我们三姐妹和妈妈奶奶在家里等待。爸爸回家的日子,就像是我们孩子的狂欢节——他会带来很多漂亮的花裙子和糖果,邻居的孩子们也跟我们一样盼望。
而我们家的三姊妹也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而在当地红得发紫。但是,似乎爸爸从来不觉得我们有多出色,总是严格要求,并且以身作则。他认为看电视是浪费时间,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很少看电视,即使我什么都不做,也不看一些无聊的电视,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
印象中小时候父母很少表扬我们。我们成绩好,似乎是理所当然。高考时我因为第一志愿没有填报北京大学而失去了机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尽管爸爸安慰我说北师大的中文系可以和北大中文系媲美,但我好多年都觉得低姐姐一头。尤其觉得自己给爸爸丢脸,因为爸爸认为我无疑是要上北大中文系的,于是,“北大”就成了我年轻时心里的痛。
印象中爸爸从来没有对我们姐妹发过脾气,只是在姐姐看到邻家女孩子编织窗帘和桌布等手工也买来线要织时,爸爸阻止了,我清楚的记得,爸爸说:“我不喜欢女孩子只会干这个,这是没出息的!”但是,姐姐仍是偷偷地编织了一些东西,爸爸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太了解爸爸,他不会去强迫任何人,与其说他有善解人意的好心肠,不如说他是有着自由的平等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
就像我当年迷恋小提琴,爸爸毫不犹豫地托上海的朋友给我买来,而且亲自找人教我。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在七十年代,十九块钱相当于妈妈半个月的工资。
在通往深邃的、理想的、人道主义意义的征途上,我们姐妹和爸爸是永远的知己,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我们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不会专横、不会苟且。我们经常共勉的,就是那句著名的语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绝对不是我矫情。
所以,不论爸爸当所谓的“官”,还是平民百姓,他从来不害人,做事坦坦然然。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没听他讲过任何人的坏话,即使是那些背地里诋毁他的人。他曾经无私地帮助过很多人。我印象极深的是一个女作家,在她很年轻的时候爸爸就帮助她调出她插队的农场,但是后来因为她对于工作的一些要求没有被上级部门接受,而当时爸爸是领导,她便归罪于爸爸,背后恶语伤人。常常有人来问,但爸爸几乎不去解释。当然文坛上大多数人知道爸爸的人品,有很多人,见到我总要说说与我爸爸的友情,和对我爸爸良好口碑的赞赏,所以,我从来都是为父亲自豪的。
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大度。二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来到哈尔滨,主动要与爸爸合作将爸爸的一个长篇小说改成电视剧,爸爸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了他,包括一些采访录音带。但是后来这个人背信弃义,竟然私自利用这个素材改编了一个自己的“电视剧”,爸爸很生气,觉得此人很不君子,当时文学界的人知道后都谴责这个人!就连他的妹妹(也是作家)都觉得难为情,亲自打电话向爸爸道歉。当时很多人建议爸爸打官司,但是爸爸没有再计较,这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爸爸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度了。
淡薄名利和金钱是我从爸爸身上学到的。从而也印证了无欲则刚的道理。爸爸的朋友蒋子龙先生曾经说过:“程树榛是文学界的福将!”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爸爸的许多荣誉、包括省作家协会主席、“十三大”代表、名刊主编,甚至许多文学奖的获得,都不是他刻意去争取来的。《人民文学》主编的位置,爸爸做了十五年,早就请辞,但是上级不允,一直干到七十岁才退下来,也是文坛的一个奇迹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爸爸的《钢铁巨人》了,那种大工业题材的大气魄深深地感染着我,后来,爸爸的 《大学时代》出版,恰逢我和姐姐在读大学,记得图书馆里学生都在排队借阅此书,而爸爸送我的那一本已经被我的同学看烂了,不知被哪个细心的人用纸粘好。《大学时代》是爸爸二十三岁大学毕业时创作的,但手稿却在“文革”时被抄家的造反派抄走,但幸运的是在二十三年后又回到爸爸手中。可以想象:如果爸爸二十三岁就出版了这本书,或许一举成名;或许,因为“文革”而万劫不复。这一切,都不可知。
爸爸的创作一直是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在他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经历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但是,他以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见解写出五百多万字的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电影剧本、话剧、报告文学、评论。其中最著名的除了《钢铁巨人》《大学时代》《生活变奏曲》《遥远的北方》等等,还有引起文坛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它以歌颂改革者的深刻形象获得当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记得那一段时间,爸爸一直活跃于文坛,他的作品和人品都得到了文学界肯定,所以在爸爸任黑龙江作协主席时被中央调至北京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就不难理解了。
在文学界任职的这些年,爸爸一直在坚持文学创作,尤其是到北京后,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作品。在接近古稀之年、依然还在担任职务期间,竟然写出了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遥远的北方》,这部作品对于一些特定时期的深刻反思是鲜见的,有着深邃的政治思想内容和精神世界,但是爸爸从来不利用关系炒作自己,他的创作,是来自内心,是为了理想,因而更具力量。
所以,这些年,作家们纷纷出版文集的时候,爸爸从没想出,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劝他应该把自己近六十年的创作做一个总结,爸爸愉快地答应了。作为女儿,作为编辑,能帮爸爸做一些编辑工作,是我的幸运。
我知道我的爸爸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他从来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我们做什么。当年爸爸听说《人民文学》要发表我的散文作品时,立刻要求编辑撤下来,我也丝毫没有怨言。但是在这里,我却愿意由衷地赞扬一下我的爸爸,以我四十多年朝夕相处的理解。
我常常感叹:爸爸是一个不贪心的人,一个负责的人,少年的苦难没有让他吝啬和计较,我知道爸爸身上几乎不带钱,他不会买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对钱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于老家的乡亲,他总是慷慨解囊,对于苦难的人,他总是充满了同情和理解。
爸爸还是个充满情趣和好修养的人,小时候我们姐妹三人和奶奶最爱看爸妈合作唱戏,当然是爸爸拉二胡,妈妈唱戏。爸爸还喜围棋,常常和工学院的教授曲叔叔、孙叔叔等人对弈,有时也和姐姐摆几盘。姐姐的围棋是爸爸让子教出来的,而且由于奶奶经常在旁边观摩,以至于年迈的奶奶也会下上几盘,奶奶的棋艺绝对在我之上呢,这是许多人都想象不到的。我爸爸还有一个绝活,也是无人知晓的——他曾经为我们家打过两把沙发椅,完全是他自己手工制作,那时家里的刨子、锯等各种木匠工具应有尽有,年少的我经常坐在那舒适的带弹簧的椅子上,大声地背诵毛主席诗词……
在那些压抑的年代里,这些家庭内的小活动给我们的身心潜移默化来了许多健康元素。现在,爸爸经常在家里研磨挥毫,爸爸的字一如他人,正直温厚,儒雅高洁,我自己家的墙上挂了一幅爸爸的大字——“程门立雪”,笔迹浑然,颇有古风。而今,许多亲友都在“排队”等候他的墨宝呢!
我从小就崇拜爸爸,我的许多女同学们也都崇拜我的爸爸,年轻时的爸爸博学多识、风度翩翩,我们未来的爱人就是我爸爸这样类型的男人!所以,直到现在,我少年时代的女友见了我爸爸仍然赞叹不止:“程叔叔还这么潇洒啊!”
爸爸是我们姐妹三人的骄傲,我觉得作为父亲,我爸爸也足够幸运:三个女儿花团锦簇、事业有成;几个可爱的孙男孙女绕膝欢怡;我们不仅仅是天底下最亲密的父女,我们还亦师亦友……从小到大,我什么话都可以和爸爸说,遇到文字上的、政治上的、历史上的问题,都会打电话问爸爸,包括我的恋爱和婚姻。以至于我每每听到爸爸稳缓的声音,就有一种放松和安心,就像回到了家。
今年年初,我和丈夫带着爸爸妈妈和儿子们一起去海南度假,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带”着父母出游。坐在舒适的头等舱里,爸爸和我谈起他的一些童年往事,奇怪的是一向晕飞机的我却没有丝毫不适,听得津津有味。在海边的酒店,丈夫特意安排了面朝大海的房间给父母。每天我们都在海边玩耍,尽享天伦。面对蓝天绿海,身边嬉戏的幼小儿子们,远处仰游在水面的父亲,以及我身边的丈夫,我竟然百感交集——这些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男人们,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我走上岸,坐在妈妈的身边,看着水中属于我们的男人们,骄傲地笑了。
我特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如果真的有来世,爸爸,就让我做你的父亲吧!我觉得爸爸一生唯一的缺憾,就是幼年丧父,没有享受过来自父亲的温情。所以,爸爸,我来生要当一个茁壮的男人——做你的父亲,你今生今世缺失的父爱,来世我弥补给你,好吧!
是为序。
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