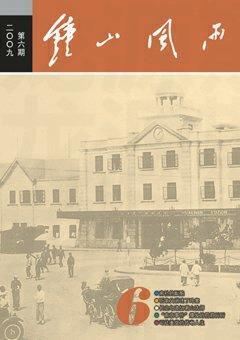陈独秀的最后总书记生涯
张家康


从筹创中共到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任过临时中央局书记、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内有“开山书记”之称。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不久即投入党内反对派活动,也就四年的时间,他又被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推至总书记的位置,这是他最后的总书记生涯。
年轻的托派斥他为老机会主义者
中国托派起源于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些学生便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1927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在红场游行时,公开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批留学生的公开亮相,可谓中国托派运动的滥觞。
斯大林以严厉的手段打击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接着被政治流放。参与红场游行的中国留学生史唐、梁千乔等人也被遣送回国。托洛茨基在流放途中完成《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写作,这个文件的第三部分便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此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将译文的第一、三部分交与大会,指示只能传阅,不得扩散。中共六大工作人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利用工作之便得到这份文件,后又向国内传送。
1928年9月,中国留苏学生正式建立托派组织,他们与苏联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的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派文件等。同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其全称为“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央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北京、香港、广州、武汉、苏州、哈尔滨等城市还建有分支机构。次年4月,总干创办《我们的话》刊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通过尹宽读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那种感觉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萦绕于脑际的疑问和困惑,似乎都已找到了答案。他开始与中共中央公开论战,而他的政治影响此时并没完全消失,兼之党内左倾领导难以服众,一些干部思想迷茫,于是便形成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为骨干的所谓党内反对派。此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正式名称,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陈独秀派”。
他们真心诚意地想加入“我们的话派”或与其合并。陈独秀甚至不惜放下架子,辞尊居卑,与“我们的话派”多次磋商。“我们的话派”却心胸狭隘,担心陈独秀等人加入后,会像《水浒》中的宋江那样抢了王伦的宝座。他们始终百般刁难,竭力阻挠。此时,刘仁静由莫斯科归国,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委托他充当自己的联络员。
陈独秀假刘仁静的特殊身份,委托他向“我们的话派”表示,有意在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理论的前提下,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刘仁静费了不少口舌,做了大量工作,总算说服“我们的话派”接纳陈独秀。不过,陈独秀等人必须履行一个条件,即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然而,就是这样苛刻的政治条件,还是遭到梁千乔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认为陈独秀是“老机会主义者”,他的要求加入托派“完全是个阴谋”。
陈独秀愤怒了,再也不能忍受如此的戏弄和侮辱,明确地向刘仁静表示,“我们的话派”既是如此态度,再也无需去作努力,他们就是加入进去也无益有损。1929年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独立的小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他们利用自己在中共的影响,加紧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
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一再批评乃至警告。他都置之脑后,继续在错误的歧途上滑行。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断然将他开除出党。12月,他们召开全体会议,亮出了本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正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等人为常委,吴季严为秘书长(后由何资深担任)。他们是继“我们的话派”后,中国的第二个托派小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次基要年轻的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等九人,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因其机关报为《十月》,又被称为“十月社”派。同年夏,游离于上述三派之外的赵济、刘胤等七人,又成立第四个托派小组织,因其机关报为《战斗》,又被称为“战斗社派”。至此,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登场了。
这班年轻的自诩为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丝毫也不给他们当年的导师和领袖的面子,无休无止地纠缠历史旧账,清算所谓“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对《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极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还在文饰自己的错误,还在散布“二次革命”的错误思想,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与斯大林的“工农民主专政”如出一辙,而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背道而驰。他们断言,陈独秀仍然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以,必须与之作“无情的理论之战争”。
在对陈独秀进行批判的吵吵嚷嚷之中,刘仁静的表现尤为突出,他自恃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以为最得托洛茨基理论的精髓。所以,在所有的批陈文章中,只有他总是带有不容置疑的断语。他说,陈独秀是“透彻的孟什维克主义”,如今又“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新商标”。还说陈独秀周围的那些人,“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所以,“我们应当丢掉他”。刘仁静甚至自鸣得意地说,当前中国的托派运动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反对派的路线”、梁千乔为代表的“投降派的路线”和他们为代表的“左派反对派路线”。
这就是中国托派的现状,三条路线实际就是三种派系,他们之间互相拆台,谁也不买谁的账。远方的托洛茨基极为焦虑,害怕刚刚兴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走入死胡同。他立即给刘仁静和中国托派发来指示,批评他们的争论“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要求刘仁静尽快地将陈独秀等八十一人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当托洛茨基读过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便立即给刘仁静复信,称赞这“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他对陈独秀明确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至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达他的问候,并告诉陈独秀:“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同时,托洛茨基又给“我们的话派”去信,批评他们和刘仁静“异常地夸大了”相互间的“细节的歧异”,指出这“是不允许与不足为训的”,要求中国托派组织必须加快统一的步伐,“共同拟订一个短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刘仁静立即向陈独秀传达了托洛茨基的信,并与“我们的话派”联系。中国托派不得不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嗡鸣于陈独秀耳际的聒噪,一时间也沉静了下来。陈独秀感慨系之,在《无产者》上发表文章说,读了托洛茨基的来信后,“很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警告道,如果现在还有人“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
统一后的托派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在托洛茨基的垂询下,已经沉寂一些时日的陈独秀,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奔走游说于“我们的话”、“十月”和“战斗”社之间,那种争争吵吵的纷乱情景,短时间内稍稍有了一些收敛。他们终于坐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协议委员会,商谈所谓统一的问题。托派的组织统一谈何容易,注定要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一些年轻的托派仍然无视托洛茨基的指示,继续纠缠陈独秀的历史旧账,对此,陈独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
可是,彭述之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首先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再提过去“谁是谁非”的政治争论,要求其他三派作出表态性检讨,承认过去对陈独秀的批评是一种错误的成见,扬言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组织的统一。托派的其他三个小组织,原本就没有统一的意愿,只是因为托洛茨基的一再催促,才勉勉强强地答应协商统一,如今经彭述之等的发难,已是松散脆弱的统一基础,眼看就有崩塌的可能。
陈独秀着急了,立即批评彭述之等人的错误,制止“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并且不许提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因为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他之所以如此积极推进托派的统一,是有着东山再起的政治设想。当时,“立三路线”受到批判,“王明路线”刚刚冒头,中共党内的多数迷茫犹豫,不知所措,处此思想混乱之际,陈独秀便萌发出托派早日统一,取而代之的意念。他郑重其事地劝告托派小组织:
“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
“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
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再次发来指示:“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而这正是陈独秀提出,并一直受到年轻的托派的批评,以至成为欲将陈独秀排斥于托派圈子之外的政治理由。多年来,年轻的托派分子们喋喋不休争论的所有问题,最终经托洛茨基一锤定音,作出了最后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他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了吧!”
三个多月后,中国托派四个小组织的代表悄然来到上海大连湾路的王茨槐家召开统一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其中谈到,托派作为反对派,“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要“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他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党领导作任何的让步”。这次统一大会决定了中国托派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或“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5月5日,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选举出由五人组成的书记处,陈独秀为总书记。
我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的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此,他开始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活。仔细算来,他一生中最后的总书记生涯,也只有一年五个月零十天。在狱中,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不大过问托派的事务,而以过多的精力忙于自身的“官司”和重操读书、写作的旧业。可是,一些年轻的托派对他还是不依不饶,频频挑战,他这才又卷入从概念到概念的“咬文嚼字”的名词争论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他又倡议联合中共,共同反蒋抗日。这一切都遭到多数托派分子的攻击,他们仍在叽叽喳喳,什么“工人无祖国”,什么“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似乎国破家亡,山河破碎,与他们毫无干系。
1935年1月,托派上海支部在托洛茨基派来的外国人格拉斯的支持下,背着陈独秀召开“上海代表大会”,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新改选中央委员会,并强令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放弃所谓“斯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否则将他们开除出党。
陈独秀一向反对外国人插手中国事务,让人转告格拉斯:“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最终由于托洛茨基的过问,这场开除出党的闹剧才不得不中途收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他走出牢房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他奔走南京、武汉等地,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指出:“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他知道,这些主张是决不会为托派所接受,因此,他一再郑重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年轻的托派还在兜售“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教条,甚至将这场战争曲解为“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这些荒谬的高调,使陈独秀极为反感。他在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坦率地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他对中国托派已是彻底绝望,表示将不受一切“圈子”的拘束,重估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之价值,因此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喜滋滋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并向友人解释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溥仪,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一直到反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