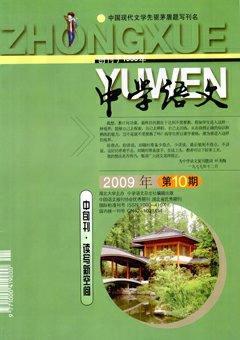树魂
周保林/文 刘慧文/评
进城多年了,我总是时刻想起我的老家,更想念那棵五人合围的柿子树。
那是一棵伟岸、绮丽的大树。主干笔直,约2米高处,生了个丫,由一棵变成了两棵;其中一个分枝离地面只有一人高,横空出世,像条长虹。一个四季,树上树下,生机勃勃。春天,树叶苍翠欲滴,含苞欲放,摇曳着一树春光,成了鸟儿寻偶嬉戏和蜜蜂采蜜之处。夏天,青果累累,挂满枝头,阳光从树叶渗透出来,柔柔软软,呈现着青春的美姿;下雨时,只闻树上笃笃响,却只滴下几点儿,美极了。秋天一派缤纷,一个个鲜红的果子,像一盏盏小红灯笼,藏身于斑斓多姿的金黄色叶间,飘出一阵阵香味。冬天,树枝光了,露出结实的身躯,最美还是雪天,银装素裹,简直成了一棵银树。
树下是我们的生活区,又是我们娃娃们的游戏场所。一清早,太阳刚染红了树尖,树下便忙开了。大人们洗衣、做饭、备家具。小孩们割猪草、拾牛粪。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早饭后,爷爷将一根藤条烟袋杆往嘴里一衔,要我给他点上火,坐在树根上,悠闲自得地吐着烟圈儿,摸着山羊胡,给我们讲故事。记得有一次,我问爷爷这棵树是哪年长出来的?爷爷笑了笑,神秘地说:“我也弄不清,只记得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曾问过爷爷,他说,他一出生就看到树有这么大。”
有时故事听腻了,我们几个光屁股娃娃,便揪着那个横枝打吊吊,树枝一弹一弹的,悠悠然,飘飘然。这时,我想起爷爷讲的朱元璋的咏蛙诗:“独坐井畔似虎形,绿阴树下掌乾坤。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这树下,不就是我们的“乾坤”吗?
晚间,树下是最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夏天,这里成了乘凉、游乐的佳境。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都带上板凳、茶杯,男人摇着扇子,在树下聊天,女人则借着凉风,织毛衣,纳鞋底,边干活,边听人讲故事,算计算计今年的收成。一个接一个笑话,从树间渗出,回旋于空中。我们一些小伙伴,便穿插其间捉迷藏。有次不慎将张三爷的椅子绊倒,让他跌了个脚朝天,讨了一声骂,我们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夜深了,人们还舍不得离去。
立秋后的第四天,是我家收柿子的传统日子。这天爷爷搬把椅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父亲收采。收摘柿子要用特殊工具,一根长的篙,一端安上一个小篾篓,一个一个收摘,以便完好无损地收进来。进屋后用罐子封好,约半个月后,当柿子又红又软时,才能品尝,那味儿又甜又香,比荔枝还要好吃!爷爷说:“柿子不能独吃,要给邻居送。金果果,银果果,大家吃了多结果。”
如水的岁月匆匆而去,柿子树在村子里许多人脑海中也许荡无痕迹了。但在我记忆中仍有它的形象,它的影子,尤其我每次回到家时,它的高大身影就浮现在我们眼前。是它庇佑了我们一家人,我永远忘不了它。
[简评]这是一篇思乡怀旧的散文。故乡的柿树既是感情的寄托物,又是本文的线索,串起作者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作者通过柿树,回忆起故乡的人和事,写出了故乡的人情美,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浓浓的情意。本文语言质朴,自然流畅,字里行间融入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情。
[作者单位:江西峡江中学]